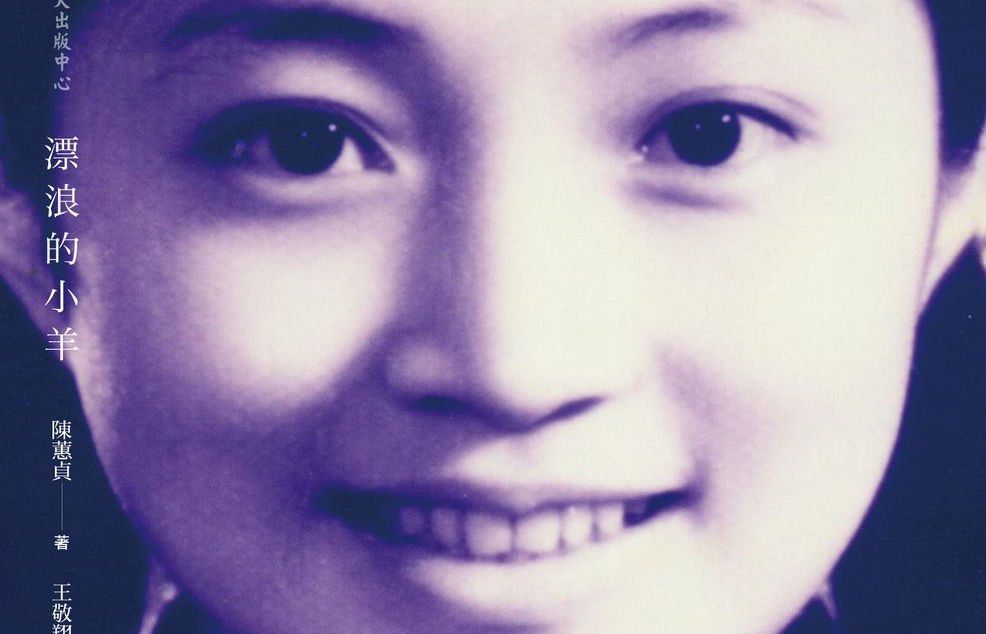〔……〕我所謂的中國的沉默。準確地說,應該是三重沉默:因為我們聽不到它談它的現在、它晚近的歷史、還有它整體上的過去。
先說它的現在。這層沉默是政權禁止公開討論領導者及其親屬、他們行使的權力、以及政權的性質所導致的。的確,八十年代的平面媒體──尤其是地方媒體──曾經出現過豐富的資訊,開始揭露弊案,分析某些社會問題,呼應民眾的不滿。
可是,太過勇敢的記者最後總是會被整肅。而最缺的也並不是資訊,而是對社會整體面臨的根本問題進行開放的討論。對新聞的控制最為有害的效果不是隱藏了某些真相,而是阻止了中國人就已知的事實表達意見,加以分析,得出結論。還記得新聞自由和反腐鬥爭,乃是1989年民主運動首要的訴求,許多記者還曾率先遊行抗爭。前此一年,曾經發生過一件引起全國許多人關注的大事。
中共當政以來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有一部電視連續紀錄片開啟了一場關於中華民族的帝制歷史及其未來的深刻論辯。整場討論其實還相當節制,卻引起了舉國民眾強烈的關注,說明這樣的論辯在中國有多麼缺乏[1]。
可以肯定的是,當有一天中國公民,不管是在國外還是國內,能對他們國家的事務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時候,就會發生一種根本的變化。我永遠記得1998年4月在日內瓦大學座無虛席的大禮堂裡,魏京生發言的時候,自己感受到的激動心情。我不是為他的到來,也不是為他所說的內容而感動,感動我的是他在那兩個多小時裡,面對公眾,安靜而清楚地回答別人向他提出的問題,其中許多還是遠道而來聽他發言的眾多的中國同胞所提。那天晚上我們聽到了,倒不是「中國」的聲音(la voix de la Chine)──這樣說沒有意義──,而是一些中國人的聲音(des voix chinoises)。
中國對於其晚近歷史的沉默,首要原因也是政權當局對於一切根本論爭所下的禁令。當然在中國的確已出現了許多的見證文字,通常是自傳或是傳記性的。特別是有關已故革命領袖人物的傳記更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但在這方面也一樣,缺的還是對事實的討論、詮釋,對其歷史脈絡的清理。歐洲為理解史大林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催生它們的歷史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對應的工作。歐洲這一努力之下產生的豐富的見證文學與反思,在中國也少有人知。
當有一天,一種類似的工作要在中國展開的時候,人們將會面臨別處未見的巨大障礙。第一道障礙就是事實的釐清。假如對歷史的檢視推遲太久,證人就可能都已消失了。在許多領域,將不會有文獻檔案來彌補這一損失。歷史真實當中整片整片的內容可能就會吞沒在遺忘的黑洞中。政權當局對於自身歷史當中最黑暗的那些章節,是竭盡所能希望達成這一效果的。
第二道障礙是這一反省勢必會導致諸多「平反」,對政權的基礎會形成挑戰。震盪將不只是政治意義上的。如果平反發生在比較近時間的未來,那將會在受害者與加害者身上引起一場從思想到情感的大顛覆。但是我們知道,人類社會只要有可能,就會保護自身免受過大的創傷,總要把真相時刻推延到真相變得可以承受的那一刻。
第三道障礙是一種概念性的困難。晚近的歷史將會需要重新詮釋。沒有哪一個政治共同體可以不必對自己所處的、定義了自身的歷史達成某種共識。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五十年來強加於他們的官方歷史。他們將必須發明另外一部歷史。我相信,在中國還沒有誰,無論是史學家還是別的領域的人,知道這部歷史的內容會是怎樣的。
這於是把我們帶到了第四道障礙上。近代歷史不可能只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被釐清,即使這個國家是中國也一樣。中國人只有在把他們自己的經歷聯繫到人類至少一百年或兩百年以來所經歷的更廣闊的歷史後,才可能真正意識到在他們的國家發生了什麼。
這需要一種眼界的改變,對他們來說會比對別人要更困難,因為中國對他們來說是那樣一個獨特的世界,那樣地自成一體。不過我敢肯定這樣的眼界轉變將是大有好處的。它將能把他們從某種程度的封閉,一種對他們國家的困境過於狹窄的關注當中解放出來。他們將明白,中國一個世紀以來所遭受的一系列不幸,儘管有中國歷史文化本身的原因,但其主因卻是這個將全人類都捲入了其中的失控的連鎖反應。他們會發現別的人民經歷過的悲劇於他們將會是可以借鏡的,而他們的悲劇對別人也會多有啟迪。到那時,他們的關懷將會取得一種現在還不曾有過的普世性意義。
中國的沉默原因也在於此: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知識人、中國的作家一直太過於關注純粹是中國的問題,或者說在他們看來是如此的問題,而他們以為,這些問題只跟他們的同胞相關[2]。
說中國對它更久遠的歷史抱持了沉默可能會顯得很弔詭,因為中國的古老歷史是不停地在官方言論、電視連續劇、日常生活、旅遊工業散佈的圖像當中被提到的。而且古老的年限還在上升。前些年還是言必稱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今天愛講的是一萬年中國文明。
與這種古老相連的一種觀念是過去的榮耀,只是被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列強的霸權辱沒而受到損害。鄧小平號召中國人展現他們的愛國主義,重修長城,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舉動。中國本該就是一個另外的世界,自成一體。與這一觀念相應的,正是中國政府在它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中經常採取的態度:中國不需要對任何人做任何交代。
這種封閉的企圖在許多別的領域也都可以觀察到。比如說,政權當局十幾年來一直系統性地鼓勵復興某些傳統的活動,像是氣功或武術,同時也回歸了傳統上伴隨這些活動的那套話語。在回歸祖先文化的名義下,它推動了怪力亂神的復興。
1999年四月的法輪功事件中,上千信眾靜坐包圍中央政府所在地,而事前警方竟然完全一無所知,此後信徒更是持續與政權對抗,其實也只是當政者自食其果而已。這個例子很清楚地說明了「文化」問題是如何可能完全出於政治操弄被生造出來,──但反過來也可能與挑起這些問題的始作俑者作對[3]。
從整體來看,這樣一種「古老偉大」其實是一個對自己的過去已經陌生化的社會才有的夢。割裂是深層次的。在城市裡,甚至在小鎮裡,很快將不會再有任何舊時生活的氛圍了。家庭,這個在中國比在任何別的地方都更為核心的制度,由於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而喪失了其根本的階序結構[4]。

伴隨著傳統結社生活的摧毀,節慶與儀式消失了。除了在南方少數的一些例外,倖存下來的都只是些碎片。傳統工藝、說書曲藝、民間戲劇,都已所剩無幾。很少年輕人對中國歷史有足夠嚴謹實在的認知,很少能夠閱讀文言這種延續到了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化與思想語言。中國在夢想自己的過去,可是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記憶的國家。
我這裡所說的,指的是大多數普通人。而對於那些在追問歷史,在研究歷史以便更好反省歷史的知識人、學者和大學生來說,情況當然不同,但卻同樣很成問題。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在思想層面一直是拿西方為參照,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而這還在繼續。一個例證就是「比較研究」的空前高漲,在所有領域都要拿中國觀念與西方觀念一一相對。
近百年來,中國的知識人做得非常徹底。他們把整個中國的過去都用西方的範疇重新加以詮釋,力求把它變成一種可說是「接軌」的歷史。他們使用了一整套借自歐洲的語彙。今天在經濟、社會政治領域,在哲學和人文科學當中使用的術語,大部分都是套用歐洲詞彙的新語彙。不管他們願不願意,今天的中國人思考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文明,使用的是來自別處的概念。因為這些新語彙在形式上完全是中國的,如今也已進入了日常用語當中,所以對於理解過去構成了一種無形的障礙,結果就造成了一種熟悉與不解相混合的詭異狀態。過去似乎伸手可及,但卻不再有任何反應了[5]。
這一情境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我所描述的連鎖反應,在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是伴隨了一場在思想領域裡不可逆流的轉化。這一轉化,相對於過去是有反對,但更是批判吸收的態度。中國在帝制末期也的確發展出了某種對過去的批判,而在1915到1925年,中國在思想上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這十年當中,更經歷了一次令人矚目的飛躍[6]。但是這一批判後來很快就中斷了,甚至似乎被遺忘了。整體上看,現在的回歸過去完全是以一種非批判的形式在進行。這也就難怪為什麼中國人今天對他們的歷史的陳述會那麼地讓我們覺得沒有說服力了。

相對於中國的過去,以及一般意義上的過去,缺乏批判,就造成了對現狀的批判失能。中國人好像是看不到他們與世界一同捲入其中的這場連鎖反應。他們看不到,但是卻感覺到了其沉重的解體效應,同時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脫節。他們期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經濟強國,像當前佔據主導位置的美國樣版那樣,可是他們發現,在這場競爭當中他們嚴重落後了。此外,他們投身到這條道路時,正碰上純粹的經濟邏輯越來越徹底的控制力造成了新的貧困,尤其是在美國,甚至是人與人之關係的扭曲變態,這不禁令他們猶豫卻步,把他們拋向了那個他們其實已被割裂開來的中國的過去。
我所謂的中國的沉默,原因就出在整個這樣一種歷史情境上。
(作者為日內瓦大學中國研究退休教授)
註釋
[1] 紀錄片《河殤》共分六集,主筆為作家蘇曉康。參閱第49頁註腳最後所引杜瑞樂的文章。
[2] 一個例子是Perry Link林培瑞的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燕京夜語》中(Norton, New York, 1992)講述的他八十年代末在北京所見的中國知識份子討論。
[3] 關於這場回歸傳統的政治背景,可參閱Catherine Despeux戴思蓓 “Le Qigong, une expression de la modernité chinoise”〈中國現代性的一種表現:氣功〉,見於En suivant la Voie Royale, Mélanges offertes à Léon Vandermeersch《追隨王道》,J. Gernet謝和耐、M. Kalinowski馬克編,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遠東學院初版,Paris, 1997,第267-281頁。材料顯示,法輪功組織在1992到1995間年都曾獲得中國官方補助以拓展其在中國與歐洲的活動。
[4] 關於中國家庭的階序結構,參看後文第74-79頁。
[5] 二十世紀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為了定義「中國特性」,賦予了中國一些與他們認定的「西方特性」相對反的特徵。這些哲學家把一種「中國思想」與一種「西方思想」對立起來。他們的作法不可避免地就成了要在兩邊孤立出一些可以對立的特徵,再根據論證的需要,賦予這些特徵一種它們不曾具備的重要性,而對不符合期待中的對立的因素則予以忽略,即是說加以簡化,有時甚至到了誇張漫畫的地步。論證結果之薄弱從前提就可想而知了。這種薄弱本身卻同時又保證了他們的說法的成功,因為容易理解,而在政治上又可以利用。康德專家出身的牟宗三(1909-1995),在香港和台北講學之時就成為了這一趨勢典型的代表。我之所以提到他是因為于連(François Jullien又譯:朱利安)從他的研究中汲取了靈感,把他的論點轉述給了法國讀者,因此複製了一種關於與「西方思想」對立的「中國思想」的論述,其吸引力與虛假的深度感恰如一場鏡像遊戲。
[6]魯迅(1881-1936)是一位打動人心的重要作家,因為透過他的辛辣、他的清醒和他的複雜,他比別的任何人都更好地體現了1915-1925這段特殊時光。他實在應該要有遠比迄今為止的法語譯介高明許多的翻譯和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