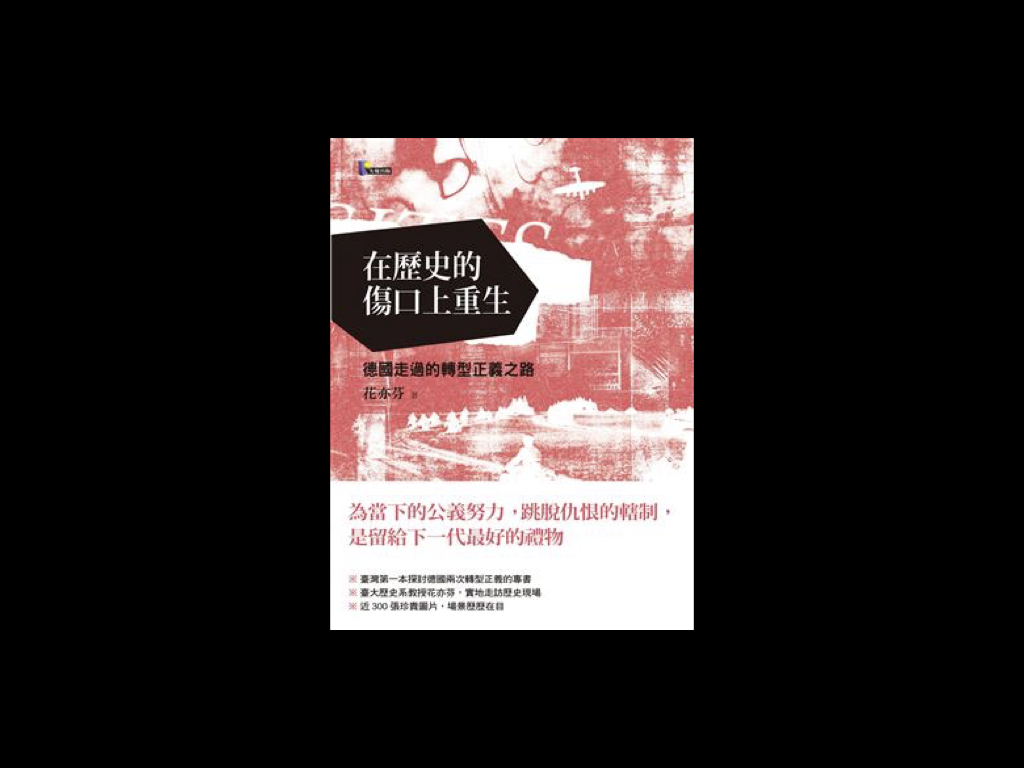1813 年 10 月 18 日,德意志聯軍在萊比錫會戰(Völkerschlacht bei Leipzig)中打敗了拿破崙的軍隊,贏得了勝利。31 年後的 10 月 18 日,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Ludwig I., König von Bayern, 1786–1868)特別選在德軍取得勝利的這個日子,為新建成的「統帥堂」(Feldherrnhalle)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從此,統帥堂貫穿了德國的歷史,串起了民族主義、納粹政權、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等重要的德國歷史議題。
從巴伐利亞王國的文化政策到德意志民族主義
1825 年,路德維希一世繼位成為巴伐利亞國王,此後他持續地改造首都,希望藉此凝聚王國內部的認同與民族意識 [1],讓巴伐利亞王國這個中型君主國與其它「強國們」平起平坐,因此,建造「統帥堂」成為路德維希一世施政中重要的一環。
建築師弗里德里希.馮.高德納(Friedrich von Gärtner, 1791–1847)在王室的任命下,於 1835 年開始在慕尼黑舊城區與北邊新城區的聯絡大道旁,建造一系列的公共建築,用以宣傳巴伐利亞王國的強盛與繁榮。[2]在這個規模龐大的都市計劃中,高德納以義大利佛羅倫斯市政廳前的「傭兵涼廊」(Loggia dei Lanzi)為藍圖,在王室宮廷與王室教堂的中間建立巴伐利亞的「統帥堂」。
統帥堂裡矗立的兩座青銅雕像,一左一右分別是在三十年戰爭中帶領基督舊教聯軍的統帥約翰.蒂利(Johann T’Serclaes von Till, 1559–1632)伯爵,與在反法聯軍戰爭中帶領巴伐利亞軍隊的卡爾.菲利普.馮.弗里德(Carl Philipp von Wrede, 1767–1838)公爵。在這兩場形塑現代歐洲樣貌的重要戰爭中,這兩名軍事將領被視為帶領巴伐利亞迎向勝利的「沙場英雄」,這也賦予了統帥堂獨特的軍事意義。
就這樣,象徵王室政治中心的王室宮廷(Residenz)、象徵宗教力量的王室教堂(Theatinerkirche)以及象徵軍事力量的統帥堂皆匯集於慕尼黑,成為巴伐利亞王國重要的文化核心。[3]
在十九世紀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狂熱浪潮下,具有軍事意涵以及象徵巴伐利亞地區主義的統帥堂被轉化成了德意志民族主義分子的政治舞台。
在 1848 到 1849 年全歐革命的浪潮中,追求社會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革命分子,在統帥堂前升起了象徵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黑─紅─金」旗。[4]市民階級群起要求身陷情婦醜聞的國王路德維希一世下台,市民更進一步要求制定憲法、成立國民議會(Nationalparlament),建立屬於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國家。[5]
最後,路德維希一世迫於壓力,將政權移轉給其子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König von Bayern, 1811–1864),但這波追求建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革命浪潮,最終仍在德意志地區專制王朝的聯手合作下以失敗告終, 維特爾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er)也因此得以繼續統治巴伐利亞王國。然而,革命的激情卻也使得這座原本象徵巴伐利亞王朝的軍事紀念堂,轉化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政治舞台。
1871 年,隨著普法戰爭的勝利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激情的民族主義者一面慶祝德意志民族再度戰勝「死敵」法國;另一方面更是在「統帥堂」前的廣場集會遊行慶祝建國。今日所見矗立於紀念堂正中央的巴伐利亞軍隊紀念雕像(Bayerisches Armeedenkmal)就是出自於這股狂熱的民族主義。[6]

統帥堂作為德意志民族主義在慕尼黑的象徵,持續被視為重要的政治宣傳集會地,用以凝聚、鼓吹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1914 年 8 月,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三世(Ludwig III., König von Bayern, 1845–1921)與民眾們在這座紀念堂前一同歡送即將遠赴戰場的巴伐利亞士兵。[7]
威瑪共和國成立後,「統帥堂」仍然是重要的民族主義象徵地。在政治危機出現時,無論是反對凡爾賽條約的修正主義者,或是反對魯爾地區被法國和比利時聯軍所佔領的民族主義者,都以統帥堂為重要的政治集會場地,高聲鼓吹走向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
1923 年納粹黨政變
1923 年 11 月,這座歷史建築又見證了一件德國現代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納粹黨政變。8 日夜晚,希特勒與其黨羽宣布推翻共和國政府後,隔日,一行人走上慕尼黑的街頭,與巴伐利亞警方在「統帥堂」前發生武力械鬥,造成警方 4 人、納粹政變者 16 名人員死亡。
隨著政變失敗,希特勒與其黨羽被逮捕、判刑,納粹黨也被禁止舉行任何演講或公開活動,但看似逐漸沉寂的極端主義卻仍然伺機而動,等待奪權的一天。[8]

威瑪共和晚期,當極端政黨開始活躍於全國政治舞台時,極端右派的納粹黨也開始用心地宣傳自己的神話。納粹黨將納粹黨包裝成德意志人民的「革命先鋒」,塑造出他們不惜犧牲性命為德意志民族「殉難」的形象。而先前在與警方衝突中喪生的 16 名納粹黨員就成了最佳的宣傳工具,他們的「殉難地」正是「統帥堂」。
納粹黨透過經常性的政治集會與宣傳刊物的渲染,他們不僅僅將慕尼黑包裝成「納粹行動之都」(Hauptstadt der Bewegung)[9],更將「統帥堂」當作納粹黨重要的政治標誌,進一步連結德意志民族主義與納粹主義。此舉讓人民迷惑地排徊在民族主義的激情與納粹黨「殉難」的神話之間,而無法理性思考與分辨納粹黨所帶來的可能威脅。
1933 年,納粹順利奪權,慕尼黑的市政廳「被」懸掛起了納粹黨旗,統帥堂也就「被迫」成為見證納粹創黨之初艱辛奮鬥的紀念堂。

(Source:Wikimedia)
納粹極權體制下的「象徵政治」與歷史紀念堂的轉譯
1933 年,納粹奪權後,希特勒立刻下令建築師保羅.路德維希.拓斯特(Paul Ludwig Troost, 1878–1934)設計一座立在統帥堂東側的紀念碑,作為「官方認證」的「納粹黨員殉難地」。紀念碑上除了大大的納粹黨徽外,還寫上紀念「殉難者」的碑文:「1923 年 11 月 9 日,在統帥堂前及在戰爭部的中庭裡,下列人們在懷抱著他們對民族復興的忠貞信念中陣亡...」[10]
除了每年固定在黨員殉難的 11 月 9 日在統帥堂舉行追思活動,不定期動員人民政治集會外,日日夜夜都有安排持槍衛兵站哨駐守在統帥堂旁。行經於此的民眾,都必須─出於自願、或是被迫地─向納粹「殉難者」紀念碑舉起右手行「德意志招呼禮」(Deutscher Gruß)。

並將「統帥堂」打造成納粹崇拜的朝聖地。(Source:Wikimedia)
在納粹奪權後,統帥堂被迫成為重要的納粹崇拜朝聖地。利用國家機器對這座歷史紀念堂進行政治轉譯,使它成為與人民日常生活相結合,密不可分的民族「義士」紀念堂。納粹黨有意識地將自己的崛起神話與德意志民族復興連結在一塊,納粹黨與國家、民族就此連結成密不可分的一體。為同時,人民在內化由極權政府所加諸在身上的服從命令後,每每行經於此地的「尋常老百姓」,也就透過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行禮」與黨、國家、民族結合成納粹主義中強烈鼓吹的「人民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效忠黨就是效忠國家、民族;反之,只要不效忠黨,也就是國家與民族的背叛者,人人得以諸之。
這種強調統帥堂與納粹黨之間連結的手段,都是為了轉譯這座歷史建築的象徵意義。
二戰後避談的禁忌與「統帥堂」的「再轉譯」
慕尼黑歷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無情的戰火幾乎把市區夷為平地,但統帥堂卻意外地只受到輕微的損傷,建築本身幾乎完整地被保留了下來。然而,這個背負著納粹歷史原罪的紀念堂,在戰後的德國社會裡成了敏感的禁忌話題。直到 1960 年代為止,西德的歷任總統們沒有一個願意在這個曾經是納粹朝聖地的紀念堂前舉行公開演說,深怕任何與這棟歷史建物扯上任何關係。[11]
在 60 至 70 年代以後,西德社會才逐漸凝聚出了社會共識,要將這座歷史建築物「再轉譯」成反對納粹的紀念地,後來才陸續有公民團體在此示威遊行,反對極右派的德國國家民主黨(Die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
1994 年,慕尼黑市政府決定在曾經立過納粹黨員「殉難」紀念碑的地方,設另一塊紀念牌,而這次,是為了紀念在 1923 年 11 月 9 日,那 4 位因執勤公務與納粹政變者發生衝突而失去生命的員警。[12]
以統帥堂來說,歷史建築的「再轉譯」與轉型正義的腳步走得相當緩慢,卻也一步步向前行。這座紀念堂過去有太多政治與歷史的情緒交雜,讓這個議題變得相當敏感。經過謹慎處理、確立期社會價值後,紀念堂成為了象徵新價值的地標。

2015 年 10 月,當德國社會因接收難民問題而鬧得沸沸揚揚之時,極度反對穆斯林移民的右派組織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計劃在「統帥堂」前舉行集會遊行,[13]甚至要在敏感的 11 月 9 日再次舉行「散步」遊行。[14]到了活動當天,他們的「散步」地點改為鄰近的廣場,但他們計畫象徵性地走向統帥堂,而這行為正是納粹時期被極度宣傳的朝聖行為:「遊行到統帥堂」(Marsch auf die Feldherrnhalle)。
此舉挑起了社會敏感的歷史議題,也激起了公民社會的怒火。三千多名的群眾在當天下午得知 Pegida 的遊行如期舉行之後,自發性地集結至統帥堂,佔領前方廣場,不讓右派組織有藉題發揮的機會。之後,群眾們更是正面迎敵,走向 Pegida「散步」的地點,團團包圍他們,抵制仇視伊斯蘭移民的遊行隊伍。
公民團體「慕尼黑是多彩的」(München ist bunt)主席 Micky Wenngatz 在受訪時明確地指出,他們之所以佔領統帥堂前的廣場,他們正是要在這個曾經被納粹黨佔領的地點,阻止新納粹與種族主義者。慕尼黑市長 Dieter Reiter 也在遊行隊伍之列,公開地向 Pegida 的仇恨言論宣戰。[15]透過公民行動的力量,公民團體取得了紀念堂的話語權,拒絕了極端右派的種族主義言論,維持社會的多元性。

統帥堂的歷史意義與記憶政治
統帥堂曾經背負著巴伐利亞王室的夢想與民族主義者建國的激情,也曾被納粹黨借為政治神話的朝聖地,而現在,統帥堂是遊客觀光打卡的熱門景點,也是民眾約會、休閒娛樂的所在。
透過謹慎的學術研究與解構神話,我們清楚看見慕尼黑「統帥堂」隨著時間的流轉與社會價值的變遷,不停地被轉譯、被賦予新的象徵意涵,而它的歷史意義正是在於成為了德國記憶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統帥堂不僅記錄了德國歷史的發展與傷痕,同時也為社會未來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歷史並不如煙,只有透過重新的「再轉譯」與解構威權時期的宣傳神話,人們才能重新接納這類具歷史意義的建築。
[1]Andreas C. Hofmann, Denkmäler erzählen Geschichte(n)! Die Feldherrnhalle in München. Nationale Begeisterung – Instrumentalisierung – Alltagsgeschehen, in: Bayernspiegel. Zeitschrift der Bayerischen Einigung und Bayerischen Volksstiftung Nr. 5-6/2012, S. 19-21, hier S. 19. 全文線上閱讀
[2]一系列的建築物包括: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Ludwigskirche, Hauptgebäude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das Münchner Siegestor.
[3]Andreas C. Hofmann, Feldherrnhalle, S. 19.
[4]Andreas C. Hofmann, Feldherrnhalle, S. 20.
[5]三月革命在德語地區的發展與結束,詳見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 Bd. I, München 2013 [1st. 1983], S. 595–606, 661–670.
[7]Andreas C. Hofmann, Feldherrnhalle, S. 20.
[8]納粹黨在威瑪共和時期的發展介紹,詳見Hans-Ulrich Tham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ebsit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9]慕尼黑被當作納粹行動的首都介紹,詳見 NS-Dikumentationszentrum München 官網簡介
[10]紀念碑碑文全文如下:Am 9. Nov. 1923 fielen vor der Feldherrnhalle, sowie im Hof des Kriegsministeriums folgende Männer im treuen Glauben an die Wiederaufstehung ihres Volkes: F. Allfarth, A. Bauriedl, Th. Casella, W. Ehrlich, M. Faust, A. Hechenberger, O. Körner, K. Kuhn, K. Laforce, K. Neubauer, Cl. v. Pape, Th. v. d. Pfordten, J. Rickmers, M. E. v. Scheubner-Richter, L. v. Stransky, W. Wolf.
[11]Andreas C. Hofmann, Feldherrnhalle, S. 21.
[12]一直到 2010 年為止,這塊紀念牌被設置在地板上,希望路過的民眾可以記著那四位曾經因執勤公務而喪命的員警。2010 年,在他們執勤的地方,也是過去曾經矗立過納粹黨員「殉難」紀念碑的正對面牆面上重新安置一塊紀念牌,以供民眾紀念。2010 年揭牌儀式的報導,見 Süddeutsche Zeitung, Gedenktafel enthüllt. Vier Polizisten gegen Hitler, 2011.3.14.
[13] Süddeutsche Zeitung, Empörung über Pegida-Demo vor der Feldherrnhalle, 2015.10.12, Bild, „Schande!“ Pegida marschierte vor der Feldherrnhalle auf, 2015.10.27,
[14]Merkur, Pegida-Demo: Münchner Freiheit statt Feldherrnhalle?, 2015.11.04
[15]Süddeutsche Zeitung, Demonstranten versperren Pegida den Weg, 2015.11.09. Und Spiegel Onlind, Demonstrationen in Dresden und München. Tausende gehen gegen Pegida auf die Straße, 2015.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