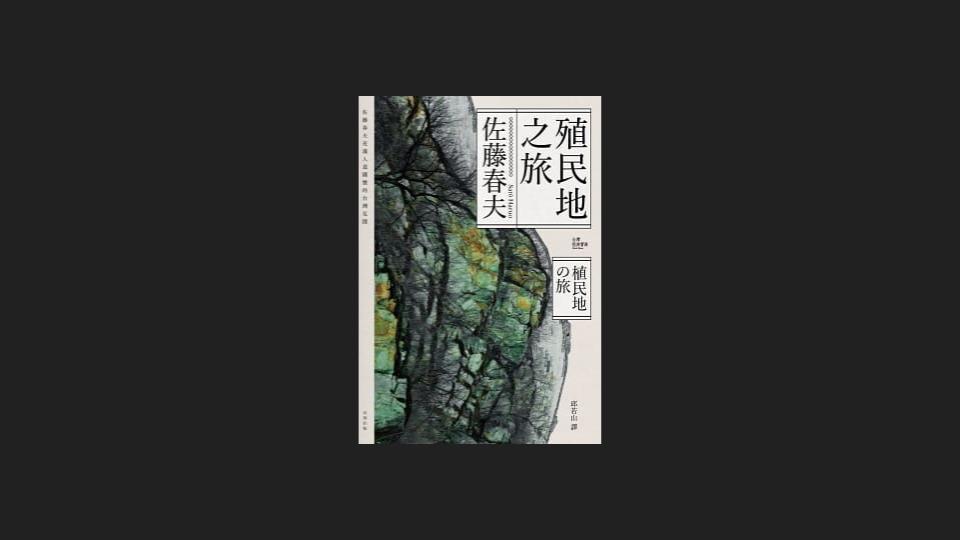「漂浪王子」法蘭克
在 20 世紀前半葉(確切地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美國和歐洲,哈利・阿佛森・法蘭克(Harry Alverson Franck, 1861-1962)是一位暢銷旅遊作家。
從 1910 年首部著作《環遊世界漂浪之旅》(A Vagabond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到 1943 年《南美再發現》(Rediscovering South America),他自己寫成的著作已超過二十本,加上兒童讀物、學校地理教學書籍和首部著作的改編本,以及身後數十年才得以問世的二戰戰史著作,合計多達三十部,可謂著作等身。[2]
這位德裔移民的第二代(父系家族來自德東的施威林Schwerin)很早就踏上了世界旅途。1900 年夏天,才在密西根大學讀完大一的他,搭上一艘運牛船橫渡大西洋,當時他只帶著三塊多美元造訪英法兩國,然後在大二開學兩星期後返校。
大學畢業前,他決心證明自己即使不帶武器、也不帶大量行裝和金錢也能環遊世界,於是在教書一年之後,只帶著一百多美元、簡單的行囊和一台照相機出發;這一百多美元多半花在攝影裝備上,他則在世界各地的基層社會中打工賺取旅費,並與常民接觸互動,多半靠徒步移動。
這趟為期一年四個月的環球漂浪旅行,不僅成就了他的首部著作《環遊世界漂浪之旅》[3],而且一出版就成為暢銷書,此後又多次再版。從此他以「漂浪王子」(Prince of Vagabond)聞名於世。十年後(1920 年),該書由他的妹妹萊娜(Lena M. Franck)改寫成精簡版《打工走遍世界》(Working My Way Around the World),此時原書已被譽為「近二十五年來最有名的旅行書籍」。這也是他首度造訪遠東,經由香港、上海來到日俄戰爭勝利後的日本。[4]

第一步的成功為他建立了繼續漂浪的信心,往後五年間,他在幾所學校任教,也為了親身體驗巴拿馬運河的工程,前往運河區擔任為期六星期的人口普查員和三個月的警察,並將這段經歷寫成了《運河區八十八號員警》(Zone Policeman 88, 1913),該書後來也發行英國版,甚至到了越南戰爭高潮期的 1970 年代又再次出版,只是此時成了批判美國帝國主義的材料。[5]
他在從軍參戰之前,足跡還遍及西班牙、中美洲的墨西哥和宏都拉斯和瓜地馬拉,以及南美的安地斯山脈;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官拜少尉的他前往法國擔任郵件檢查官,也在義大利參與戰事,因而結識了在巴黎擔任秘書和美軍志願護士的瑞秋・拉塔(Rachel Latta),當法蘭克在停火後潛入戰敗的德國旅行,並且平安歸來之後,兩人在 1919 年結婚,日後他們的女兒派翠西亞(Patricia)回憶兩人的蜜月「開始於一輛名為卡洛琳(Caroline)的別克汽車上五分鐘的駕駛教練,接著撞掉一家前門的階梯,煞車又在長長的下坡路上著火。」
隨後他們結伴踏上旅途前往西印度群島和巴塔哥尼亞,法蘭克與另一位有接生經驗的旅客就在海上迎接長子小哈利(Harry Jr.)的到來。瑞秋也擁有冒險與挑戰的性格,兩人在旅途和寫作兩方面都成了合作無間的伴侶,瑞秋隨後也寫下了《我嫁了一個浪人》(I Married a Vagabond, 1939),從自己的角度回顧了兩人的旅途和婚姻。[6]
日本、朝鮮、華北、華南到福爾摩沙
1922 年,法蘭克夫婦來到了遠東。他們首先抵達日本,從春季的北海道一路向南抵達鹿兒島,在 5 月的伊勢山田巧遇伊勢神宮每隔二十年舉行的式年遷宮儀式裡,他們看到全體市民共同參與「御木曳」,搬運神宮建築所需的珍貴檜木。[7]
而後在 6 月初的長崎得知與上海之間的定期輪船即將通航(往返長崎與上海的日華聯絡船於 1923 年初開航),看到《華盛頓海軍條約》(1922 年 2 月由英國、美國、法國、義大利、日本簽訂,限制各國海軍規模)成立後,剛完工下水就被廢棄的土佐號戰艦。[8]
他們在最酷熱的 6 月到 8 月間抵達日本統治下的朝鮮,第一個留下的印象是朝鮮各地的缺少樹木,人民穿著白衣。[9]這時法蘭克採取的旅行方式,是將家眷安置在大城市中,獨自一人深入各地探索,在繼續往滿洲出發之前,他曾登上金剛山,到達朝鮮東北邊界的雄基(Yuki,今天的北韓羅津先鋒市。他從蘇聯的海參崴渡河越境);隨後在滿洲、華北和華南也是如此,獨自以放射狀的路線走訪各地,最遠到達了滿洲里、大連、庫倫(烏蘭巴托)、青島、蘭州及寧夏和歸化城(呼和浩特)等處。[10]
8 月進入奉天時,他們目睹了第一次直奉戰爭落敗之後退回關外的張作霖軍隊川流不息地入城,對大帥的執法嚴酷也有所描述。[11]隔年他的長女凱薩琳(Katharine)在北京出生,1923 年 8 月,法蘭克在華中的避暑勝地──廬山牯嶺,為即將出版的華北遊記寫下序言〔《遊盪華北》(Wandering through Northern China)一書正是獻給長女〕,這時他的足跡也向華南深入,隨後展開與當時一般訪客有些不同的福爾摩沙之旅。
1923 年 9 月,法蘭克從江西南昌出發,沿著撫河上行,穿山越嶺進入南北兩軍往復爭奪的福建省,自邵武乘船順閩江而下,在 10 月第一天涉水進入颱風過境的福州城。他在福州會晤了時任省長的海軍上將薩鎮冰(一八五九─一九五二),也參加 10 月 7 日的文廟祭孔典禮,而後乘坐日本輪船跨越海峽抵達基隆,登陸日本統治下的臺灣。[12]

之所以如此瑣碎地記述他來到臺灣之前的行動,一方面是他先從日本內地進入朝鮮、滿洲、中國,而後跨越海峽進入臺灣的路徑,不同於其他外國訪客從日本本土到達北方的基隆,或直達南方的高雄。
研究 19 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及東亞旅行書寫的學者已注意到,在 20 世紀初期的旅行指南,例如 1920 年代日本國營鐵道發行的紅皮英文版東亞旅行指南裡,在地理上華北和華南被視為一體,但通常不包括臺灣,因此法蘭克乘船前往臺灣,其實是跳脫了多數旅行指南所建議的路線。[13]
法蘭克對這三部中國相關遊記〔《遊盪華北》、《漫遊華南》(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及本書《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的安排,也顯示出他對此相當清楚:華北的遊記包含鐵道旅行沿途所經的朝鮮和滿洲,但福爾摩沙並不收入華南遊記,而是收入《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即使他是在華南旅行期間前往的。如此一來既能清晰地呈現出政治現實(福爾摩沙當時仍是日本領土),也能讓讀者聚焦於中國見聞,而不致分心於作者個人。[14]
再者,也因為法蘭克這幾部遊記的寫作方式都是以旁觀者角度,面向與自己一樣並非專家的大眾讀者,試圖透過自認不帶感情、不做修飾地記錄自身印象和體驗,呈現出通商口岸的進步西化之外,專家、進步學人及老經驗人士見樹不見林的「真正」中國和日本樣貌。[15]
頂多依照地區排列而未必按照時間先後(例如《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開頭,法蘭克初到東京,因接待西方人的旅館毀於災變或擠滿難民而不敷使用,而被日本政府安排借宿公務員家庭的見聞,顯然是發生在 1923 年 9 月關東大地震之後,[16]但其後從北海道到九州的記述則發生於前一年),因此必須細讀各書中所提及的重大事件,才能推定他在臺灣停留的時間應是 1923 年 10 月中到 11 月底。[17]但限於筆者學力,從記述臺灣見聞的三分之一內容,目前只能辨識出一兩個時間點,未能釐清更為具體的時間表。

福爾摩沙一瞥
離開了西方人享有治外法權、宛如置身仙境的中國(他也多次承認,在治外法權保護下,他才能在中國內地旅行而不受危害),一到基隆,法蘭克立即體驗到日本人的「固執」和猜疑心:他因為護照上 t 字和 i 字的點線位置不合,而被警察扣留在船上長達兩小時,直到臺北的總督府外事課給予特別許可。警察還告誡,[18]他攜帶的旅行指南記載有誤,照相機在全島都嚴禁使用。
他乘坐火車抵達臺北,由於身穿正式服裝〔美國總統哈定(Warren Harding)在這年 8 月驟逝,美國仍在國喪期間。或許也因為美國駐臺北領事出缺[19]〕,他得以參加新任臺灣總督內田嘉吉(1866─1933)的晚餐會,[20]但在東門官邸(今天的臺北賓館)的晚宴中,與會的外國人卻被迫全程站立、無人聞問,還得付費購買難吃的餐點。
這種與中國人接待外國人大相逕庭的無禮對待,自然令他聯想到日本人既抱團排他又要求他國公平對待、既刺探機密又管制資訊,以及仿製外國商品、壟斷運輸和市場等種種表現,並譏評日本人是「出色的模仿者」,「害怕別人偷走他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想法」。[21]
法蘭克對於日本人的評價整體偏低,他在日本本土和福爾摩沙為期不長的互動之中,感到日本人並不像西方人以為的那樣聰明,甚至不那麼潔淨。上層日本人或許較為出色,但多數日本人的身高、智識乃至幽默感都不如中國人,甚至不如他們所支配的朝鮮人,日本人的領袖崇拜和一板一眼,以及軍國主義和間諜習性確實稱得上是「東方普魯士人」,揣摩上意、害怕冒犯、說話拐彎抹角則讓他們看來更不聰明,過多的禮節與粗魯行徑及漠視他人權益並存,男尊女卑的程度連西方人都難以接受,他甚至認為日本人無法成為優秀的飛行員。
但他同時也稱許日本人的耐心、沉靜、勤奮,乃至日本女性的超強能力,肯定自力更生兩千多年的日本文明不遜於西方,且擅長效法他人優點,從而對於日本歷史上的禁教鎖國,以及一戰結束後與西方列強關係時好時壞,甚至對外國的不信任,偶爾也能同情地理解。[22]
中國人聰明開朗又樂天,但髒亂無序,而且抗拒進步發明,福爾摩沙的中國人除了比中國的同胞營養更充足、外貌更整潔、也更沉默之外,風俗習慣、階級區分和信仰都與天朝人無異,較早移居島上內山地帶,成為沿海移民與山地民族之間緩衝的客家人不僅驍勇善戰,食用原住民人肉(番膏)的習俗更令人震驚。
法蘭克認為當時尚未完全臣服於日本、仍控制著廣大山林的獵頭原住民,才真正稱得上是「福爾摩沙人」,其中以北部的泰雅族最為剽悍,南部的原住民則多半已定居農耕,他們在馴化「歸順」後或許仍保有野性,但性格純樸耐勞,有些馴化的原住民在山地邊緣的樟腦寮工作或擔任基層警察、教員,有些則到了臺北成為人力車夫。

雖說是「一瞥」,但法蘭克在臺灣其實也停留了一個多月,除了煥然一新、紀律謹嚴,「就熱帶來說有點太大」的首府臺北城,他由北而南的鐵道旅行、由平地到山地的臺車旅行及沿途所見的鄉村風景,日式旅館的浴池、西式旅館的高昂價格和髒亂的福爾摩沙人客棧之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外貌差異和差別待遇、新聞媒體被噤聲、宗教自由被剝奪、風俗和道德今非昔比,以及殖民政府歷經數十年仍未能有效治理山地原住民,這些現象也沒有逃過他的目光。
他在殖民政策上經常參照美國統治菲律賓、佔領多明尼加和海地的經驗,一面感嘆殖民者濫用暴力的藉口如出一轍,批評強制同化之失策,一面卻以臺灣人不考慮獨立,印證當時正在萌芽的菲律賓獨立運動沒有出路,甚至在當時列強有意接管中國或納入「保護國」的輿論中,從日本統治臺灣和法國統治印度支那的現況,看到中國日後的可能發展。
他對臺灣原住民的前途也抱持悲觀的態度:日本和全世界對資源的無盡需求,使他們必須支配臺灣山地,弱小的原住民難免在抵抗中毀滅、或更快在酒精中萎靡,獵頭部族終將被不獵頭的文明世界征服,而只能期待日本在取得資源時履行承諾,為原住民畫出保留區。
他知道臺灣人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這一年稍早發生的治警事件,也知道臺灣人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榨取和差別待遇,但仍認為中國人的被動天性和追求安定,將使福爾摩沙的新生代習慣於日本的統治,而不像上一代或朝鮮人那樣銘記被征服的恥辱。

法蘭克對於 1920 年代的臺灣的印象與評價,與在他之前兩年曾走訪臺灣十天的英國軍官及前殖民地官員魯特(E. Owen Rutter, 1889-1944)之見聞對照起來,異同之處十分有趣。他們行經之處或許有所重疊,但行進方向、旅行性質、觀看視角、與在地人物的互動方式乃至母國各自面臨的處境大不相同,導致他們的所見所思各有所側重。[23]由於篇幅有限,無法一一列舉,在此姑且各提一樁法蘭克注意到而魯特未能留意,以及兩人都曾留意到且對日後歷史產生相當影響的見聞。
相對於魯特在人口統計中注意到臺灣島內有些中國人因屬人或屬地原則而不具有日本國籍,[24]從福州渡海前來的法蘭克,則注意到具有日本國籍的臺灣人,在享有治外法權的華南各地,特別是廈門製造出的社會問題「成了當地政府的心腹大患」,甚至成了傳聞中日本在華南搶佔地盤的口實。[25]
1923 年下半年當法蘭克經由華南來到臺灣時,廈門的臺灣人和當地吳姓宗族爆發械鬥並互有死傷,事態因日本領事調派四艘驅逐艦(法蘭克記為六艘軍艦)前來保護僑民,並出動海軍陸戰隊登岸的「砲艦外交」而激化,直到 12 月初才達成協議,日艦在法蘭克抵達廈門當天撤離,史稱「臺吳事件」。[26]
但從隔年 1 月開始,臺人又因「平日攜槍遊行、殺人越貨,視為常事」而再度與廈門市民、當地警察、駐軍臧致平部隊和北洋政府海軍爆發流血衝突,並因日本領事再次出動軍艦干預,福建軍閥內戰波及廈門而愈演愈烈,直到下半年才得以解決,事件起於臺人拒捕殺害警探,因此稱為「臺探事件」。[27]
廈門「籍民」的教育和管理,此時已成為日本政府和臺灣總督府的一大課題,到了1930 年代的南進時期,日本政府更積極利用廈門和華南各地的臺灣人,作為殖民擴張和控制佔領區的尖兵。[28]
魯特和法蘭克同時提及一點:臺灣原住民來自馬來半島。魯特引用學術研究和早期西方探險家的記錄,指出臺灣原住民語言與婆羅洲部族語言及馬來語近似之處,並勾勒他們數千年來從上緬甸遷徙到交趾支那和馬來半島,再被當地民族驅趕而航行海上,最終來到臺灣的軌跡;[29]法蘭克的旅行見聞則提及臺灣原住民的外貌與日本南方島民並無差別,連日本人都無法分辨,進而推論出臺灣原住民與日本人同樣源自馬來人。[30]
但將部分海域亞洲的人種歸類為「馬來人種」這樣的看法,是在 1795 年體質人類學之父布魯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宣告「馬來人種」的誕生後,才在英國的海峽殖民地建立過程中產生相關的論述。
這種流行於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的「假設」,所基於的往往是「外觀」上的印象,以及「慣習法」是否相同;換言之,所謂「原始馬來人種」,與 19 世紀為了建立海峽殖民地而產生的「馬來人」,兩者從動機與本質上就是不同的兩件事,但卻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相混淆,而忽略了六千年前甚至八千年前的「原始馬來人種」究竟是什麼根本不可知的事實。[31]
隨後在 1930 年代臺灣原住民「歸順」和皇民化的過程中,日本殖民當局有意識地運用這種外貌和生活習俗的近似,加上蓬萊仙島的起源傳說,以及豐臣秀吉時代高砂國進貢的歷史,塑造出「高砂族」與日本人血緣及歷史的同源性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主權再次轉移之際,仍有日本人記載泰雅族人相貌和體格與日本人幾乎相同,以及兩者系出同源,其中一支日後前往東方島國的「祖傳故事」。[32]

法蘭克的《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收筆於紅頭嶼(即蘭嶼)非常原始的雅美族(即達悟族),同時也向讀者宣告,他在日本帝國的旅行到此告一段落,北方的千島群島、臺灣西部外海的澎湖群島,乃至於南太平洋的雅浦島和馬紹爾群島等當時由日本管轄的角落則只能割捨。[33]
隨後他重新踏上華南之旅,在耶誕節前夕抵達南方「護法」政府的首都廣州過年,對統治廣州的「總理」孫文(1866─1925)政治理想與實際施政的落差,地方軍人割據橫行的實況,以及孫文政府試圖收回利權、提倡聯俄容共的事態發展有所評述;而後他以廣州為中心,先是環遊整個廣東省,踏上海南島,而後進入廣西、借道法屬東京前往雲南、貴州、四川,探訪了峨眉山和長江三峽,並遇見了尚未被文明世界征服的強大部族──倮倮人(彝族)。[34]
他在 1924 年 10 月初回到廣州,家眷從香港前來相聚,而後在 10 月 10 日乘船返回美國;當時廣州商人和市民正團結起來,欲驅逐與蘇聯結盟的孫文國民黨政府,衝突一觸即發(即「廣州商團事件」)。法蘭克並未親眼目睹雙方爆發的戰鬥,及商團被國民黨的黃埔學生軍鎮壓的過程,但他事後追述,認為孫文實際上在這次衝突之後因喪失人心而被逐出故鄉廣東省,即使孫文在隔年 3 月逝世時以布爾什維克自居,但國民黨人仍不願以蘇聯贈送的棺木為他收殮。[35]
後來的事
歷史學家克利福德(Nicholas Cliord)分析這位 20 世紀前半暢銷旅遊作家的著作,認為他和 19 世紀後半葉的英國著名旅行家──皇家地理學會第一位女性會員伊莎貝拉・柏德・畢夏普(Isabella Bird Bishop, 1831-1904)──近似,他們都試圖將自己對於所到之處的生活體驗和社會百態,以自己的五感切實傳達給讀者(甚至有意記錄他人眼中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不受任何背景知識、利害關係或各種主觀意願(無論是引進技術和文明的傳教士,亦或追求民主與科學的「少年中國」留學生們,以及讀過幾本書就自以為可以一勞永逸解決中國問題的美國青壯年)[36]影響;即使在 19 世紀後半大英帝國鼎盛時期旅行的畢夏普,和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殘破壞之後旅行的法蘭克,其上路時的心態與關懷已不再相同。
如同他自我定位的「浪人」身分,這種不受專業知識或背景拘束,不顧艱難險阻,只靠雙腳和相機(偶爾攜帶武器)就行遍天下的風格,在當時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有人稱讚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名的旅行家」,也有人將他的《遊盪華北》和馬可波羅記載風土、民情和習俗的方式相提並論;但也有人認為他的記錄太過冗長,好像感恩節大餐吃了四、五遍,即使食物再好吃也都變得難以下嚥。
法蘭克有意識地抗拒書寫「文學」,他只提供基本資訊和見聞體驗,也不會對所到之地的前途做出預言的「天真文風」,這不免引起批評,有人認為他投合了無知大眾對外地奇風異俗囫圇吞棗的喜好,卻無助於他們確切而優雅地理解外國。[37]
《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在 1924 年問世之後,隔年 5 月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地學雜誌》(The Geographical Journal)刊登了一篇書評,作者署名 O.R.,不知是否即為 1921 年曾在臺灣旅行十日的皇家地理學會會員歐文.魯特[38]?這篇書評相當嚴厲,從書腰上宣稱「日本需要一種新的觀察者」說起,直指法蘭克就算目光銳利,但仍需要在日本多生活些時日,才能夠真正觀察出一些名堂,而他所記下的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在眾多介紹日本且提供寶貴資訊的既有著述面前顯得缺乏新意。
他甚至連原創性的見解都有誤差,例如他竟宣稱獨立的可能性對於福爾摩沙中國人來說「完全不值得考慮」;對日本遭遇關東大震災說出缺乏同情心的「東京的一大部分市區無論如何早該摧毀」,因為「泥濘河畔骯髒街道旁的嘈雜陋屋」配不上文明國家的偉大首都;並且認為日本對福爾摩沙原住民的治理「公正、人道而有效率」(倘若評論者正是魯特,法蘭克的見解恰好與他完全相反),而他宣稱隘勇線的通電鐵絲網僅供自衛之用,顯然也是因為他不知道或沒讀過人類學家麥高文夫人(Janet B. Montgomery McGovern, 1874-1938)數年前親自走訪臺灣原住民部落的見聞。
當然,從常民角度出發,盡可能不帶感情、不受知識及時事牽絆地記錄日常生活見聞和體驗的「浪人」遊記,即使事隔數年之後重讀,都會感受到時代變遷與作者感受之間的強烈落差,更何況是在將近一百年後的今天?
但不論作者主觀上如何自居客觀或不帶感情,其所記錄下的見聞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個人的關懷,必定包含著作者所處時代的印記,乃至後世所感受到的偏見。今日重讀法蘭克在 1920 年代造訪中國、日本和福爾摩沙的遊記,其意義也正在於此。
克利福德注意到,法蘭克有意識地踏上乏人問津的旅行路線,從常民生活中發現「真正的中國」(以及「真正的日本」、「真正的印度支那」等),其實受惠於交通運輸條件進步,得以離開通商口岸的「白人城市」,看到多數觀光客未曾見到的景象;在刻意不顧中國追求現代化的一面,凸顯自古至今保持不變的各種風俗舊慣和民族性格之際,或許也不經意透露出美國人所正面臨的 1920 年代工業化、現代化和移民湧入的衝擊,其追尋有別於他者的「真正美國」之心理需求,而從中展現的幽默感也就多半是挖苦在地人或其他西方人,而非反思式的自嘲,於是敘事者的角色不時浮出紙面,情不自禁下起指導棋。
由此觀之,他所發現的「真正的中國」,實際上仍是「他想要看到的中國」,在面對真實存在的中國天翻地覆的巨變之時顯得蒼白無力。[39]至於他所描繪的日本領土福爾摩沙,是否在旅行者所見所感的「真實」與歷史上的「真實」之間,也有著如此耐人尋味的落差和歧異?就交由讀者們玩味了。
法蘭克在遠東的兩年多當中,除了造訪日本、朝鮮、中國和臺灣,也到了法國統治下的印度支那。此後他在賓夕法尼亞州建立了家園,但仍繼續漫遊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他已開始搭乘飛機旅行。
美國參戰之後,六十一歲的法蘭克謊報年齡加入陸軍航空軍,首先在本土負責訓練飛行員,並為戰略情報局(OSS)標示歐洲和亞洲的重要地景圖像,1944 年底奉命加入歐洲戰場上的第九航空軍,並撰寫戰史,但這部戰史命運多舛,先是軍方審查未能通過,終於等到軍方放行時,戰爭回憶錄在書籍市場上已經沒有銷路了,當 2001 年發行時,已是法蘭克去世四十年後。[40]
他在 1947 年以中校官階退役,往後數年曾受聘於豪華遊輪擔任講師,但這種行程在他看來遠遠偏離了旅行的意義,而他的遊記也不再受到讀者歡迎,直到 1962 年因帕金森氏症去世的他,再也沒有寫下任何一部作品。
由於法蘭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曾從軍參戰,而得以安葬於阿靈頓國家公墓,妻子瑞秋繼續活躍於地方社會,直到 1986 年去世前一週都還在巡迴演講,向人們介紹她和法蘭克共同去過的地方,以及法蘭克年少時代的環球漂浪旅行。[41]
臺灣學界在 1997 年開始重新注意到法蘭克的遊記,當時任教於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張洋培博士和夫人黃素鶯女士,在 1991 到 1996 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時,受中央研究所臺灣史研究院黃富三教授之託,從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Library)蒐集臺灣史料、檔案及圖書,因而閱讀了法蘭克《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所見的福爾摩沙,回國後在《臺灣風物》雜誌上簡介這本書。[42]
此次《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後半部的中譯,以 1924 年版為底本,一切疏漏和錯誤由譯者負起全責,自不待言。法蘭克的相關文件目前典藏於他的母校──美國密西根大學圖書館,但截至 2007 年為止尚未整理和編目,不知近況如何?[43]倘若已獲得整理,或許今後可望運用其中的書信、報刊資料及相關檔案,對他這次福爾摩沙之旅進行更細緻的研究。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1] "Vagabond",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vagabond(2018 年 11 月 11 日瀏覽)。
[2]著作目錄請參見法蘭克的後人為他設立的官方網站:http://harryafranck.com/books.htm(2018 年 11 月 11 日瀏覽)。這個網站主要是為了宣傳 2001 年終於得以出版的二戰戰史著作《穿越第九航空軍的冬之旅》(Winter through the Ninth)。網站設立時,仍持續向大眾徵集更多未及列出的法蘭克著作。
[3]請參見法蘭克官網《環遊世界漂浪之旅》書介:http://harryafranck.com/vagabond.htm(2018 年 11 月 11 日瀏覽)。
[4] Harry A. Franck, A Vagabond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A Narrativ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1), 457–60.另請參見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New York & London: D. Appleton-Century Co., 1924), p. 122。
[5] 請參見法蘭克官網《運河區八十八號員警》書介:
http://harryafranck.com/ZP88.htm(2018 年 11 月 11 日瀏覽)。
[6] Patricia Franck Sheffield, "Remembering Rachel Frank,"
http://harryafranck.com/rachel.htm(2018 年 11 月 11 日瀏覽)。
[7] 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pp. 76-85.
[8] 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pp. 139-140.
[9] 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through Northern China (New York & London: Century Co., 1923), pp. 3-35.
[10] 路線圖請參見 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through Northern China, p. 12。
[11] 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through Northern China, pp. 75-79.
[12] Harry A. Franck,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New York & London: Century Co., 1925), pp. 125-159, 160-195.
[13] Nicholas Cliord, "With Harry Franck in China," in Douglas Kerr & Julia Kuenn, eds., A Century of Travel in China: Critical Essays on Travel Writing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40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1. 請參見蘇碩斌,〈台湾観光の二つの歴史──戦前と戦後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海外旅行〉,2012 年度公益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成果報告書,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resources/tokyo/ez3_contents_nsf/0/9985292037255ce449257b7c002bc433/$FILE/2012sushuobin.pdf(2018 年 11 月 12 日瀏覽)。
[14] Nicholas Cliord, "With Harry Frank in China," p. 141.
[15] 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through Northern China, pp. vii-ix, "Foreword"; Harry A. Franck,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pp. vii-x, "Foreword".
[16] 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pp. 3-12.
[17]《漫遊華南》敘述廈門見聞的第八章,法蘭克提及擁有日本國籍的臺灣人和廈門當地人發生流血衝突,導致日本派出六艘軍艦前來,甚至意圖佔領;但事態最終得到解決,日本軍艦在他抵達當天撤退。參照當時報刊史料,日本驅逐艦在八月為保護僑民而到達廈門,並派遣陸戰隊上岸,日籍臺灣人和當地人在九月爆發械鬥,並與中國駐軍衝突,中日雙方直到十二月一日才達成協議。請參見 Harry A. Franck,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p. 200;陳小冲主編,《廈臺關係史料選編: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北京:九州,二○一三),頁 256-259。
[18] 隨後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底造訪臺灣的作家雷夫.帕里特(Ralph Parlee),抵達基隆時更在海岸上看到巨幅看板,明文規定「禁止攜帶照相機」。請參見ポール.バークレー(Paul Barclay),池上直子譯,〈「日本通」の目を通して見た台湾:太平洋戦争直前にアメリカ領事館が収集していた絵葉書と写真〉,《臺灣原住民研究》,12 (2008): 97。
[19] 原任領事希區考克(Henry B. Hitchcock)在 1922 年 11 月調任美國駐長崎領事之後,駐臺北領事一職懸缺一年,直到 1924 年由原任駐橫濱副領事古迪爾(Harvey T. Goodier)接任。請參見http://politicalgraveyard.com/geo/ZZ/TW-consuls.html(2018 年 11 月 12 日瀏覽)。
[20] 請參見〈內田總督の晚餐會 東門官邸に於ける〉,《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10 月 17 日;〈內田總督晚餐會〉,《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10 月 18 日。
[21] 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pp. 185-188.
[22] 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pp. 105-125. 請參見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Through Northern China, pp. 56-57。
[23] 關於魯特的福爾摩沙之旅,詳見E. Owen Rutter, Through Formosa: An Account of Japan's Island Colony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23);本書已有繁體中文版,請參見歐文.魯特著,蔡耀緯譯,《一九二一穿越福爾摩沙》(臺北:遠足,2017)。
[24] E. Owen Rutter, Through Formosa, p. 94.
[25] 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p. 162; Harry A. Franck,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p. 200.
[26]上海《申報》關於「臺吳事件」的報導,請參見陳小冲主編,《廈臺關係史料選編:一八九五-一九四五》,頁 256-259。
[27]1924 年的衝突始末,請參見陳小冲主編,《廈臺關係史料選編:一八九五-一九四五》,頁259-288,引文見頁 260(《申報》,1924 年 1 月 6 日)。
[28]請參見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上冊第二章。關於廈門臺灣籍民的研究,先前多半聚焦於他們作為日本協力者或抗日運動參與者的角色,例如王學新,《日本對岸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較為同情理解的角度,請參見江杰龍,《臺灣人在廈門活動之再探討(一九一一-一九四六):以鴉片、走私、漢奸問題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29] Owen Rutter, Through Formosa, pp. 241-247.
[30] 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pp. 224-225.
[31]「原始馬來人」與殖民地建立過程中運用的「馬來人」兩種概念之差異,承蒙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廖晉儀先生補充說明,在此致謝。
[32] 請參見傅琪貽(藤井志津枝),〈臺灣原住民族的近代日本國家認同(一九三五-一九四五)〉,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2014 年 4 月 2 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Column/Column_Fujii_110.html(2018 年 11 月 2 日瀏覽);芹田騎郎著,張良澤編譯,《由加利樹林裡》(臺北:前衛,2000),頁 83、133、159-160。
[33] 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p. 235.
[34] 路線圖請參見 Harry A. Franck,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p. 16。圖上並未標示法蘭克從福州到臺灣的行程。
[35] Harry A. Franck,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p. 649. 法蘭克在廣州停留時曾會晤孫文,整體來說,他讚許孫文的崇高理想和愛國情操,以及嚴格自律、閱讀求知的生活,但批評孫文作為熱情的宣傳家,擅長破壞而不擅長建設,實現理想的具體行動往往引發後患;領導廣州政府時期為鞏固地盤而引進客軍、橫徵暴斂,更與中國境內其他軍閥無異。請參見 Harry A. Franck,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pp. 259-296。
[36] 法蘭克對這幾種人的批評,請參見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through Northern China, pp. vii-ix, "Foreword"。
[37] 請參見Nicholas Cliord, "With Harry Franck in China," in Douglas Kerr & Julia Kuenn, eds., A Century of Travel in China: Critical Essays on Travel Writing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40s, pp. 133-145。
[38] O. R., "Review: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by Harry A. Franck,"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65:5 (1925.05), pp. 449-450.
[39] Nicholas Cliord, "With Harry Franck in China," pp. 138-143.
[40] Katharine Franck Huener, "Harry A. Franck: A Brief Biography," http://harryafranck.com/haio.htm(2018 年 11 月 13 日瀏覽);Patricia Franck Sheffield, "Remembering Rachel Frank," http://harryafranck.com/rachel.htm(2018 年 11 月 11 日瀏覽);"Winter Journey through the Ninth," http://harryafranck.com/journey.htm(2018 年 11 月 13 日瀏覽)。
[41] Patricia Franck Sheffield, "Remembering Rachel Frank,"
http://harryafranck.com/rachel.htm(2018 年 11 月 11 日瀏覽)。
[42] 張洋培、黃素鶯,〈哈利.法蘭克眼中的臺灣〉,《臺灣風物》,四八.一(1997),頁 193-200。
[43] Nicholas Cliord, "With Harry Franck in China," p. 203n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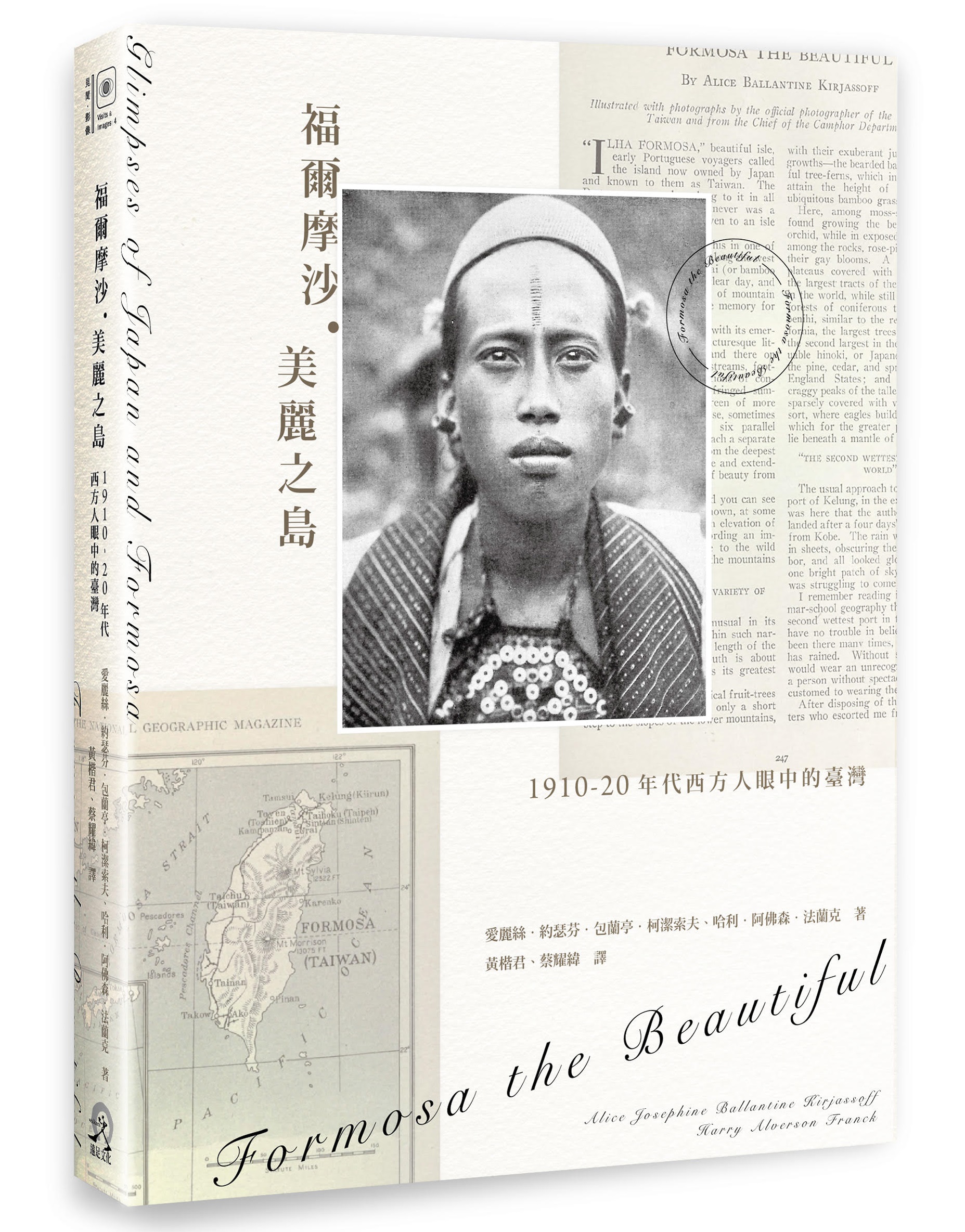
本書收錄了兩篇 1910-20 年代西方人旅遊臺灣的報導文章,記錄下一百年前臺灣的身影和面貌。
第一篇文章是出自 1920 年 3 月號《國家地理雜誌》的報導文章〈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由愛麗絲.柯潔索夫撰寫,描述 1916-1919 年間她與外交官夫婿居住臺灣時觀察到的點滴。
第二篇文章由美國旅行作家哈利・法蘭克撰寫,他在 1923-1924 年從日本到中國後造訪福爾摩沙,1924 年出版了《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本書收錄後半部他在臺灣的所見所思:〈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福爾摩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