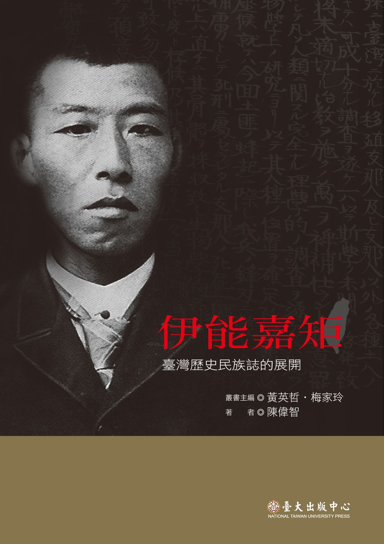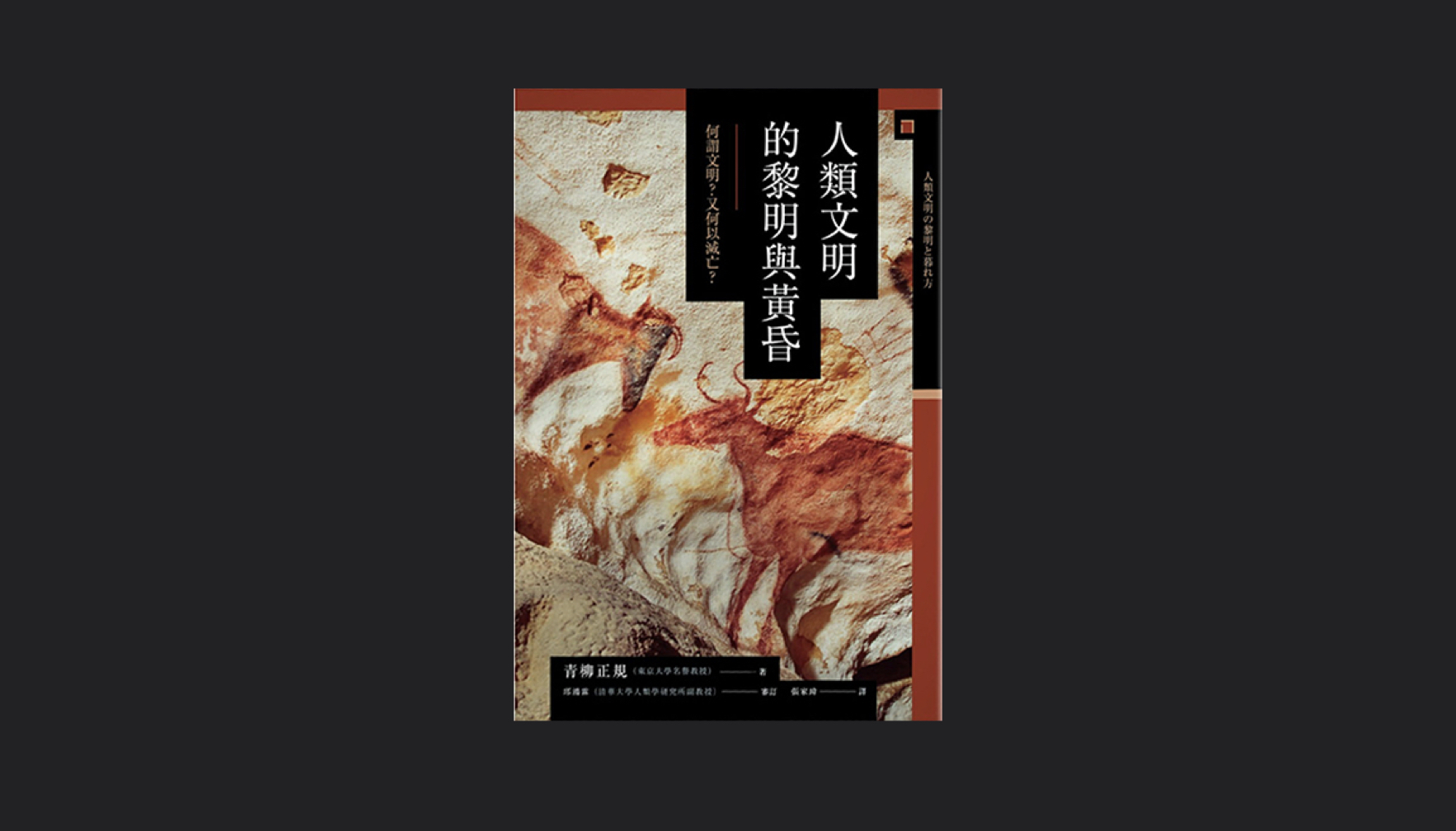臺大出版中心在二月十五日於世貿一館迷你沙龍舉辦「攀登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巨峰──重現伊能嘉矩的踏查蹤跡」講座,邀請到《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一書的作者陳偉智先生,與翻譯了多部包括伊能嘉矩、鳥居龍藏等重要日治時期臺灣史料著作的楊南郡先生,對談伊能嘉矩當年的臺灣路。
陳偉智先生首先分享楊南郡先生對他的影響,他高中、大學時期喜愛閱讀自然寫作的作品,楊先生的《與子偕行》除了自然書寫外,更有人文歷史的層次在其中,陳偉智先生對此感觸很深。陳偉智先生又以伊能嘉矩的成就類比楊南郡先生的翻譯工作,楊先生以一己之力在僅僅數年間翻譯了許多臺灣的重要著作,其實和伊能的業績相似。
伊能嘉矩除了擔任臺灣總督府的下級官員、參與總督府的調查計畫外,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他的調查工作與研究。他的田野資料和研究成果成為重現臺灣歷史的重要文獻。他在臺灣調查的十年間,恰好是日本統治方針引起臺灣社會巨變的前夕,他目睹了當時臺灣社會的原本樣態,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而楊南郡先生將這群以伊能嘉矩為首的人類學家在臺調查的資料翻譯成中文,讓臺灣歷史的研究者可以更容易入門,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陳偉智先生同意楊南郡先生對伊能嘉矩基業的位置及貢獻的看法,而特別提出兩點分享。首先是伊能的田野調查方法與他在田野中的經驗。在一百二十年前,田野工作不僅辛苦,又有許多危險。伊能雖不像鳥居龍藏能進入高海拔的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調查,主要是在淺山地帶和平原地區調查,但還是遭遇到幾次幾乎喪命的危機。因為多族語言不同,伊能相當依賴當地通曉多種語言的助理擔任翻譯,才能與原住民溝通。
另外,在淺山地區的原住民部落已經由漢人或傳教士累積了一些基本的調查成果,成為伊能重要的參考資料。伊能的行程緊湊,一天可以調查多個部落。這與伊能想問的問題有關。當時人類學的核心問題就是人種起源,伊能想找到人種分類的依據和素材,也就是基本語料和起源的口述歷史,因此他收集資料的速度很快。
二是伊能嘉矩研究的時代意義。伊能受到演化人類學的影響,強調不同人種發展的階序關係,因此他參考原住民的社會組織、宗教等特質,建立了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發展程度順序。這樣的研究方向雖已不是當代人類學關注的問題,卻是當時普遍的研究方式。十九世紀末,近代人類學者紛紛向世界各個角落展開人種的研究,伊能嘉矩的研究可說是將臺灣納入了世界人類學的研究範疇之中。
長年從事翻譯工作的楊南郡先生指出一個重要現象,購買伊能嘉矩著作中文譯本的外國人比臺灣人還要多,尤其是日本人更專為書中註解而買。因為書中有許多臺灣原住民部落的專有名詞,需要透過註解才能詳細了解,於是日本許多大學來臺收購中譯本。另一個學界的風潮則是對原始史料的重視,反省臺灣歷史的重建過程,需透過荷蘭文書的史料重新開始,連帶地,伊能嘉矩等人在臺灣的第一手資料也重新受到重視。
伊能嘉矩是研究臺灣史的先驅,他在臺十年建立起臺灣史的基礎,可謂「臺史公」。與伊能嘉矩相仿,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三人都是在年輕時來到臺灣,沒有學術地位、作為下級官員的薪水也很低,他們多以徒步的方式深入山林進行田野調查。伊能在平地則坐轎子,因為坐轎子比徒步走過崎嶇的道路要快得多,而且坐轎比較不容易被劫匪盯上。雖然辛苦,但他們憑著一股對學術的熱情,將研究做得徹底。當時漢語的臺灣史書對原住民習俗皆是以「番俗」概括之,後經伊能嘉矩調查後,將各族的習俗區分開來,這是伊能嘉矩貢獻卓著的地方。
楊南郡先生說,伊能嘉矩在日本時就已經對人類學有強烈的企圖心,他加入東京人類學會,同時也參加人類學講習會,並學習朝鮮語、清國官話、愛奴語等。來臺後不到一個月,就和田代安定組織臺灣人類學會,可見其強大的企圖心。伊能嘉矩並未停下學習的腳步,他收養了兩個泰雅族小孩,學習泰雅族語。甚至回到日本仍潛心研究,將堆滿臺灣研究資料的書房命名為「臺灣館」。他旺盛的企圖心值得我們學習。
當時人類學的潮流才剛開始,伊能嘉矩銜接上這股潮流,甚至比西方世界更早。民族學的潮流啟動之時,臺灣做為實驗先鋒,締造了非凡的成果。現在還有很多成果未被整理、翻譯,有待有志之士發掘。
陳偉智先生補充道,我們很幸運在當時有伊能嘉矩一號人物走遍臺灣,留下了豐富的文章與田野筆記。伊能對人種階序的解釋有他的時代背景,我們以現今的眼光觀之當然不必盡信,但若我們將伊能的田野筆記當作是他在時間之流中的一個片段的目擊紀錄,便能讓我們窺見些許已然消逝的臺灣的殘光片影。
楊南郡先生最後說,關於平埔族的研究,都以研究荷蘭的文書為主,但現在平埔族還是很被邊緣化。在明治年間,總督府發動了一次對平埔族的大規模調查。伊能是研究平埔族研究最大的貢獻者,舉凡語言、番俗,甚至和官員對話的樣子都一一記錄下來,也發表了完整的研究成果。伊能曾說過,平埔族不快點調查就要消失了;現在平埔族就像是大樹下的小草,在漢族這棵大樹下只能苟且偷生、永遠都長不高,但還能調查。以後就只能調查平埔族的廢墟,為其灰燼默哀而已。平埔族漢化的過程非常重要,而伊能嘉矩的田野調查恰好保留了這一個過程,成為現在平埔族研究的重要資料。
(作者為臺大歷史學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