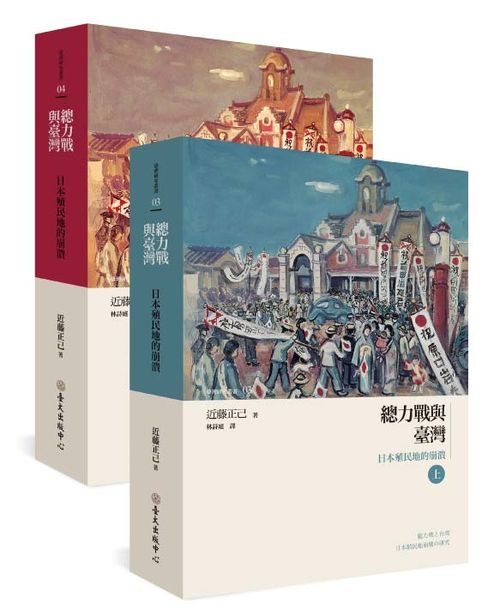近藤正己教授的《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於去年十月在臺出版中譯本,是臺灣歷史學界的盛事。這部寫成近二十年的研究,如同吳密察教授所言,「仍是日本殖民時代後期臺灣史必讀的鉅著。」在中譯本問世之後,終於能跨越語言隔閡,呈現在華文讀者面前,必將激起學界更多的對話和討論,提供人們對於臺灣的過去與當下,更深入的理解。
臺大出版中心藉著近藤教授近期來臺參加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辦「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安排了一次訪談,希望能讓讀者更認識《總力戰與臺灣》以及這本書的作者近藤正己教授。
《總力戰與臺灣》中譯本收錄於吳密察教授為臺大出版中心主編的「臺灣研究叢書」,在訪談的過程中,吳密察老師也同在現場。吳密察老師雖未直接加入對談,卻不忘提醒讀者,近藤教授此書最關鍵的創見,在於從日本帝國整體的架構,去理解其對臺灣的殖民統治,重新審視了既有的歷史解釋。近藤教授能提出那麼多深刻的問題和觀察,在吳密察老師看來,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在史料上堅實的基本功夫,這往往是今日「資料庫世代」的研究者所缺乏的。
從近藤教授和吳教授兩位老師的互動,可以感受到兩人間深厚的情誼,更能得見作為同世代的學者,他們對於學術的熱情與堅持,這份強烈的情感或許才是推動學術研究不斷前進的最大動力。
以下是這次訪談的內容紀錄,盼望能透過這份文字的整理,傳達我們在訪問過程中所體會到的那份熱情與堅持。
問:想請近藤教授您談談當時為何會對《總力戰與臺灣》中的相關課題感到興趣?當時所面臨最大的困難和挑戰為何?
我開始思考這個議題,是因為當時在日本的臺灣研究中,對於1930年代後半到1940年代的歷史幾乎沒有先行的研究。戰前所出版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及井出季和太的《臺灣治績史》等臺灣總督府方面的書籍,都僅敘述到1930年代中期。對於「戰時的臺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成為需要填補的空白。
也正因為幾乎沒有可以參考的研究,不得不從摸索的狀態出發。在日本,我先看了日本政府、日本軍的內部資料,但是不太完整,在毫無頭緒的情況下,我先從閱讀新聞報紙開始。在日本國內,我可以閱覽到《解放日報》、《大公報》等報刊,但對於1940年代的臺灣新聞、雜誌,則沒有專門收藏在一處可供閱覽的圖書館。比如《臺灣日日新報》我還是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即今日國立臺灣圖書館前身)讀到的。因此,在追索這個研究題目上,最大的問題是史料的發掘。也透過對史料搜尋和閱讀的過程,一步步建立起對戰時臺灣的理解。
問:《總力戰與臺灣》出版於1996年,經過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後,學界在相關議題上有什麼後續的開展和變化,值得有興趣的讀者注意?
這段時間內,已有不少新的相關研究問世,比如說這幾年已陸續出現利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臺灣銀行等檔案資料進行的專題研究;然而,從整體角度對臺灣總督府進行討論的研究則還沒未出現。同樣地,能夠概觀整個1930年代後半到1940年代前半的臺灣史作品,亦尚未出現有依據新史料而成的研究。
不過,我在《總力戰與臺灣》第二部所討論的問題,學界已有後續的成果,例如何義麟教授的《二・二八事件―「台湾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ィクス》(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此一傑出的著作,書中描繪了所謂的「半山」們回到臺灣後,所面對的臺灣政治狀況,可以加深我們對「光復」後臺灣的理解。

問:您曾在1970年代末來臺灣求學,並和臺灣許多重要的臺灣史研究者交往,能請您談談您和臺灣和日本之間臺灣史研究者的互動?
現在在日本的臺灣研究者,幾乎都和戰前的臺灣統治或臺灣研究,沒有人際上的關聯,現在的日本臺灣學會在1990年代才成立,是從戰後長期研究上的空白所出發。對我們在第二次大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來說,戰前的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殖民地統治的歷史,以自己的眼光去重新審視、重新看待,是不可欠缺的工作。
與臺灣的臺灣史研究者往來,也與戰前的大學研究者不一樣。現在歷史學界的臺日關係和1970年代時截然不同,當時臺灣在蔣家的威權統治下,一般日本學者不願意來臺灣,關心臺灣社會的學者非常少。但在1970年代以後,臺灣的民主化運動興起,日本的年輕人開始對臺灣產生興趣。就這樣,從1970年代到今天,我們戰後世代的研究者和臺灣人研究者間建立了「友好」的關係,這個「友」不是單線的,是有好幾個層次的,聯絡密度相當的濃厚。
問:想請問您現在所關注的研究方向?
這幾年我進行的研究,一是臺灣總督府官僚──內海忠司的研究。因為我們找到了他的日記,內容從大學時代到官僚時期,一直延續到戰後,十分龐大;此外,還發現了他出任官僚時的行政資料等等。現在已經出版了二本,內容自1929年到1945年。除了將日記完整的翻刻成活字外,還邀請幾位相關的學者,共同研究殖民地官僚當時的統治現場,嘗試由日本殖民地官僚的行動和想法,去看待殖民地統治。
另外,此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共同召開「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我將發表〈「殖民地戰爭」與在台日本軍隊」〉,論文中將帝國主義國家在執行殖民地統治時所用的武力手段,命名為「殖民地戰爭」,來和一般國家與國家間的「戰爭」作為區別,並討論了由臺灣總督指揮,與武裝抗日運動對決的軍隊。所以,抗日武裝運動以及配置在臺灣總督下的日本軍,是我目前最關心的研究課題。
明年四月起,我想將從事研究的地點從日本移到臺灣,進行以前所沒辦法做的田野調查。因為在1970年代,我當時無法進入原住民生活的地域,現在我很希望能和臺灣的年輕人一起去進行這項田野調查。
問:今年是中日戰爭結束七十週年,對今日的人們來說,您覺得對殖民地臺灣或太平洋戰爭的歷史,進行研究和思考,意義何在?可以帶來什麼啟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社會遭遇到的第二次總力戰,總力戰就如我在書中所表明的,殖民地宗主國要求殖民地人民協力作戰,而作為協力的代價,不得不給予殖民地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利。就這點而言,對總力戰的勝利者,比如英國、法國亦是相同的。戰爭的結果,使得殖民地的形式從地球上消失,就這樣意義來說,也可以將此戰爭定義為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戰爭。因此,殖民地研究、戰爭研究以及後殖民主義研究等等,對二十世紀的歷史研究,尤其是對臺灣研究來說,都是基調的主題。

問:您在《總力戰與臺灣》一書中,以「同化」和「光復」構成了第一部與第二部兩個不同的世界,並在中文版的序言提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是戰後「臺灣政治狀況的出發點」。想請問您採取將兩者並置,一同觀察的用意?
帝國主義諸國的殖民地統治類型,有以英國為代表的「自治」型,和以法國為代表的「同化」型。戰後的殖民地解放類型,大多數是「獨立」的形式,臺灣則是「光復」的形式,是回到殖民地化以前的狀態,情況較特殊。「同化」及「光復」皆非在日本殖民地下的臺灣人自己所能選擇的,就這意義來說是「他律的」。臺灣人在戰後需面對並處理日本殖民地統治時的「同化」,以及戰後新的中國的「光復」問題。
若說臺灣人有歷史包袱,那就該是「同化」和「光復」吧。也因為如此,我認為如使用「同化」及「光復」的概念來論述,就能將1945年臺灣人的處境表達出來。
問:您在書中觸及霧社事件後殖民地政府在理蕃政策上的改變,您對原住民的研究相關領域的後繼者有很大的啟發。作為該領域的先行者之一,您對現在思考這議題時有什麼建議?
我在臺灣留學的1970年代,臺灣大部分原住民的居住區域,除了少數觀光地外,不要說是外國人,就連漢人也很難進入臺灣的原住民社會。因此,我對原住民的理解,都是經由臺灣總督府的《理蕃之友》、《高砂族調查書》等龐大的史料,以及各村落所留下的須知簿、戶籍簿等官方記錄而來的。我們作為研究者要書寫或詮釋民族及地域的歷史,對於以往統治者所留下的記錄,一方面要面對它,將它當作歷史史料來看待;另一方面還要離開它,要擺脫統治者原有的意圖,進行重新解讀的作業。
問:您在《總力戰與臺灣》一書中,使用了吳新榮日記的資料,後來也參與內海忠司日記整理的工作,對於您來說,日記作為史料優勢和限制為何?
日記,能將所研究時代的人的心聲傳播給現代的人,尤其對外國的歷史研究者而言,那是理解構成當時社會的人們內心動向的第一級史料。
吳新榮的日記是透過一位地方上醫生的眼睛,傳達給我們當時臺灣地方社會的動向。對我來說,當吳新榮在面臨「改姓名」時,從他的日記裡,我可以讀到他那動搖心中的變化。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林獻堂、黃旺成等日記陸續公開,這些日記的出版成為臺灣史研究上不可缺少的史料。又或者像殖民地官僚內海忠司的日記,可以作為檢證(或檢視)身處殖民地統治最前線現場,對於臺灣史研究應該有一定的貢獻。
問:最後您有什麼想對臺灣讀者或年輕一輩研究者說的?
前面提到,明年起我就預定將研究的地點移到臺灣,除了看臺灣總督府檔案,也想到臺灣各地進行田野調查。有機會的話,我也想和臺灣的青年和年輕研究者們交流、談話,也想從這些年輕朋友處學習許多東西。
現在日本大學生最為關心的,是香港的民主化運動、臺灣的太陽花學生運動,以及現在臺灣高中生所關注的教科書問題等。我也對香港及臺灣的學生們對於將來抱有什麼樣的遠景非常關心。這些年輕人心底所抱持的新希望,以及這個社會到底將如何回應這些期待,我認為是今後東亞新世代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在每一個時代,開拓、創新的都是年輕人。不論是去年的太陽花運動也好,近期高中生所發起的反課綱微調運動也好,我相信臺灣的新世代、年輕人懷抱著對下一個時代的遠景,下一個時代的藍圖。
我很高興能和這些臺灣年輕世代的人一起看臺灣歷史。謝謝。
(記錄者臺大歷史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