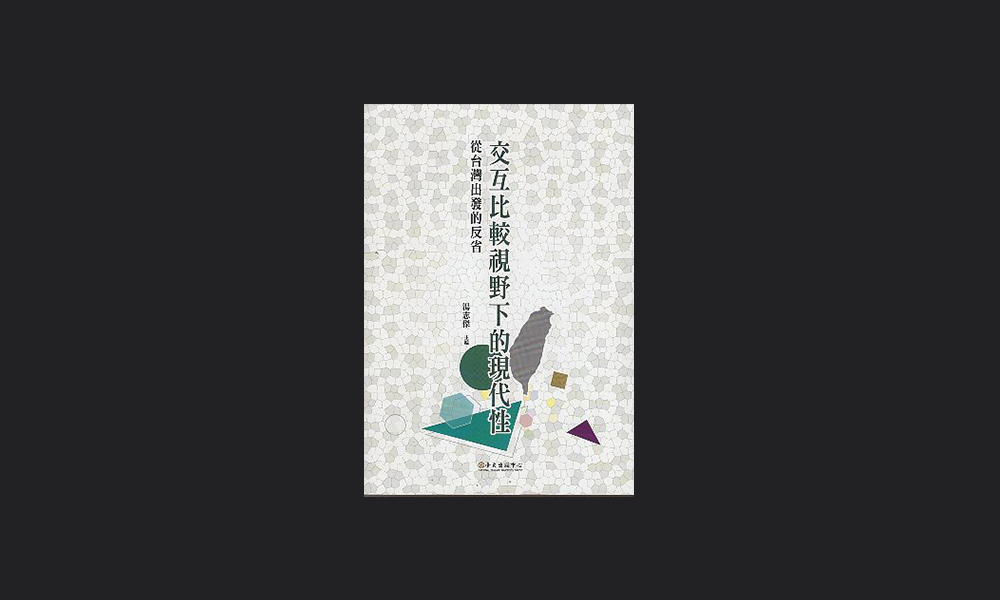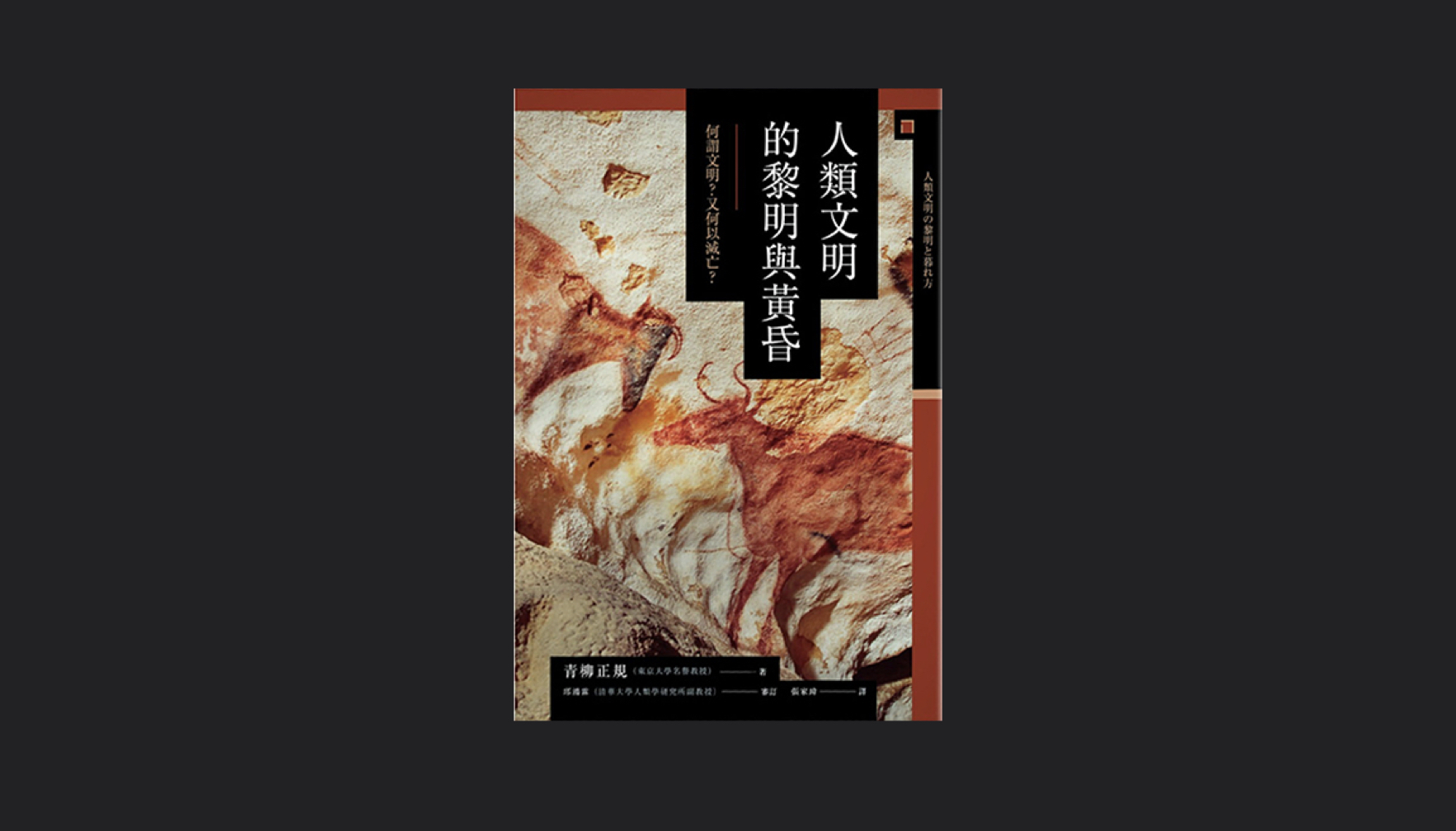點:從臺灣研究到臺灣學派
鑽研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與研究者們,可能都聽說過不少著名的學術派系,舉例來說,地理學有所謂的洛杉磯學派、經濟學有所謂的芝加哥學派,而社會學有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雖然「學派」的英文「School」聽起來比較優雅,不像中文給人一種黑道幫派的感覺(西西里黑手黨、香港三合會、日本山口組……),但事實上,每個學派確實都立基於特定立場產生的知識/權力。
也就是說,在世界上眾多國家、地區、都市裡的大專院校中,洛杉磯/芝加哥/法蘭克福的在地學者們成功地掌握了話語權,並成為其他人追隨的老大(優雅說法:被人引用的典範)。從這個角度思考的話,臺灣比較有名的是竹聯幫而不是還未誕生的「臺北學派」、「臺灣學派」這點好像有點讓人難過。
先不管黑幫的比喻有沒有笑點,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直以來確實都很難走出島嶼之外。雖然在冷戰時期,各國學者若要認識「中國」都必須來訪臺灣,而 90 年代臺灣的民主化也曾一度成為世界性的學術話題,然而近年來臺灣的本地案例至多被用來印證或挑戰西方的理論典範,難以成為獨當一面的研究主題。
在這樣的脈絡下,有志之士開始在海外發起所謂「臺灣研究」:除了已有 25 年歷史的北美臺灣研究學會以外,根據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主任羅達菲(Dafydd Fell)的整理,臺灣研究目前已有超過十個附屬於歐美大學的學術機構、三個國際年會,以及一本國際期刊。
即使已有不少資源投入學群的建置,羅達菲亦承認,「在收到大筆投資之後,一些臺灣研究單位仍舊遭逢與臺灣省政府一樣的命運」。[1]而與羅達菲同屬亞非學院的博士候選人亞然更指出,學者們只有「在滿足了自己所身處的學系的研究/教學要求之後……才另外進行臺灣研究」。[2]
換句話說,雖然體制化相當重要,臺灣研究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小心不陷入以量取勝的資源競爭遊戲;若是學術資源只是用來漫無目的地大量生產以臺灣為名的本地知識,或是用來毫不批判地套用西方理論來分析臺灣的個案,臺灣研究仍舊走不出被其他系所或知識典範壓制且忽視的景況。
究竟要如何不因臺灣的國族身份而在研究上過度故步自封,但又同時在抽象理論的層次上照顧到臺灣的特殊性呢?除了羅達菲提出「打造比較性的課程,鼓勵學生將臺灣與相似的國家如日本與南韓相比」以外,前數年主要由本土人文學者領軍所編輯的《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已開始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出發思考具有「跨脈絡性」和「可投射性」的臺灣理論[3]。
今年初,《知識臺灣》作者之一的湯志傑更從社會科學的脈絡出發,編輯《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一書,並在書中提出打造世界性的「台灣觀點」、「台灣學派」(43)的野心,可以說是替臺灣研究跨出了概念化的重要一步。
線:從東西對立到關係網絡
在《交互比較》這本雄心壯志、幾乎長達 550 頁的巨著中,湯志傑以強烈的解殖民色彩,繼續發展他在《知識臺灣》一書中已經提出的「多元現代性」概念,試圖奪回往往被西方學者獨佔的話語權,並「從本土視角重新理解現代性」(3)。
過去,人文社會學界時常視現代性為向心且線性發展的結果,也就是認為現代性以西方強權為中心傳播,並且由西方在時序上率先發展。然而,湯志傑指出,近來許多研究已經發現此種西方領先的論述其實忽視了許多歷史證據。實際上,構成現代性的物質與思想基礎皆是「在各地相互連結、交織成現代世界社會的過程中,由各地處於這樣一種糾結交錯的複雜關係網絡中的人、事、物與行動所共同生產出來」(5)。
有鑒於此,湯志傑首先提出研究現代性問題的學者應擺脫西方中心觀點,並「交互比較」各地「相互連結的歷史」(5)。但同時,學者也必須小心不陷入過度強調地方特殊性的陷阱,其本土視角「必須夠抽象,方能涵括各地不同的發展經驗,並容許交互比較」(25)。
這種奠基於網絡式連結的思考,有潛力解決學界時常虛設的「一與多的(對立)問題」(61)。無獨有偶,批判比較文學的臺灣研究學者史書美近來亦同樣提出「關係的比較學」來挑戰過去的西方及其餘的二元對立。[4]從關係性的角度來看,現代性不再是任何一方的獨佔神話,而是相互牽連的網絡。
從社會學的立場出發,湯志傑在本書中不僅邀請許多受本土訓練或在本地研究的社會學家撰文,他更批判臺灣社會學界的「殖民無意識」,指出許多「欠缺歷史思維的社會科學家」(16)仍舊複製著西方對現代性的理論來詮釋非西方的案例。他認為修正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參考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的「歷史轉向」(21)。
在這樣的脈絡下,全書的選文都不只是研究貌似普世的社會現象,而是選擇鑽研西方或臺灣的不同歷史階段,並大量引用、解析、及詮釋不同史料。此舉不但使本書的學者們得以連續性的觀點來挑戰斷裂的現代史觀,更跨越了長久以來僵化的方法學邊界。
筆者曾撰文評論《知識臺灣》一書,指出該書的弱點在於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作者們,並未能夠在書中於方法學上進行對話。[5]相較《知識臺灣》,本書結合歷史文本閱讀與社會現象分析的手法更加讓人耳目一新,也使不同學者有了比較與對話的可能性。唯有在此基礎上,本書的學者們才能進一步抽象化他們的研究,邁向臺灣理論的可能性。
面:從解構西方到探問本土
如同前述,本書的優點在於其並非只是隨機收錄不同領域中與臺灣相關的研究論文。相對的,全書作者都以社會學為主軸,將批判的火力鎖定在現代性概念上,並且都「視功能分化為現代性最重要的結構條件」(25)。
雖然本書標題並未特別強調作者們對於治理理性、專業主義,與功能分化等議題的關懷,僅選擇點出在指涉範圍上稍嫌過於廣泛的「現代性」一詞,然而實際閱讀以後可以發現作者們幾乎主旨皆在思考不同的社會領域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成為獨立自主的專業範疇。
舉例來說,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三位本土學者便各自從經濟、文化、政治的方向出發,考察這些當今早已普遍化、全球化的概念在歐美原先的論述與物質基礎。首先,吳鴻昌便指出當今象徵市場自由化與商人獨立性的經濟現代化,其實並不是歷史當初提供的唯一可能性。相對的,世界各地其實產生了所謂的「資本主義多樣性」,而西方主導的經濟現代化只有在近代才成為主流。
另一方面,林峰燦的文章雖未比較西方與非西方的不同發展,他詳細的整理文化一詞在歐美地區如何從指涉貴族特權,擴張為階級特色、帝國影響,一路到最後蛻變為大眾生活的一部份,顯示文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實代表相當不同的群體。而蔡博方則選擇從反思公民身份著手,指出現代的公民身份與其貌似與生俱來的權利並不是一直密不可分。實際上,在現代化以前就產生的專業主義,可能才是國家願意給予特定人士國民權利的基礎。
雖然這些學者並沒有在文章中納入第一手資料,而大多是以整理西方學術圈晚近的批判研究為主(有時讀起來像是概論教科書或文獻回顧),然而他們提醒我們,許多眾人習以為常的現代觀念其實是在不同的時空狀態下,被多元的政治與社會勢力所定義並散播,而最後才回過頭來影響了歷史的發展。
另外,他們對於西方現代性的批判考察同時也展現了臺灣社會學界既本土化但同時也國際化的多樣性。誠如 STS 女性主義學者唐娜・哈洛威所言,光是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知識是不夠的;研究者為了不形成孤島,必須時常藉由翻譯跨越學科的藩籬。[6]
然而,翻譯外來知識從來不是船過水無痕;事實上在本書中,有許多外來詞彙或顯尷尬,或與本地概念有所衝突。當蔡博方將西方的「gentlemen」翻譯為「仕紳」時(245),我們不該輕易將其與本書中林文凱筆下討論的清代臺灣「仕紳」畫上等號(299-300)。而林峰燦筆下的歐洲「culture」雖然譯為「文化」,但其與本書另一位作者齊偉先所說的臺灣宗教「文化化」,或是鄭祖邦所思考的中國天朝主義「文明」或儒家「文化」在本質上亦有極大差異。[7]這些翻譯所產生的模糊地帶提醒我們,為了理解現代性,光是回到西方追本溯源是不夠的,研究者們更必須交互比較不同地區,才能得到更多啟示。
這凸顯本書第三部分的重要性。此間,作者們從臺灣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文化,與經濟等層面出發,不但與第二部分的西方現代性進行批判性對話,並且也挑戰過往學界對臺灣現代性的想像。
舉例來說,雖然一般認為臺灣的現代統治理性必須一直等到劉銘傳之後才慢慢展開,林文凱卻認為有必要「重估清代在台灣長期現代性發展上的意義」(269)。即使清廷在早期並未對臺灣進行系統化的直接管理,然而林文凱認為政府實際上透過本地的郊商仕紳自治等要素來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並未延緩臺灣現代化的腳步。[8]
另外,齊偉先則透過史料與田野研究,點出臺灣的本土宗教信仰──尤其是以廟宇為基地的神明──走出了一條與西方基督宗教相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面臨著全世界世俗化的潮流,本土信仰卻未消退,而是重新與不同的現代經濟、傳播等領域結合,繼續生產自身的符號與儀式。
鑽研臺灣經濟史的謝斐宇則是試圖以臺灣的中小企業模式做為全球主流資本主義以外的特殊案例,指出不受國家干預並不斷自由累積資本的大公司並非唯一典範。以臺灣的經濟發展而言,得到國家在技術與財務上幫助的複數中小企業,最後得以和其他同質企業構成所謂學習網絡,並進行產業升級。
這些案例都再再顯示臺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味的抄襲西方的範本,但也不是故步自封,而是在比較與連結的情況下調整出一套自己遵行的規則。再者,有許多原先並不被認為符合現代性典範的台灣特色,在本書的論證之下,促使我們必須以多元現代性的框架去理解它們。
本書的第二與第三部分綜合起來,所意圖達成的便是跨越西方與臺灣的鴻溝,將臺灣的個案提升至能夠挑戰及回應西方抽象理論的境界。不過,這並不代表本書沒有其缺陷:當第二部分主要焦點都擺放在重思歐美概念,而第三部分則以臺灣特色回應時,本書似乎犯了湯志傑在導論中所急欲避免的「一與多」的二元對立。當湯志傑提出以關係網絡來理解現代性時,西方與臺灣之外的歷史經驗甚或理論思想卻都難以進入本書的範疇,甚為可惜。
事實上,許多文章在進行臺灣與西方的比較時也難以達到平衡:舉例來說,林文凱雖反轉清朝治理的落後形象,但他在文末結論仍舊認為西方國家因戰爭上的優勢,因此其現代性是較為成熟的;而齊偉先雖不斷強調臺灣本土宗教與基督宗教有所差異,但全文卻少有篇幅仔細深掘基督宗教自身的多元樣貌。大體而言,第二與第三部分的論文若是能夠在議題上更好的整合,或許讀者能夠有更深刻的啟示。
在西方與臺灣仍舊在比較上有所隔閡的情況下,以臺灣為標題的本書最後以當今中國的天朝主義作為壓卷之作便顯得相當耐人尋味。確實,與其與西方現代性相比,臺灣的現代性發展在概念與物質基礎上或許與中國(及整個亞洲)有更直接的連結,而本章作者鄭祖邦更指出一直以來主導中國不同政體的天下思想不但使其與西方現代國家有所不同,更讓其不斷藉由「邊疆地域的混雜、模糊與變動性」(423)來保持政治邊界的彈性。
若說此種模糊的治理手法能夠算作是某種另類現代性的話,天朝體系顯然和資本主義一樣是道雙面刃:帝國主義者能夠將其作為擴張的藉口,但邊疆地區(如臺灣)卻也能夠以此作為脫離中央影響的擋箭牌。畢竟,天朝不是民族國家,而臺灣與中國也不是一國。
網絡:從解殖西方到解殖臺灣
《交互比較》這本社會學研究新書,帶著明確的對話目標及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臺灣社會學以及臺灣研究注入強大的能量。不但學生們可以將整本書做為教科書使用,爬梳西方與臺灣在不同領域上有關現代性的文獻與史料,學者們亦能從此書的批判關懷出發,持續以更另類且有趣的社會發展或專業化來反思過去許多有關現代性的成見。
如同前述,本書的基本立場是解殖的,也是跨學科的:湯志傑不但鼓勵社會學進行歷史轉向,更期許本土社會學不要癡癡尾隨西方學界。然而,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感到好奇,為何臺灣的人文學界早已在 90 年代大談後殖民、後現代,解構西方中心,但社會科學乃至於科學研究卻難以解殖?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更加嚴苛,催促人文、社科,乃至科學圈都加速與彼此進行跨學科對話:雖然本書主要僅借助歷史研究,然而人類學深度田野、文學文本閱讀等等應該都能夠在資料及理論上更加豐厚研究成果。畢竟,現代性並不只是社會科學的關注對象,而是所有學術研究的核心關懷之一。
在本書的立論中,湯志傑表示在 「既有養成訓練下,我們對真實的西方不夠熟悉」(24),也因此造成本土學術研究時常誤將西方視為一塊鐵板,並且尊為圭臬。然而,在更加認識「西方」過後,我們勢必質問:有所謂「真實的西方」的存在嗎?再者,為何臺灣學術研究的解殖只選擇挑戰西方呢?日本與中國對臺灣造成的影響是否也需要解殖?
最重要的是,臺灣研究自身也不是一塊鐵板,若是要理解臺灣內部的多元現代性,是否也必須對自己進行解殖?原住民、客家人、東南亞移民工等群體在以閩南人為主的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不論是研究臺灣的傳統還是現代(或許兩者未有斷裂),未來的臺灣學派都必須將西方以外的更多要素納入比較的關係網絡中,才能獨樹一格。
(本文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生)
[1]Dafydd Fell, “The Golden Age of Global Taiwan Studies?” Taiwan Sentinel.Oct. 24, 2017.
[2]亞然,〈這是台灣研究的黃金年代〉,《明報》,2019 年 2 月 11 日。
[3]陳瑞麟,〈可以有臺灣理論嗎?如何可能?〉,《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台北:麥田,2016
[4]史書美,〈關係的比較學〉,《中山人文學報》39 期,2015。
[5]沈昆賢,〈世界史、主體性與學術社群──讀《知識臺灣》〉,《說書》,2016年 10 月 14 日。
[6]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14.3 (1988)
[7]另外,本書中有些英文學術名詞則是沒有進行中文翻譯,像是「learned professions」(262)
[8]有趣的是,如同前述,蔡博方筆下的歐洲仕紳顯然與林文凱筆下的清代臺灣仕紳是截然不同的:蔡博方的文章中指出歐美歷史上的現代化發展主力是「由仕紳到志業」(245);然而,林文凱的研究顯然指出臺灣的仕紳仍舊是現代化的重要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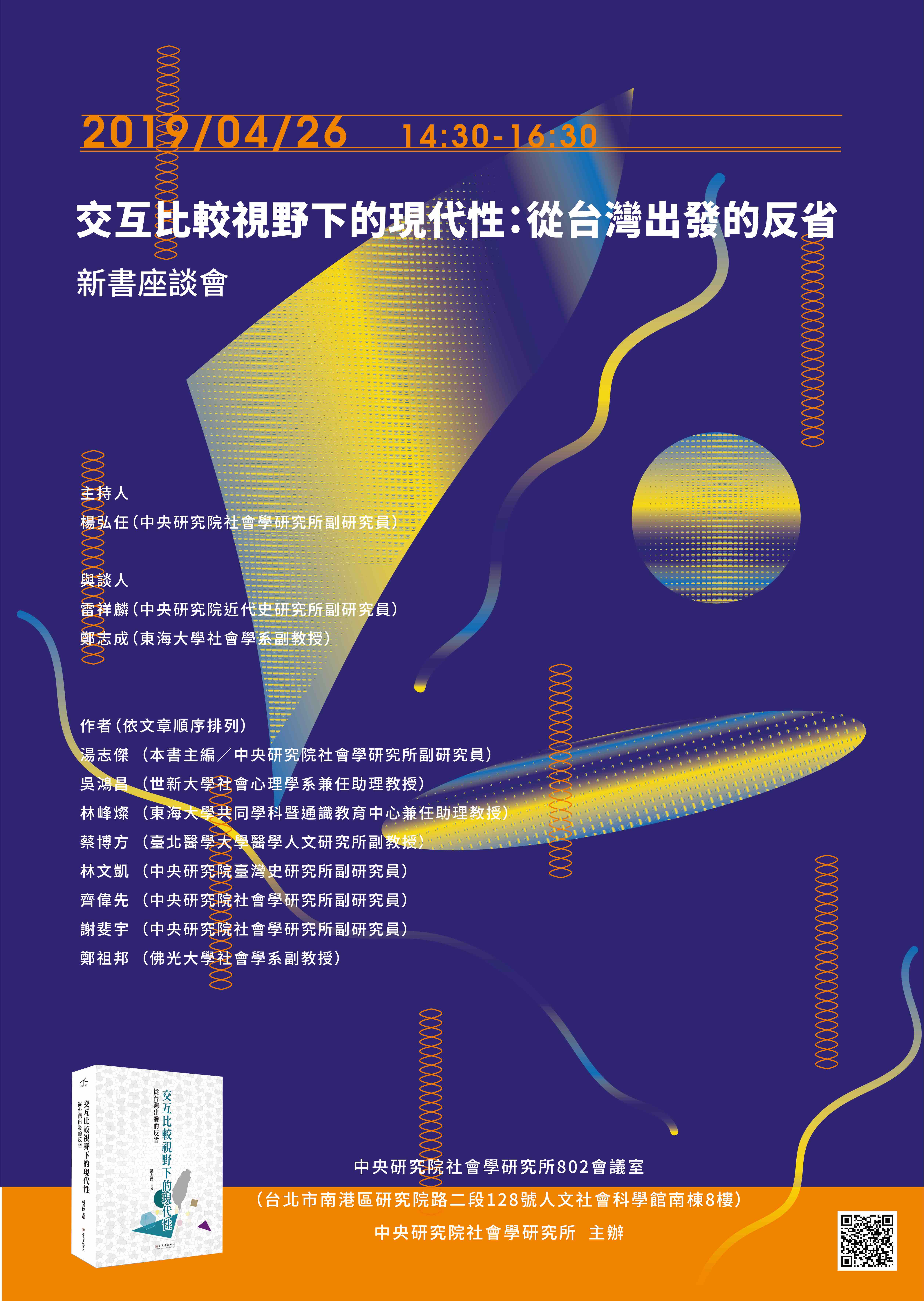
【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新書座談會】
▍時間:4 月 26日,14:30-16:30
▍地點: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802 會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