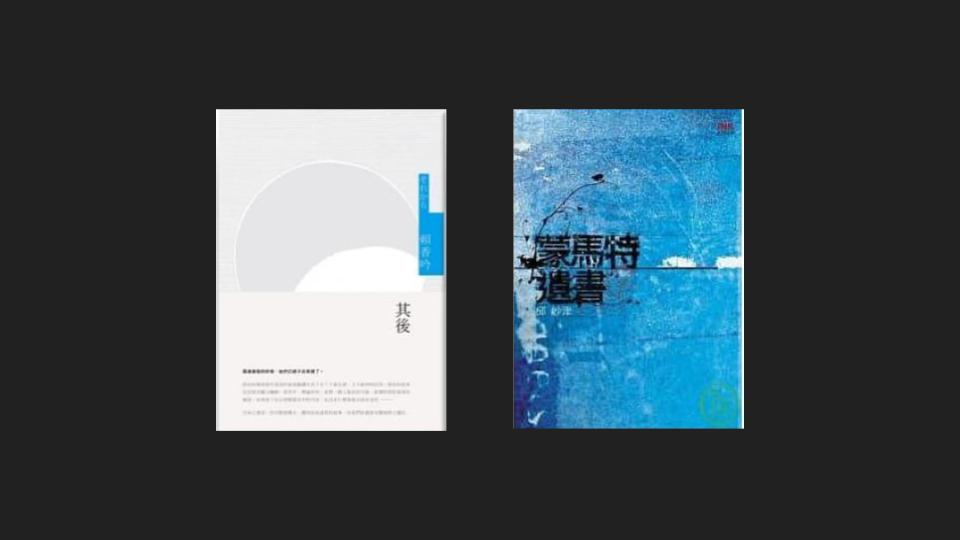即將步入而立之年,有時候不免對讀博士的初心感到迷惘。學術專業的道路坑坑絆絆,幾年清苦的博士讀下來,教職稀缺,終身職更是可望不可及,一關闖過一關,學問卻無盡。做學術的熱情不免在日常生活中瑣碎中渙散,一日日的閱讀、思考、書寫,一日日的教學、批卷子、備課,一日日的申請助學金、贊助,一日日的煮飯、洗衣、通勤。現代人的苦痛我們統統都承受著,甚至是妄想著改變些許這樣的現代生活模板,卻更掉入了生活的陷阱,泥沼纏身,不得脫出。然後是手上的論文。緩慢的進行,閱讀中文文獻,用英文書寫,一面還要翻譯原始文本,怎麼翻怎麼不滿意,怎麼寫怎麼怪。
於是我隨手選了書架上的一本英詩評論選集,作者是英詩界大名鼎鼎的 Helen Vendler(1933-),現執教於哈佛大學英文系(是的,在 84 歲高齡,她依然站在課堂上)。通常在寫作遇到瓶頸或是英文卡殼的時候,我都會抓一本與專業相關的書,時常能人豁然開朗,也能回到學術英文的語感當中。
今天抓的便是 Vendler 的這本《那海,那鳥與那學者》(2015)( The Ocean, the Bird, and the Scholar )。大約是前幾個月便買了這本書,但是還沒有仔細閱讀過。取下它之前預期的是正統的學術著作,是那種在〈序言〉裡面是對全書的概括總結,方方正正,整整齊齊。一打開,沒想到居然是 Vendler 的個人自傳。
我想幾乎所有投身於學術研究的人都有自己的專業偶像,也有很多崇拜的業內明星。Vendler 可以說是評論詩的學者裡面很特殊的一位,在上個世紀中期便隻身在美國學界打天下。那是二戰結束不久,那是一個仍然保守,對女性外出工作充滿敵意與不信任的時代,更不用說是知識產生的大學校園。Vendler 在序言中緩緩而談,從她一開始讀研究所便決定鑽研詩,而非任何其他文類,這在當年的英語文學當中非常少見。那時的流行是選擇一個時代,好比浪漫主義,而浪漫主義時期的各種文類都必須有所涉獵──在現今研究所選擇題目的時候,已經不如此行事,但是吊詭的是大學開課仍然是以「浪漫主義」或是「現代文學」等時間性範疇作囊括性的教學。
在日日冗長的閱讀,孤獨的寫作與繁瑣的教學業務當中,在學界打滾的我們需要維持社會所期待的我們的專業形象,看似自由而且微小的工作時間,背後是不能間斷的自我要求。但是我們幾乎是入不敷出。學校給的薪資會以一種美好的匯率出現,比如一個小時時薪高達一千台幣,但是工時給妳算的奇少無比。大學課堂的教學要求極高,教學內容亦是分秒必爭,從教學大綱的安排、批改作業,及安排與學生面談的時間,林林總總,所耗費的心理都遠遠超出了那站在課堂上的兩個小時。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 Vendler 的自傳中接收到了鼓舞。Vendler 認為,在她的事業當中,最為消耗她的生命的經驗即是她博士剛剛畢業那幾年。離異,單身帶著幼子,沒有終身教職,沒有出版物。為了生活,她一年教授十門課,一個學期兩堂,晚上夜間部一堂,暑假兩堂。如此一來她所有的時間與精力都耗在了日常的教學之中,這樣的工作強度僅能度日而已,幼子連托兒所都去不起。但是她堅持寫作。在她快支撐不下去之時,她捫心自問,是否有任何方法能減輕她的生活壓力?她知道,就是不寫作。努力過著日復一日的日子,勉強度日。但是她內心在吶喊著,「不行,他們不能這樣逼我!」她說,「他們」指的也許就是生活本身。
於是她繼續寫作,寫莎士比亞評論,寫里爾克的評論。為了生活也寫過違背自己原則的書評。但是她不斷地寫。將評論家的角色貫徹到底。她要證明,她不只是一個母親,她更是一個詩評家。詩評家,才是她生命的價值與歸依。那些生活的瑣碎激勵了她對更為舒適的生活渴望,讓 Vendler 在其專業的道路上更為善戰,而不是屈服在性別歧視、專業壓力與日常消耗之下。她是幸運的。不知我是否也能如此堅定而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