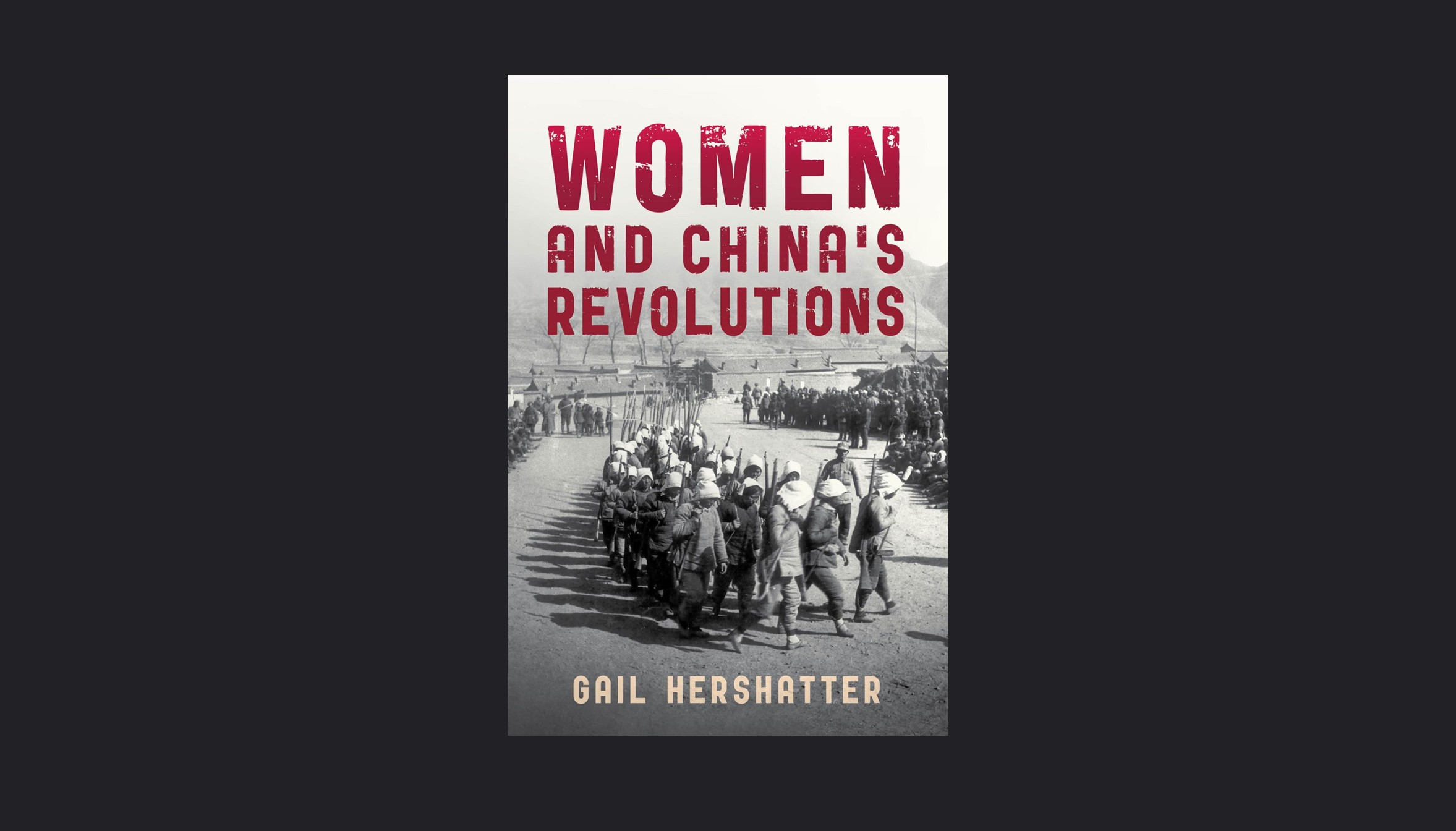「國際婦女節」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根基,它始於 1908 年,當時美國制衣行業的女工在紐約市游行,要求縮短工時、提高工資、獲得投票權。時至今日,這個節日卻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成為頗有商業意味的節日。像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這樣提出「向前一步」的時尚商業精英,正成為女性的榜樣,而不再是女工或革命者。與此同時,當丁玲關於婦女節的一番慷慨陳詞這兩年走紅,多少令人意外,因為丁玲被譽為社會主義作家,並在 1951 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
1942 年,她在延安寫下「三八節有感」:
網民稱讚她筆頭敏銳而犀利,敦促同胞覺醒成為現代公民,並為困難做好準備。從這個現像或許可以看出,很多人,包括女性,已經不再滿足於新自由主義下的成功模式,並且在思考如何超越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論述,從其他思想和文化資源尋求理解和力量。
更重要的是,丁玲這番話廣傳,顯示了歷史資料的意義,讓我們看到無論多麼零散或邊緣的歷史,都可能給後世帶來新的意義和鼓勵。
這也是我在讀美國歷史學家賀蕭(Gail Hershatter)的最新作品《女性與中國革命》(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時的感觸。賀蕭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視角,生動地展現了包括丁玲在內的那些女性的故事,而她們通常都只出現在有關中國歷史著作的腳注中。當然,在既有的話語中,婦女的歷史地位經常被引用,以表明過去的某些問題,或以女性的「陰性」屬性來表現中國的弱點。但是,女性除了被動的「陰性」屬性之外,還是教師、士兵和工人,在當代中國擁有更加複雜和流動性更強的多重身份,正如我們近幾年在以寫作才華而出名的農民工范雨素身上所看到的那樣。
賀蕭問道:「如果把女性放在過去兩個世紀的敘述中心,會如何改變對歷史的理解?」她認為我們習慣從單一角度講述歷史,但中國歷史是如此複雜,在繁榮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男性精英,和北方女農所看到的、體驗到的歷史會非常不同。
要從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的角度講述歷史,就會面臨資料稀缺的問題。儘管如此,賀蕭在重建歷史方面仍然做得非常出色。例如,在〈帝國的性別勞動:1800 至 1840 年〉這一章中,她通過檔案和歷史著作的腳注,為那些無名的婦女立傳。儘管資料有限,她還是努力通過對女性和性別的關注,提供了新的見解,尤其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關注的時刻,例如太平天國運動。
太平天國運動通常被稱為激進和具有革命性的運動,且對社會問題採取平等主義的改革。但賀蕭認為,太平天國的親王積累了大量錢財和資源,其中一些擁有幾百名妻子,更與數千名女官和奴婢發生性關系,因此這場運動本身,包括它的「平等主義」,依然是父權式的。
上海這樣的現代港口城市,通常被認為受到了更多進步影響,有更平等的性別觀念和實踐,但賀蕭展示了歷史的另一面:當男性精英在上海的商業、新聞、文學和政治領域找到新的前景時,女性的新職業則包括從妓,為那些精英和他們的大時代陪酒賣笑,以便文商政客歡快交流,談論如何建立新的社會。
但女性,或任何其他邊緣化群體,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種種危機的受害者,也是過去兩個多世紀以來每個重大建設項目和社會發展的參與者。在這本書中,我們了解到清末女性如何管理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在家中教育女兒、安排聯姻,還通過編織和紡紗為帝國晚期的經濟做出了貢獻。我們還學習到當時的稅收和道德秩序是如何產生的,譬如纏足的女性留在家中編織大大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也作為按時交稅的良性主體使家庭和社會秩序井然。
賀蕭也討論了「隱性勞動」的概念,包括生殖勞動,並研究了勞動分工如何限制婦女的社會適應性和可見度,最終這種基於性別的勞動分工從公眾的理解中抹去了她們對中國進步的貢獻。根據 1850 年代的資料,男性從事更多知識生產和商業活動,而女人除了負擔更多家務之外還需要務農,這種分工顯然不平等。婦女確實在紡織業做出卓越的貢獻,但商人雖然為了爭奪婦女的勞動力而相互競爭,卻只向女性提供原棉和紗線,再向她們購買制成的紡織品。這種分包制度使婦女無法直接銷售自己的產品,也失去了市場能見度和參與權。
這本書展示了在 1980 年代在改革開放政策下,婦女如何成為國家改革的主體。隨着 1970 年代後期農村地區進行改革,黨國將土地私有化並承包給家庭,農民卻仍因其農村戶口,無法像城市同行那樣獲得國家福利。國家鼓勵數百萬人離開農村,到城市中謀求新的工作,卻沒有為他們制定相應的福利計劃。這數百萬被國家遺忘的人口中大部分是女性。同樣,1980 年代開始制定的獨生子女政策,以人口總數作為唯一相關數據,執行時沒有考慮到總體人口結構、輿論或婦女生殖健康和權利。
這些都是《女性與中國革命》所揭示出的中國改革發展政策的缺陷。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的口號,「婦女可以撐起半邊天」,最初是毛澤東的一句名言。但事實上,那撐起半邊天中的許多人都無法獲得醫療、教育、工作、退休金等普遍權利,甚至無法獲得尊嚴和愛。
但女性還是憑藉才華和毅力,努力改變着她們的處境。好比農民工范雨素這樣的作家,她的作品的意義並不全來自於相對艱辛的經歷。相反,她的文字總是充滿語言的喜悅,這既要歸功於她勇敢的母親,也要歸功於她在北京皮村工人之家參加的文學課。
誠如筆者在《洛杉磯書評》中所指出的,范雨素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無能為力的小人物,而是一個擁有自由靈魂的堅強的人。她的好奇心促使她去理解、觀察和質疑周圍的世界。正如她寫道:「帝王將相和升斗小民都是同一個靈魂」,她寫的是家族的故事,是「關於平等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小說」。
從女性的角度來書寫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反思當代的問題,看看我們究竟取得了多大的進步,或者在哪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退步的影子。例如,1989 年的天安門抗議活動和隨之而來的大屠殺已經過去三十年了,但紀念方式仍然是保守的。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每年都在維多利亞公園組織燭光守夜活動,以保持記憶之火。但該組織在去年選出了一個全為男性的小組,似乎女性的抗爭是民主自由實現之後才飄忽而過的一絲青雲。正如香港記者伊拉里亞.瑪麗亞.薩拉(Ilaria Maria Sala)所言,沒有平權的民主並不是民主。這是在世界各地依然進行着民主抗爭的人們,都需要時刻自覺的東西。
關於女性的書面歷史遠少於男性,這一點不局限於中國。帶着這樣的意識去發現和記錄那些不被講述的、更豐富多元的故事,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更為重要。
- Gail Hershatter, 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 (Rowman & Littlefield, September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