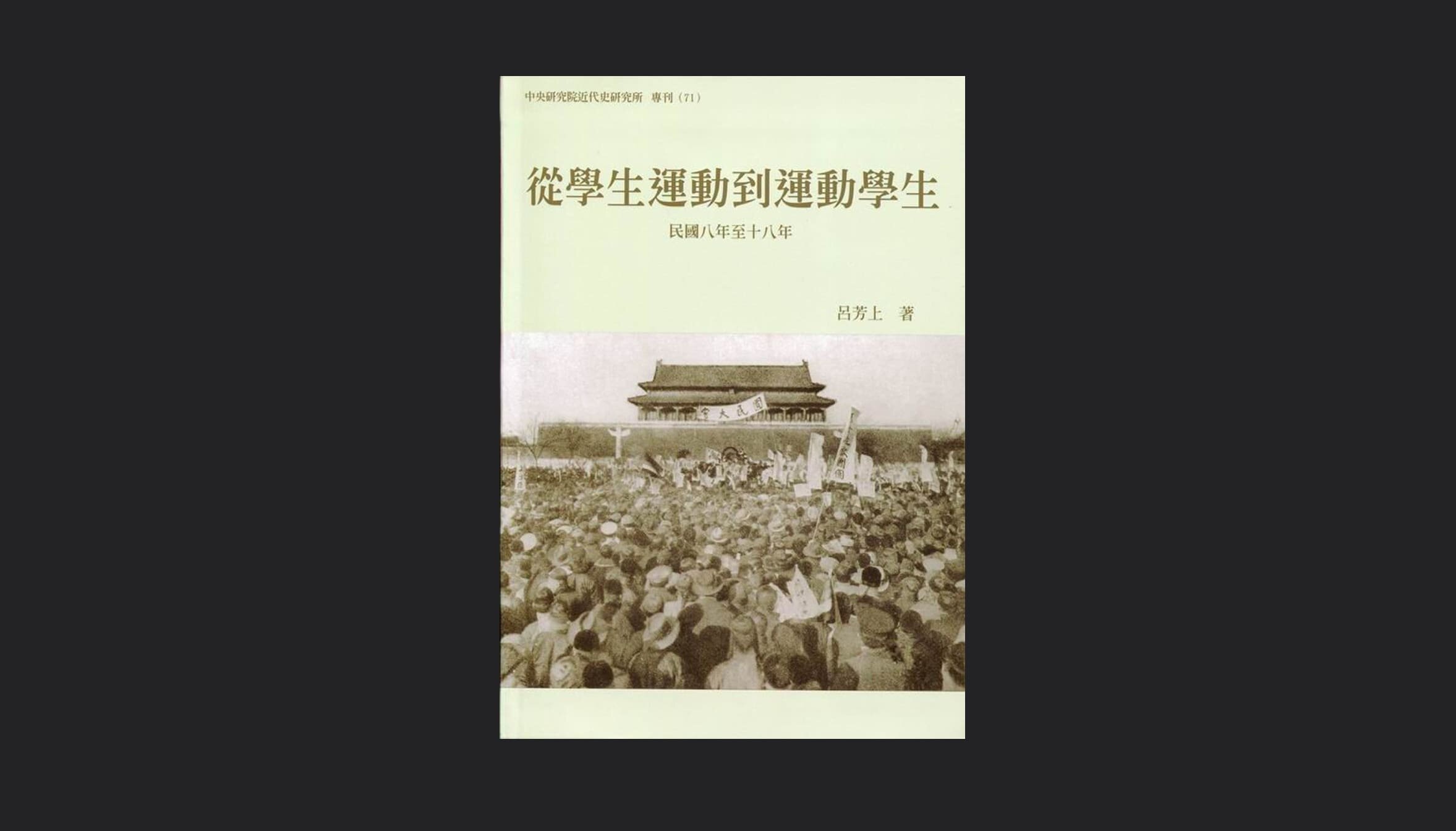去年(2014)春天,一場「太陽花學運」震撼了全國上下,迄今猶是餘音不絕。關於這場運動的認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國內外討論已多,本文無意另起爐灶作全面性的點評。本文要作的,是藉一本舊著新刊,省思「學生運動」的本質和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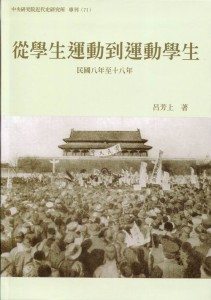
這本舊著新刊是呂芳上教授於1994年初版,今年(2015)再版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以下簡稱《學生》)。《學生》是嚴格意義上的學院式歷史學著作,史料豐富,論證嚴謹,自非「借古諷今」之作。但這並非意味,作者沒有深刻的「現實」情懷。原書初版序言謂:「從八○到九○年代,由北京天安門事件到臺北的三月學運,顯示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環境急遽變遷中,緊扣社會脈動的校園,也隨著產生極大的震盪。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面向社會,不能沒有時代的感觸和關懷」。從此可見一斑。
二十年後,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的變動巨輪並未停下,臺灣尤其走向國家認同的關口,波濤彼落此起。於是,《學生》於2015年再版發行,不能不令人想起臺灣餘燼未熄的太陽花學運,還有香港「雨傘革命」。《學生》再版序文即言:「學生運動有如一把不滅的火種,不同的時代,只要適時適溫,火苗一竄,便要星火燎原」,而「學運的議題可能變種不居,學運的本質和手法幾難二致」。學運的本質和手法是否幾難二致,當然是讀者可細細玩味的。
在介紹本書的內容以前,我們不妨先看看1990、2014年兩次臺灣學運共同反對對象--「國民黨」的形象。兩次運動皆身歷其事的范雲教授嘗言,「二十四年前的野百合運動,是在威權體制下希望為臺灣搶下民主。二十四年後,臺灣社會已經有了基本的民主,但此新生的民主卻面臨倒退危機,太陽花運動的努力,則是力抗不讓臺灣的民主被偷走。」
也就是說,國民黨被學生運動群體定性為一種保守的力量,甚至是與「進步」價值相抵觸的力量。站國民黨立場者,倘另有看法,應屬自然。但即使如此,許多國民黨人其實也意識到,反對者在所謂「進步」價值上提出的重大挑戰。例如,太陽花學運期間,流傳一封當時行政院長江宜樺夫人李淑珍的信函,提及目睹學運現場後的觀感,略謂:「在場靜坐群眾,幾乎全是大學生,而且個個眉清目秀、眼神堅定。相較於許多只關心追星打卡、吃喝玩樂的同儕,他們關心國事、勇於表達,顯然是年輕世代中的佼佼者。可以預見,在這一群人中,將會出現下一代的政治家、律師、學者、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
李淑珍說,「這裡坐著的是下一代的菁英」,這令她悲從中來。
相較於國民黨內若干一股腦兒「把學運推給反對黨」的言論,李淑珍能正視青年人心的歸向,應是可正面看待的。至少,筆者願相信她曾經一番下筆沈重。畢竟,這不是國民黨人第一次說類似的話。且不談1946至49年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窮於應付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坐令學運為共產黨在武裝鬥爭外的「第二條戰線」所利用。其實遠在1924年,亦即共產黨初建未久,尚屬襁褓嬰兒的年代,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便語重心長地說過:「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
今夕何夕,把文字中的「共產黨」替換成現今的反對力量,把「中國」改為「臺灣」,還是會讓人感到歷史女神開了國民黨一個玩笑。
數十年來,多數國民黨人對群眾運動認識不清,方法欠周,造成諸多惡劣影響,應有相當程度的事實。或者更確切地說,不論是在南京抑或臺北,國民黨人似乎總是有「站在學生運動對立面」的形象。然而,過份聚焦於國民黨對學運的舉措失當,很容易忽視一個事實:國民黨本身曾經是學生運動的弄潮兒。即令是前引的戴季陶的感言,也必須用此角度,方能適切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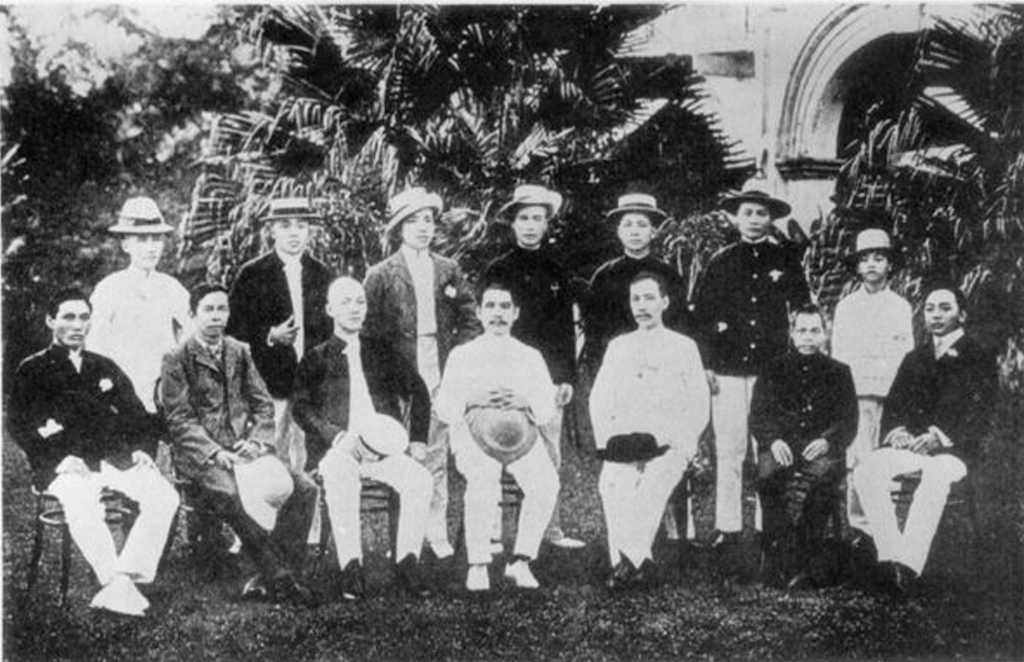
溯國民黨組織的前身,興中會、同盟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成員固不乏江湖豪俠、綠林好漢,但青年學生仍是當中重要的主體(特別是同盟會組織)。及清廷傾覆,民國肇建,有「清遺臣」吳慶坻、金梁等人編輯《辛亥殉難記》一書,詳列忠於清室、力抗革命黨人的「殉難」之士。
是書收錄前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著名經學家王先謙所寫序文,內稱:「推肇亂之由,自學校至軍屯,創立制度一以不教之民處之,列省奉行,糜金錢無算。其出洋留學者,復不加約束,以致流言朋興,莽戎潛伏,謀國不臧」。用白話文即是說:我大有為清政府之所以遭逢不測,原因出於未嚴加約束「學生」言行,造成政治、社會秩序大亂。
不意在一百年後,繼承革命團體家業的國民黨人,在臺灣已經失去了革命氣慨,也失去了「學生」人心。於是乎,國民黨人師承清遺臣的衣缽,接力指責「學生」的不是,當然用語隨時代會產生區別:「不教之民」變成了所謂「婉君」。
究其實質,國民黨(及其前身眾革命團體)從學生運動弄潮兒,變成在價值論述上否定學生運動,是一個發展過程。而這個過程是發人深省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號稱「成功」,但黨人並未藉此奪取政權,政權落於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軍人、官僚之手。自1912至1926年十多年間,黨人基本上是在野黨,除了數度掌控廣東地方政權外,缺乏挑戰北京中央政府(所謂「北洋政府」)的實力。
直到1920年代中期,國民黨借鑑蘇俄經驗,轉型為動員性的革命政黨,再搭配強調意識形態訓練的黨軍,始漸有問鼎中央政權的能力。經過曲折的統合過程,「國民革命軍北伐」終於在1926年夏天發動,打下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江山。
這時期,國民黨作為動員性革命政黨,又保持接近青年學生的傳統,與學運的關係極其密切。即使是在北伐軍事行動中,每有「學運世代」(借用現代的語言)成員擔任幕僚、政戰與宣傳人員,「持筆且從戎」。今天臺灣讀者熟悉的羅家倫先生,本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北伐戰爭期間便在蔣介石總司令部幕下服務。他們洋溢著革命情緒,深信國家的危難「實由於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之相互勾結」;他們所高喊的「打倒列強,除軍閥」口號,根本就是五四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直接傳承。
然而,自1927年下半年起,國民黨因北伐軍事的勝利,由「在野黨」向「執政黨」轉型,許多政策開始改弦更張,「穩健」的施政計劃取代了「激進」的革命話語,學生運動也因此有明顯轉折。
1928年6月,北伐軍開入北京,北洋政府覆滅。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於南京召開,自由派知識份子國民黨員蔡元培提出一個引人矚目的提案「取消青年運動」,內稱:「本黨之青年運動,則在運動學生,使犧牲其光陰,犧牲其課業,犧牲其學校之秩序。」值今北伐軍事結束,國家需要培養建設人材,如不及早籌謀,「十年二十年以後,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學業之不足以應世變,雖取吾輩之白骨而鞭之,豈足以償誤國誤黨之罪耶?」因此,「非停止往日之青年運動不可!」
蔡元培之議一提出,正反意見紛至沓來,贊成者多半是教育行政單位,反對者多半是學生組織及民眾團體,無法獲致結論。但基本上,國民黨之疏離學生運動,已是無可逆轉的現實了。
綜上所述,國民黨疏離學生運動的形象,應是始於1920年代晚期。1930年初,國民黨通過「學生團體組織原則」及「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終於明令限制學生不得與聞校政和涉入政治。於是,在「合法」的學生團體中,五四學生運動的意義和精神已經蕩然無存。
根據學者王奇生的研究,國民黨在大陸時期黨員群體的社會構成,除了軍人黨員外,始終主要集中於知識界;只不過,在國民黨於1928年取得中央政權後,一個趨勢是教師所佔比例增大,而學生所佔比例逐漸下降。其原因可能是在教育「黨化」的口號下,某些地方限制非黨人員從事教職,或者強制教師集體入黨。1920年代青年學生爭相入黨的情形已不復見,黨對富有革命激情的學生失去了吸引力。
國民黨之所以在取得政權之初,隨即疏離學生運動,原因是多方面的。《學生》一書的主軸,簡單說就是探討「五四」後十年中國學生運動的變化及其政治意涵。中國學生運動以學生自發性活動揭開序幕,以停學、罷課、請願、遊街、示威等手段,提出含括下至個人權益,上至政治、人權、教育、外交等項目的訴求。
但是,富理想色彩的學生「以極無責任之人,辦極有責任之事」,學運不能不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學生固然有知識,惟能力薄弱,又無經濟基礎,既擱不倒北洋政府,也逼退不了「帝國主義者」。他們若能獲致一點成果,多半還是要靠「各界」的同情與援助。適在此時,新興的動員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還有青年黨,抱著「誰有青年,誰有將來」的看法,逐步與學生接近,多方滲透學運,甚至操控了學運,終於使「學生運動變成了(政黨)運動學生」。

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從自主到喪失自主的過程,可以《學生》一書中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簡稱「學總」)為例。溯五四運動時期,各地青年學生為加強聯繫,擴大活動,相繼於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南京、杭州等大都會成立學生聯合會。及至1919年6月,各地學生團體進一步成立「學總」,作為串連全國學生力量的組織。一、二、三屆負責學總的理事,多無政治色彩,也不願和政治扯上關係。但是,學總的政治獨立性,在1921年以後逐漸失去。
是年7月,共產黨成立,注意佔領「機關」「團體」的重要,有意操縱學總的活動。未幾,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特設「青年部」作為領導青年學生的機關,很快就將學總收納入黨的青年運動組織中。然而,當時國民黨正值「聯俄容共」時期,許多具有共黨身份的「跨黨分子」,身居各級國民黨黨部的要職,包括青年部及其附屬機關。處此情境,國民黨「純正黨員」和「跨黨分子」之間,既有合作,亦有爭執。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勢必會波及學總的前途。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已受政治力介入的學總當即表態支持,各地學生也相繼響應。於是,北洋政府軍警動輒以「赤化」罪名逮捕學生,摧殘學運,學總只能更堅定地追隨「革命」陣營。不意革命陣營內部的左右翼之爭,亦已逐漸白熱化,大變繼起。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對峙,史稱「寧漢分裂」。處此情勢,學總左右翼遂分別在武漢、南京各開各的第九屆全國大會,交相指責對方是「偽學總」。7月,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決裂,不久垮台,武漢學總即告瓦解,負責人作鳥獸散。至於南京學總,雖能繼續存在,實已徹底失去了獨立性。這正是學生運動夾在政治運動下進行的最佳寫照。
面對政黨的介入,學生未必毫無自覺。《學生》指出,學生是否應涉入政治,在1920年代已是爭議性的話題。贊成者謂:一、青年是國家未來主人翁,所以對政治應有相當研究,但研究不如切實訓練好,故第一步應該加入政黨;二、政局杌隉,校園不安,欲改革教育先改良政治,改良政治目標在打倒軍閥官僚、打倒帝國主義;加入政黨,使目標得以實現。反對者則認為:一、青年人思想未固定,加入政黨乃一時之衝動,於黨義漠然,於黨於學生均無益處;二、青年時代應先打好學問根柢,再努力實際政治不晚;三、青年入黨,囿於黨義,喪失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於黨員責任又不能放棄,會造成荒學後果。
不可否認的是,學生加入政黨,加深了學運政治色彩,一不小心便栽入爭權奪利的現實世界中。《學生》認為,前揭蔡元培提案取消青年運動的說詞,是令人驚訝又不失坦白的話語,一語道破了五四以來學運變質的實情。不惟如是,政黨介入學生運動,或有其必然性,但也有令人難以忽視的負面效果。例如,「校園自主」、「學術獨立」,原是近代西方社會的觀念,傳統中國思想一向強調學問與入仕的關係,而發展中國家尤其很難奢侈地供養大批知識分子作「純粹的學術研究」。於是,學術為政治目標服務,校園滋長為政治的資源,是常見的事例。儘管學校依然是政治批評的主要來源,學生運動在許多場合確是促使國家進步的力量,惟弄到「教育為宣傳之工具,學校成結黨場所,學生充戰地之先鋒」的程度,顯然是一個壞現象,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隱憂。
事實上,《學生》一書所揭露的學生運動景象,對當代臺灣一般的「藍」、「綠」青年(如果可以這樣硬性區分的話)而言,是同感陌生的。
讀者也許想問,《學生》對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的斷語,是否合理?這部分,讀者自可從書中浩繁的史料引註找尋答案。惟對臺灣讀者來說,更大的疑問恐怕是:1920年代的中國歷史經驗,可否作為思索臺灣未來前景的靈感?對此,筆者仍舊是抱持肯定的答案。畢竟,歷史固然不會單純重演,但太陽底下確實不會有太多的新鮮事。
《學生》書內所描寫的,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訴求維護國權、改善人民生活,不同學運群體間的路線衝突,政府當局對學生運動的壓制,在野黨對學生運動的微妙關係,以及學生運動始終存在失去獨立性的質疑,對照當今臺灣的現狀,真令人有撫卷長嘆之慨,值得細細品味。當然,筆者並不主張,生硬地將舊日中國經驗套用在當今臺灣之上,淪為「借古諷今」者流。兩者的情境差異,在某些方面是很明顯的。例如,1920年代的國民黨、共產黨一方面試圖操弄群眾運動,但同時也正走向武裝奪權。而臺灣過去雖有軍事化政權的執政,確沒有軍人干政的傳統,今後更不該有任何政黨企圖假此手段。
其次,1920年代的群眾運動,正由五四時期的百花齊放、重視個人解放,轉向集體主義化的發展。這是國共兩黨革命奪權後走向「黨國體制」的重要關鍵。相較於此,當今臺灣已有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還有正在萌芽的多元價值觀。太陽花學運的爆發,曾引起社會各界對政治制度的焦慮與爭辯。但無論如何,筆者對政治體制、自由化、多元化的遠景仍深具信心,不相信臺灣政治走向「革命奪權」的回頭路。
筆者言盡於此,不擬再多作發揮,相信不同的讀者會另有不同的感懷。記得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友人,形容《學生》一書是「一部時代之作,每個人讀都各有體會」。誠哉斯言。不管我們對臺灣的未來有何看法,若願意用歷史的眼光來做點思考,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