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從大陸遷到臺灣時,攜帶了不少珍貴的檔案與文物,其中殷墟文物可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種,這些文物是「歷史與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於1928年至1937年間在河南安陽殷墟進行考古發掘出土的,現在史語所的意象「鹿紋」即是來自於「鹿方鼎」腹底的銘文。
此外,現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徽上也有七個甲骨文,說起這七個甲骨文,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圖片出處:歷史文物陳列館網站,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museum/tw/artifacts_detail.php?dc_id=10&class_plan=138
中央研究院從1928年創立以來都沒有院徽,過去曾有幾次提議院徽的建議,例如院長吳大猷(1907-2000)曾在1992年決定徵選院徽,並在《中央研究院週報》上刊登徵稿啟事,但議案擱置以至無法做成決議。直到1997年才在院長李遠哲(1936-)與副院長楊國樞(1933-)的帶動下積極籌劃院徽徵選,並在翌年舉辦徵選,共徵得29件作品,經主管座談會議選出4件進入複選,由院內職員進行投票決選。

圖片出處:不著撰人,〈院徽徵選公告〉,《中央研究院週報》,660期(臺北,1998),頁3-4。
編號一的圖案由一面方盾與彩帶組成,盾形圖案代表中央研究院學術地位崇高,盾內畫有電子運轉、雙螺旋、展開的書籍三個圖案,分別代表中研院的數理、生命、人文三個組。而方盾下方的彩帶上有三折,各折上分別有創新(Innovation)、卓越(Excellence)及真理(Truth)三句標語。
編號二的圖案由太極圖構思變化產生,從傳統出發演進為創新的現代感覺,象徵數理、生命與人文三大學科平衡發展,環環相扣,並均源自一個起始。而中心一點向外旋轉,亦可視為由外向內旋轉凝聚,象徵宇宙、生命與歷史精神的自然循環,生生不已。
編號三的圖案以「中」字做為設計的出發點,學術研究自由獨立有如手握巨筆,中央三槓並代表了數理、生命、人文社會三大學科平衡發展。
編號四無說明,但從圖案觀察,其概念與編號一類似,只是將盾改為門,並在外環加入六大領域的中文。
院方在各處所設置投票箱,經過了七天的投票後,總共發出1200張選票,最後收回了617張選票,其中有近六成的職員選擇了由鄭瑞芳女士所設計的編號1院徽,經過院長核定,並提交作者修改後正式成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徽。但是此院徽通行不到一年,就有倡議第二院徽的計畫,原因是通行後發現原設計圖因元素太多,縮小後效果欠佳,導致印名片時擠成一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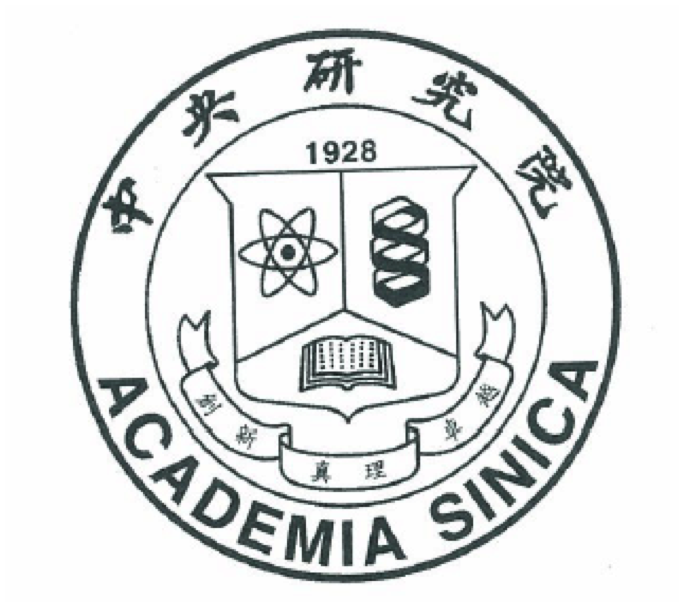
圖片出處:梁啟銘,〈院徽的故事〉,《中央研究院週報》,789(臺北,20008),頁8。
此外,還有幾個問題待解決,一是舊院徽在設計時外圈為藍色,白色的內圈背景,紅色的盾形及紅色的彩帶,後來核定後卻沒有正式宣示顏色,導致印製院徽時,各單位自行配色,造成不良的視覺效果。
二是舊院徽的螺旋體結構在〈院徽徵選公告〉的樣式中上下兩端是開放的,但通行的版本則改為封閉的,副院長楊祥發(1932-2007)指出應改回開口。
三是舊院徽中的中央研究院字體非蔡元培的字跡,有院內職員建議最好回歸蔡元培先生的原始手稿體,作為標準字體使用,因此決定嘗試重新設計第二院徽。

圖片出處:中央研究院網站,(網址:http://www.phys.sinica.edu.tw/images/sinica_logo.png)
通行至今的院徽就是後來院方將舊院徽簡化修正而成的第二院徽,此院徽的圖型仍維持鄭瑞芳女士的原創概念,只是去掉了彩帶,並將三組的象徵圖案改成重疊方式呈現。
最上面的是象徵生命的雙螺旋,其次是象徵數理的電子運轉圖,而象徵人文的書本被改為甲骨文,時任近史所研究員的謝國興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週報》的〈有關院徽設計的補充說明〉一文中指出:「甲骨文是現存最早的中國文字,文字是文化傳承與表現的重要元素,本院創始即設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即以研究甲骨文起家,甲骨文可視為漢學研究的原點。」

圖片出處:歷史文物陳列館網站(http://www.ihp.sinica.edu.tw/~museum/tw/exhibition_detail.php?dc_id=270&class_exhibion=162)
該甲骨文是採自中研院史語所博物館收藏的一塊鹿頭刻辭,上刻有十一個字:「已亥,王田於羌 ,在九月,隹王 。」根據考古學家董作賓(1895-1963)的解釋,意思是商王於九月已亥這天,在羌地田獵。謝國興先生請教時任史語所文字學組主任林素清先生後,選定其中七個字作為院徽上的甲骨文。
可是,第二院徽通行不久後,時任史語所研究員的柳立言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週報》上寫了一篇〈對院徽的淺見〉對甲骨文的意思提出質疑,觸發的動機,竟是某天其八歲的兒子突然問爸爸新院徽圖案的意義,柳立言先生當時也不能回答,後來查到了資料後,才發現其中大有問題。
文中提到:「聽說刻入院徽時犯了無心之失,故目前的甲骨文是有點錯誤的。我們已在短短兩年內換了兩個院徽,大抵在短期內很難再改了。那麼請至少告訴本院的同仁,那幾個甲骨文究竟說些甚麼,好讓我們回答子女朋友以至民眾的詢問吧。」
柳立言先生在文中暗指了院徽上的甲骨文存在兩點錯誤:一、甲骨文把破損的痕跡也當作筆畫了;二、從十一個字中挑選出來的七個甲骨文,並不能組成通順的意思,因此明知故問地詢問甲骨文的意思,頗有挖苦的意味。
時任中研院公共事務組主任的梁啟銘先生在同期的《中央研究院週報》,亦刊載一篇〈院徽的故事——答辯〉作為對柳立言先生的回應。文中指出他一開始還異想天開的想要在院徽上呈現「創新、真理、卓越」六字的甲骨文,但是甲骨文並沒有這幾個字,只好作罷。但梁啟銘先生並沒有直接回答柳立言先生的問題,只含糊的回答道:「後來我輾轉從朋友處得知,院徽這幾個甲骨文的含意,雖然不是『歌功頌德』,但也絕對不是『詛咒罵人』的字眼。」
梁啟銘先生當時故意不講明的原因是希望製造一個「求知高潮」,以後院內同仁年節聚餐時,也可當成獎猜謎的題目。並指出時任史語所研究員的袁國華先生亦曾建議改用幾個更有意涵的甲骨文字,院長李遠哲亦認為可以考慮。
兩週後,柳立言先生再於《中央研究院週報》刊載一篇〈甲骨文之謎——本院同仁2019年9月當選總統〉,首先公布了甲骨文的字義,院徽上右邊三個是「己亥王」,左邊四個是「九月唯王」。其次表示七個甲骨文,只有三個字刻對,其餘的都把原件上的破損痕跡當作筆畫刻入院徽。至於這無實際意義的七個字,柳立言先生則打趣的表示,甲骨可用來占卜,因此「己亥王,九月唯王」,似乎是預言中研院有同仁在2019年(己亥)9月當選總統。
謝國興先生亦在同期中刊載一篇〈再談院徽甲骨文〉對甲骨文的問題做進一步的解釋,指出起初選擇甲骨文字時,誠如梁啟銘先生所言,確實曾考慮兼顧字義,但由於甲骨文多為祀戎之事,因此在執行上有其困難。李遠哲院長亦曾半開玩笑說:「只要選用的字不是殺人放火之類就好。」只好退而求其次,僅將甲骨文作為象徵意涵的圖案使用,不再拘泥於字義。
故在最後設計時,以結構簡單、易於辨識為標準,嘗試了幾組圖案之後,認為「己亥王,九月唯王」的排列方式,對於第三層的整體構圖與視覺效果是最佳的。此外,謝國興先生亦表示:「院徽中的這幾個甲骨文字是以電腦圖檔的方式處理,是『圖案使用』的思考邏輯,應該沒有『刻對』、『刻錯』的問題,也不會有學術考證與愧對古人的問題。」
因此,柳立言先生提出的字義與誤刻兩個問題在此都得到了解答,院徽的甲骨文討論便在此結束了。只是謝國興先生打趣的說,萬一2019年真的有院內同仁當選總統,屆時還可以去找梁啟銘先生領獎。問題是……2019年並沒有要選總統呀!
後記:感謝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提供《中央研究院通訊》。
- 不著撰人,〈院徽徵選公告〉,《中央研究院週報》,660(臺北,1998)。
- 不著撰人,〈辦理院徽甄選投票統計結果〉,《中央研究院週報》,662(臺北,1998)。
- 梁啟銘,〈院徽的故事〉,《中央研究院週報》,789(臺北,2000)。
- 謝國興,〈有關院徽設計的補充說明〉,《中央研究院週報》,790(臺北,2000)。
- 柳立言,〈對院徽的淺見〉,《中央研究院週報》,790(臺北,2000)。
- 梁啟銘,〈院徽的故事——答辯〉,《中央研究院週報》,790(臺北,2000)。
- 柳立言,〈甲骨文之謎——本院同仁2019年9月當選總統〉,《中央研究院週報》,792期(臺北,2000)。
- 謝國興,〈再談院徽甲骨文〉,《中央研究院週報》,792(臺北,2000)。
- 杜正勝主編,《來自碧落與黃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文物精選錄》,臺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