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的父親是一位記者,而您早年也從事記者的工作,我這樣說正確嗎?
答:正確。
問:您辭去記者的工作是為了成為在大學中任教的學者。但在某方面上,就您對新聞媒體的興趣,或可稱之為您的副業來說,您仍然與新聞界有所關連。您認為您的興趣是源於早年的職業嗎?從事新聞業的經歷對您有著什麼樣的影響?
答:嗯,的確有影響。但對我來說,究竟這個經歷是怎麼樣影響我,則是難以解釋,也難以理解的。部分原因是心理上的,因為我的父親在二次大戰中身亡。他當時是紐約時報的特派員。而我應該要繼承他的遺志,也就是說,成為紐約時報記者的一員。我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想要一展成為記者的抱負,我並不是指編輯或專欄作家,而是人們所稱的那種西裝革履,穿著風衣、叼根香菸,在帽子上插著記者證的傢伙,也就是那種在街頭尋找報導題材的新聞記者。回想起來,這幅景象還真是摻雜了些許浪漫色彩。不過我們家中每個人都是記者,從我父親、母親到我弟弟…
問:您母親也是一位記者?
答:是的。在我父親過世之後她也進入紐約時報,一路從記者做到婦女專欄編輯,隨後成立了一間通訊社:國家婦女通訊社(Women’s National News Service)。
問:她還活著嗎?
答:不。她在1968年去世了。
問:那你的弟弟呢?
答:我的弟弟約翰,他是個頂尖的記者,同樣任職於紐約時報。我們一家四口都為紐約時報工作。我四歲的時候就接到我在紐時的第一份工作。當然我當時還不會寫字,不過麥克.伯格(Mike Berger),紐時的一位記者,同時也是我們家的世交,在 1943 年帶我到華盛頓旅遊,並錄下我近乎嬰兒牙牙學語般的童言稚語。當時這個報導的構想,是透過一個四歲小孩的觀點看戰時的華盛頓,就像是國王新衣寓言的情節。因此,我漸漸覺得我注定要成為一個記者。所以當我離開紐約時報時,我的感觸很深。我成了家中的異類:一個大學教授!當你可能成為記者時,你又怎能想像未來會是如此的光景。
經常有人問我為何要離開新聞界,答案很簡單,就只是因為我喜愛歷史研究。而這是一份困難的工作。不過研究寫作雖然是一種煎熬,卻極有成就感。我在新聞界從業的經驗,和我所從事的歷史研究顯然有一些關聯,譬如我研究新聞史。然而我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都尚未出版。還有我曾在一家大報受過基本訓練,在社會版報導謀殺、搶劫等等…
問:是在哪一家報社?
答:《紐華克星定報》(The Newark Star Ledger),在紐澤西州的紐華克市,那是個高犯罪率的城市。我就是在那裡接受記者的基本訓練,主要是在警局。當時是 1959 年。後來我在曼哈頓、皇后區和布魯克林的警局中工作。因此我寫過許多犯罪故事報導…。
問:這是從 1960 年的時候開始的嗎?
答:嗯,從我大學時候就開始了。不過我以前就有在報社打工,甚至從國中的時候就有,那時我差不多十二、三歲。我在 1952 到 1953 年間為康乃迪克州西港鎮(Westport)的一份週報,撰寫一個叫做「貝德福青年要聞」(Bedford Junior Highlights)的專欄。我在這個小鎮中度過了大部分的童年時光。之後我在紐華克接受新兵訓練,訓練結束後,我在紐約時報的週日新聞部待了一個暑假。後來我在哈佛大學完成學士學業,並獲得牛津大學獎學金負笈英國。在那裡我還擔任紐約時報的兼任通訊員,放假時則在紐時的倫敦分社當代理通訊員,還有…
問:這是 1960 年的事嗎?
答:沒錯,一直到 1964 年。我在 1964 年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後就到紐時擔任記者的工作,重操舊業報導謀殺和持械搶劫。那時我至少已經學到如何快速而精確地撰寫我的報導,並養成了一種我奉行一生的態度,那就是尊重讀者。
當然讀者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群體,但他們可能比大多數大學教授所認為的更加聰明。我不認為作家應該遷就一般大眾的口味,但我們(歷史學家)應該以平易近人的筆觸寫作,不賣弄學術術語,面對事實更應秉筆直書。
然而正如同我剛才說過的,現在我們已經明白,所謂的事實在相當程度上只能是再現。不過在撰寫報導時,你必須要知道被害人姓名的正確拼法、年紀與住址,而且要能將資訊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一絲一毫也馬虎不得。假如報導有誤,那麼當你被社會新聞編輯叫去辦公室時,你的皮就得繃緊了。跑上幾個月的犯罪新聞會使大多數的研究生大開眼界。
以我為例,這個經驗導致我對輿論和媒體產生莫大的興趣。我的學術興趣,最開始是在哲學和傳統的思想史領域,而隨著研究的進展,我也嘗試處理在底層社會中,思想和觀念傳播的問題。我想要創造一個叫做觀念的社會史的領域(這是Alphonse Dupront的用詞),並且,套句 1960 年代流行的術語,「從底層的角度」(from below)寫作智識史。
我對哲學體系在哲學家之間的遞嬗關係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的興趣,是想了解一般人如何將他們生活周遭的世界理出頭緒、賦予情感,以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用知識,是如何在社會中傳遞的,而這些知識又是如何形成他們應付周遭環境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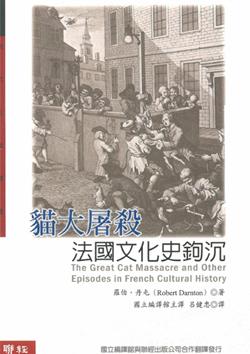
對我來說,一般庶民百姓其實是很聰明的,只不過他們不是知識份子罷了。因此,為什麼不試著寫作一種非知識份子的智識史──或者,假如你喜歡的話,稱做心態史也未嘗不可。不過這種歷史關注的不是社會結構的決定性影響,而是意義形成的過程。
我的這種研究方法,可能和我以前的工作經驗有關。在擔任報社記者時,我的工作就是訪問、報導,並捫心自問一個任何社會新聞編輯和記者,在提筆之際都會想到的基本問題:「何謂報導?」你在報紙中讀到的東西,並不真的就是發生的事情,而是有關發生的事情的報導。
我認為新聞的敘事杜撰性質,一直沒有被好好的研究,而這正是一般訊息傳播史研究的核心部分。究竟根植於文化傳統中的敘事方式,如何形塑資訊的傳遞、影響輿論的形成,甚至在何種程度上構成了人們的世界觀?
我過去任職記者的經驗,對我歷史研究第三種可能的影響,則是和警察有關。我曾在好幾個警局中待過很長的時間,不消說我當然對警察檔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現在仍不斷進行警察檔案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理解文學史的幾個面向,諸如作家的社會地位、文人生涯的本質、出版檢查以及書籍的流通,甚至是書籍對警察所稱之「公共精神」(l’ esprit public)的影響。
但這並不是說我相信警察檔案的記載都是真實的,剛好相反,在與偵探和警官相處過這麼長一段時間之後,我體認到他們並不總是可信。雖然警察檔案中必然有主觀的成分,但我們仍然可以利用警方蒐集的資料,研究書籍交易的遊戲規則,以及這些規則和檢查制度之間互動的關係,同時也可以確認文化的傳播者,及其在出版業和文人共和國的派系政治中運作的模式,更可以藉由口傳和印刷的媒介,追尋知識擴散普及的蹤跡。
在基本的層面上,我們可以找出當時究竟有多少文人作家,他們都住在什麼地方,長什麼模樣,性生活又是如何等等。這些檔案的可能性是無限的,但歷史學家幾乎未曾好好利用過。
問:所以您的著作大多與18世紀的法國有關。究竟為何您會對這方面產生興趣呢?
答:老實說,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作為一個身處二十世紀末的美國人卻著迷於十八世紀的法國,這或許是有些古怪,不過雖然我熱愛法國及其人民,我主要的興趣卻不在法國史。只是法國史領域,有豐富的檔案資料以及歷史著作,對於我興趣所在的研究主旨和問題都極有幫助。
法國是第一個警察國家。「警察」一詞在十八世紀的意義是現代、理性的國家行政措施。而警察在執行工作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文件。在這些文件的扉頁上,間諜、警官和警察總監的潦草字跡,至今猶可辨識。這些文件資料浩如煙海,塞在數不盡的箱子中,堆滿了檔案室。打開國家檔案處或阿色那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 Arsenal)中的一個箱子,就像是踏進了另一個世界,你永遠也不知道你將會發現什麼。
在其中的一個箱子中,我發現了警方線民有關 1726 和 1729 年之間,在 29 間咖啡館中談話記錄的報告。這就彷彿漫步在將近三百年前的巴黎街頭,耳中縈繞著城市的喃喃私語。這些報告不能照字面解讀,因為其中蘊含了線民的主觀偏見。
法國的檔案就像個巨大的實驗室,在其中可以測試一些棘手的概念問題,例如輿論的本質之類的問題。我對這些問題要比對法國史本身更有興趣。
問:您在您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您有幸走進一個歷史學家的夢幻天堂,即一堆尚未被發掘的寶貴資料,也就是瑞士紐莎泰印刷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簡稱STN)的檔案。這是有十八世紀印刷公司檔案,留存至今的唯一記錄。而正是因為有這些檔案,您才得以完成那部出色的百科全書出版史。我想知道您是否曾想過,假設您並未發現這個夢幻天堂,您的命運將會是如何?STN 檔案在成就您今日學術地位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答:嗯…猜想未曾發生過的事並不容易。確實我大部分的學術生涯,都是在挖掘這些豐富異常的檔案:五萬封信與帳簿,還有各式各樣的文件。我對18世紀全部的感受,都是得自於積年累月浸淫在這些檔案中的結果。如果我從未發現這些檔案,我不確定我的人生將會往哪個方向走…
問:這是你第一次著手…
答:嗯…我在開始研究這些檔案前就出版過一本談催眠術的專書。
問:是您的博士論文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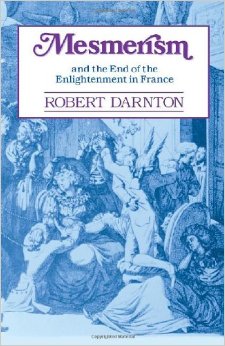
不是,我從未出版我的博士論文。這是一本有關科學史,特別是通俗科學的書,同時也是對當時在法國開展的心態史研究的一個嘗試,儘管我當時尚未與我的法國朋友們展開合作關係。
這本書研究大革命前夕法國人觀看世界的方式,以在大革命前巴黎流行的動物磁性學,或稱催眠術(Mesmerism)為例,探討此一在當時深具魅力的風潮對人們世界觀的影響,及其如何與各式各樣的激進政治思想沾上關係。所以我可能已經在心態史的領域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事實上,《貓的大屠殺》一書延續了這個研究的主軸,如果不是埋首於 STN 檔案之中的話,我將會持續這個研究。
問:你是如何發現這個(STN)檔案的?
答:1963 年我正在牛津大學寫我的博士論文,一本瑞士著作中的一個註釋,讓我想到在瑞士紐莎泰的圖書館中可能藏有雅克—皮耶‧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的原始信件。這個人便是大革命時「布里索派」(Brissotin),或稱吉倫特(Girondin)派的首領。他身為一位在1780年代,熱衷於和美國獨立革命相關之一切事物的眾多法國人之一,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在 1962 年寫了一篇談論他,和他在一個名叫「法 — 美協會」(Société Gallo—Américaine)的激進團體中黨徒的文章,做為我在牛津大學的 B. Phil. 論文,而我還想在博士論文中對布里索做進一步研究,於是我想說不過花點郵票的錢,乾脆寫封信問紐莎泰圖書館:「你們可能有任何布里索的信件嗎?」
圖書館長回信說他們有 119 封信,其中一封是照片存檔。這封信是 1784 年布里索從巴士底出獄後寫的。在信中他描述了他的悲慘遭遇,從他的作家生涯談到他的出版社,也就是 STN,以解釋他為什麼付不出錢來。牢獄之災毀了他,他因為在瑞士出版許多著作,而欠了瑞士出版商一大筆錢。
這些信件中鉅細靡遺,彷彿歷歷在目地呈現文學史的諸般面向,令我感到驚喜萬分。所以我馬上把握機會,決定前往紐莎泰閱讀這些信件。
問:這些信件全都放在那兒嗎?
答:完好如初。一位名叫約翰.讓普耶(John Jeanprêtre)的退休化學家將他人生的最後幾年,都花在把這五萬封信分類做成目錄的工作上,這些信都保持完好無缺。
然而,當時我又回到紐約時報,繼續報導性侵害和謀殺案件。後來幸虧我之前在哈佛的老師亞瑟‧施列辛格二世(Arthur Schlesinger, Jr.)伸出援手,哈佛大學提供我一個研究工作,也就是所謂的「青年研究員」(Junior fellowship)。於是我辭去紐約時報的工作,搬到哈佛,並在最短的時間內動身前往瑞士紐莎泰。
如我所料,這些信都還在那兒。119 封布里索的信之外,還有我前所未聞,總數高達五萬封的各式各樣信件。這些信的作者乃是出版業的圈內人:活字鑄造工人、印刷工、造紙工、書籍走私販子、書商、書籍小販、作者、讀者──就像是個未知的世界,等待著歷史學家的發掘。
而我就如原先計畫好的那樣,從撰寫布里索的傳記開始我的研究。但寫了 500 頁的草稿之後我決定放棄,因為我認為寫一本書的傳記,要比寫布里索的傳記來得更有意義。因此這些草稿至今還躺在一個抽屜裡,從未出版。而我所寫的傳記,就是《百科全書》的研究。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接觸到了大量有關盜版、商業競爭、商業間諜、陰謀詭計、地下交易等各式各樣的資料,我的研究因此就變成了偵探故事 ― 或者說,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像回到了之前的犯罪報導一樣 ― 牽涉了真實的犯罪和規模龐大的詐欺。我試著在一本關於最重要的啟蒙運動作品生產和流通的著作中,陳述這個有血有肉的故事。
.jpeg)
本書還選譯針對「新文化史」研究進行反思的文稿,該文是首次以翻譯形式在原產地境外的國家發表,這是本編的一大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