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 4 月以降,孫中山的遺體一直安放在北京城外西山的一個廟宇中。孫早於 1895 年已相信南京的中央位置是統一全國的關鍵要素,故其靈柩亦祈能永久安葬該地。後來軍閥內亂結束,孫中山的遺體便運往南京。
在南京城外紫金山宏偉的紀念堂中,他可以凝望新政府的一切,包括統一全國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各項措施。在孫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守護神的新角色下,他過往的不足與自相矛盾早已被遺忘。孫中山由這個尊貴的安息地所產生的影響力,比他以前在這城市中所經營的革命活動還要大。
是年 6 月 1 日,連珠槍響打破黎明的沉寂,向沿着中山路聚集數以千計的人們正式宣佈,對孫作最後致敬的儀式已經開始。長達兩里的行列隊伍步離南京,這個隊伍由士兵、各個工會代表及男女童軍組成,另外亦有許多非正式的弔唁者站在路邊,而沿馬路邊都拉起繩索,由士兵警衛,不許人們越過。士兵都很清楚自己身負重任,要讓今天的活動順利完成,因此一直高度戒備,手指從沒有離開過步槍的扳掣。
群眾注視着行列中各個隊伍安靜經過,他們的耐心終於得到回報,終於一睹靈車上巨大而造工精細的棺木。靈車後面是孫夫人、她的弟弟宋子文、她的妹妹與蔣介石、孫科及其夫人、胡漢民,還有這位逝去領袖的其他戰友。所有人的衣着都十分簡單,一律是樸素的白色。靈車拖着藍白相間的繩索,繩索後是各國的外交團成員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逾 4 小時後,大約是 10 時半,靈車抵達紫金山山腳,亦即孫中山安息之地。負責主祭的人早在南京城外換乘汽車到達,重新排成隊伍,拾級而上。挑夫將棺木移往一個巨大擔架,旁邊是藍白相間的挑擔。挑夫從山腳抬棺而上,動作緩慢而吃力,這時候主祭者在前面引導。上山大約要半小時,樂隊亦沿山而上,奏着特別為這次喪禮而譜的輓歌,打破山上的寂靜。挑夫隊伍由 16 人組成,各個致祭者亦不時出手攙扶,隊伍後是一群平民及非官方弔唁者。
在致祭者中,有一群令人矚目的日本人,當中兩位年紀較長的外貌尤其突出。在紀念堂最後的儀式中,其中一位日本人站在蔣介石的身旁,反映出其受禮遇的身份。
參加葬禮的人大都沒有注意到這兩位日本人及他們的同伴的身份,事實上他們能在葬禮上佔一席位正是亞洲主義的證明。在孫中山生前曾投入過、奮鬥過的各理想中,亞洲主義居重要部分。
雖然日本一面呼喊亞細亞口號,一面在中國進行殺戮,使得這些口號為人唾棄。可是這些想法對孫中山而言,並不僅止於口號。日本人曾景仰他,並與他結盟,並肩作戰,這一切都與亞洲主義密不可分。在孫的革命奮鬥過程中,他從沒有忽視日本人援助的重要性。他曾寫道:「我們一定要讓中國革命官方歷史詳細記下日本友人的無價貢獻。」站在紀念碑前兩位滿頭白髮的日本人,是當中貢獻最大的。
74 歲的頭山滿,在日本人領導及啟發下的亞洲團結運動中,一直堅持不懈推動了逾半世紀。不過他們的精神追隨者卻懷抱着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無法視中國為平等夥伴。而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與他們同處在一個相同環境中,亦不肯接受屈居人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頭山滿只能在個人層面上交到一些親密的中國朋友。他雖然資助孫中山的事業,卻無法阻止孫於日後接受蘇聯的救濟。
在孫中山過世後,其所留下的反帝國主義事業,反而引發與頭山滿追隨者政策的尖銳衝突。蔣介石亦曾接受過頭山滿的幫忙,但卻不滿一年前日本人妨礙其北伐事業。蔣的妻子曾在美國接受教育,受此影響,他似乎缺乏頭山滿所認定,以亞洲道德及目標為長處的東方領袖資格。
同是年屆 74 歲的犬養毅是個備受人民擁戴的國會議員,他一生都在為日本的代議政治奮鬥。跟頭山滿及孫中山一樣,他意識到亞洲團結的重要性,因此一有機會便大張撻伐日本政府的親西方傾向,與及其受日英同盟主導的政策。犬養曾認為孫中山是個志同道合的亞洲主義者,因孫接受及感謝日本援助的同時,通常亦接受日本解釋其侵略行為是不得已,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的共同敵人──不長進的中國政府,多於日本擴張主義。

犬養曾是孫中山的忠實支持者,在孫革命過程不得意的時候,他說服日本政府,不要讓孫中山太難堪,同時亦經常對孫作庇護。在孫中山革命事業得意的時候,犬養亦繼續幫忙,派人進行調查,以助革命之發展。犬養毅在 1932 年曾總結其對孫中山的感情:
在 1911 年,犬養與頭山曾一起到中國,同行還有第三位大鬍子,宮崎寅藏(滔天)。在孫的葬禮,宮崎由兒子及好友萱野長知作代表。孫與宮崎家與萱野為至交。二人的思想接近英國著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而實踐方法則取自美國經濟學家亨利 A 喬治(Henry George)。他們的行為比日本官吏的說話更能為日本的錯誤贖罪。
中國民族主義者與日本擴張主義者的合作固然有點不可思議,但在日本弔唁團那一小撮人中,各個政治光譜所代表的分歧則更令人訝異。頭山滿代表日本武士道精神及舊日本道德的傳承者,他認為自己是德川時期攘夷志士的現代化身,立志要延續及發揚最後一個封建武士西鄉隆盛的使命。
宮崎則成長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反抗傳統中,他對西方帝國主義感到恐懼、就西方自由主義的發表及為初期農村社會主義爭辯,在各種思想交錯影響下,使宮崎成為一個農民激進主義及東方傳統主義不穩定的混合體。

犬養則代表反對寡頭政治及貪得無厭的西方之中的第三條道路,選擇了代議政治。事實上他是推動議會選舉的第一代老將,但由於明治日本初期自由主義的先天缺陷,犬養的團體在反抗政府的時候,不得不愈來愈倚賴民族主義情緒。同時明治日本在政治教育及經驗不足夠,犬養的政黨漸為工業勢力所控制,結果為工業家所利用,迫使政府擴張,好讓商業利益深入到鄰國的土地上。
上述三股勢力之所以能夠合作,主要是有共同的國外及國內敵人,即西方帝國主義及國內的鎮壓。當敵人愈強,他們的合作便愈緊密;若相反,則彼此間關係愈趨於疏遠。孫中山與這些團體最親密的時期是在明治期間,到 1929 年,雖然個別代表間的友情或許仍然維持,但日本的三個團體已無法再合作下去。
宮崎的早逝象徵其團體的衰落,事實上它是最不穩定,亦是最早出現混亂的一群。早期的農民激進者要作出抉擇,若不是退出政壇,便是要把團體轉化為國會黨派,與其他代表相類似的商業利益的對手,進行彼此間的競爭。宮崎、大井憲太郎與及他們其他進入亞洲大陸冒險的同伴大概都選擇第一條路。
犬養一派與頭山民族主義派的合作亦告終結,因為當日本力量上升後,外交問題已非關注重點。犬養及頭山反而為了普選問題,各自站在不同陣營。普選很早便是議題,到 1925 年日本正式立法。在 1932 年犬養在選舉中獲勝,他自認熟悉中國事務,承諾選民會去實行一個堅定中國政策。不久,犬養被一些反對整個國會選舉制度的年輕海軍軍人行刺送命。對這些軍人而言,犬養及頭山均冒犯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威,與明治那些寡頭政治家沒有分別。
換言之,上述團體能夠合作只不過是存在共同敵人,他們追求的目標並不一致,他們對亞細亞的目標亦各有自己看法。他們可以幫助孫中山推行革命,但是當革命一旦成功,他們卻無法聯合一起幫助孫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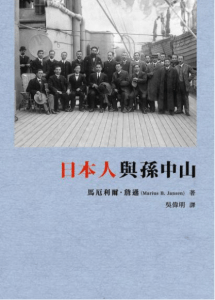
本書追溯這些日本人與孫中山合作的經過,其合作的唯一恆久結果則是彼此建立的友誼,這友誼令他們在 1929 年受邀出席南京的葬禮。雖然如此,就中日關係而言,它仍是十分重要的一章。當中國民族主義者與日本民族主義者轉為仇讎時,雙方都後悔昔日的親密交往。除了宮崎寅藏這一群人,大部分日本人都認為中國人忘恩負義,不值得結交。另一方面,當中國人回顧二十世紀初所發生的一切,則認為日本人一早居心不良,準備侵略中國。
無論你是否接受兩者其中之一的解釋,或者要尋找第三個說法,中國及日本這群朋友所做的一切,都絕對有敍述的價值。故事裏的各個主人翁都是熱心活動家,充滿傳奇性,引人無限想像。近代中國的共和主義及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大家一直關注的歷史事件,這個故事亦可以從旁呈現兩者的發展過程。孫中山與日本人交往過程中,在二十世紀初是一個惺惺相惜的夥伴關係。不過當中國民族主義及日本國力逐步發展時,雙方便漸行漸遠。最後當孫中山要求日本人助其反袁世凱時,雙方關係變得絕望。
(本文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美國的日本史和中日關係史大師。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師從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和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自1959年起至 1992 年退休為止一直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並於 1969 年在普大創立東亞研究學系及擔任首任主任。代表作包括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1954)、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1961)、Japan and Its World: Two Centuries of Change(1975)、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1975)、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1992)及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2000)等。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博士,詹遜關門弟子。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並兼任文學院副院長、日本研究學系系主任及比較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專攻中日思想文化史、旁及港日關係史及日本流行文化。近年研究以德川時代的中國人傳說、明治易學及港日文化交流為重點。新近著作包括《德川日本的中國想像》(2015)、《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2015)、《在日本尋找中國》(2013)、《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2009)等。譯有《德川日本》(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