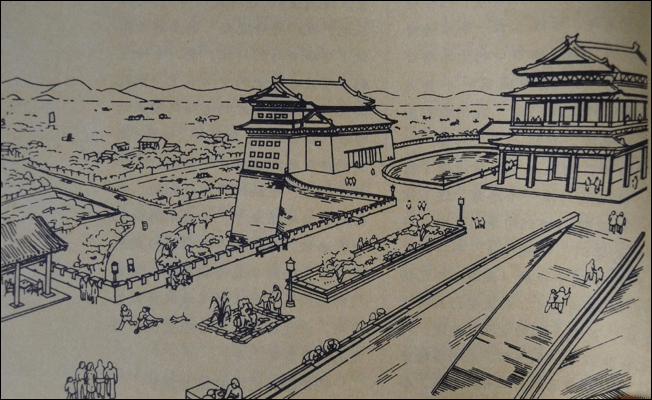很多時候,對舊物的珍惜並不是執著物質擁有本身,而是對製造者的感激,對「擁有」的鄭重,以及透過人與舊物的關系所生成的更廣闊的存在和時間。這份鄭重和珍重超越了物品本身,而對人和歷史的理解及同情。
留學英國這些年,不少人對我幫助和影響都極大,而與他們的相識也圍繞舊物。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傳奇的老人。
他在愛丁堡的華人圈子裡聲名遠傳,因為雖然不通中文但非常樂意與華人學生來往,熱心的幫助了好幾批往來學子。為了讓學生對蘇格蘭文化有較為直觀的瞭解,他甚至自掏腰包買燕麥餅、乳酪、羊雜碎(haggis)、蔬菜,煮了一大鍋薯泥(mashed potatoes)和蘇格蘭著名的“haggis, neeps and tatties”(羊雜碎蕪菁泥),真誠得讓人感動。
幾年前的一天老先生家的屋子年久失修,天花板突然坍塌,平添許多需要修整的地方。作為平日受到他照顧的學生之一,我自告奮勇前往幫忙,也藉此機會,得知了許多動人心弦,取向悠長的故事。
1913 年,蘇格蘭。修華的外祖父母由首府愛丁堡的五月花教會出發,搭船前往中國東北。在他們當時的禱告裏,可能不會念及囹圄:在侍奉異鄉的教會廿多年後二戰爆發,這對夫婦作爲異鄉客,被異鄉的入侵者投入大牢。
他們的女兒,也就是修華的母親,在山東煙臺出生長大,當時剛回到英國升學,因爲戰爭的緣故與修華的外祖父母斷了音訊。從監獄逃生後,修華的外祖母便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尋女路。她從瀋陽出發,至西伯利亞搭火車上西伯利亞大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穿越沙俄,回到歐洲。確定女兒身在愛丁堡且安然無恙後,又計劃輾轉再回中國。因爲事工未完。
回程坐船。她從愛丁堡坐火車到鄰城格拉斯哥(Glasgow),從那裏登船橫跨大西洋,停泊於加拿大東岸,再從卑詩省坐橫貫大陸鐵路(Trans-American railway)。最後,求一名大副帶她搭船跨太平洋,回到中國。
就在修華的外祖母為女兒與教會冒著生命危險翻山越海的時候,修華的父親,一名同樣被日軍捕獲的蘇格蘭年輕人,正被日軍抓了在南亞建桂河鐵路(Kwai railway, 電影《桂河大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中的歷史原型),私下偷偷挖地道預備逃跑;不料空襲的炸彈在他身邊炸開,地道幾乎成墳墓。
修華的父親奇跡般的活了下來,流亡至馬來西亞,並從那裏白手起家。
1947 年。戰後的蘇格蘭,修華的父親和母親,一對曾在異鄉逃生的年輕人在五月花教會相遇。相似的經歷與價值觀讓兩人一見如故;於是,像所有苦盡甘來的故事那樣,一見鍾情的二人很快在五月花教會舉行了婚禮。新婚佳偶回到吉隆坡,修華就在那裏出生。
基於對家族先輩的獨特經歷,很多年後,他給自己取了個意味深長的中文名字:修華。像大部分英國老人那樣,修華珍視歷史和所有從歷史流傳的物件,尤其是先輩們從亞洲帶回來的古董或小玩意。哪怕是一盞五顔六色的紙燈籠,他也珍藏至今,只因兒時在海灘上赤足奔跑時所見的明媚顔色,是曾經點亮回家路的光。他的先輩以「外邦人」的身份進入中國的土地,卻肩負向對基督教信仰而言是「外邦人」的中國人傳播福音的任務。曾經是異邦的流亡者,他們之後卻把異邦視作家鄉。「外邦人」Gentiles,拉丁文中種族/歸屬意,又特指非猶太教徒(未受割禮);而在聖經新約《以弗所書》中,保儸對外邦人傳教,告訴他們即便是外邦非猶太人,只要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便得以與猶太人同為耶穌後嗣,與神子同為一體,同蒙神的應許。身體和物理上的區別乃塵世面具,心靈的歸屬感才可作人的界定。
是五月花差遣他的外祖父母去遠東,結果二人幾乎爲此喪命;然而奉此差命半個世紀後,他們的女兒在這家教會遇見了擁有同樣傳奇經歷的良緣並攜手終生,好似是他們用生命去信奉的上主通過五月花教會在補償他們曾經的艱辛。
「還記得馬來西亞嗎?」我從滿屋的雜亂陳年貨中揀出那臺鐘和那只碗問他。那一年修華家的舊宅因爲年久失修,廚房的天花板突然坍塌,他不得不將所有舊貨集中整理。而我出於對舊貨的熱愛和天生的八卦雷達,自告奮勇去幫手。
「記得。雨水落在屋頂上的聲音,滴落到身上沁涼。一直到現在,有一次家裏漏雨,我還以爲是夢回了馬來。」
大約在公元 67 年,幾乎半本新約的作者,使徒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捕,並被押往羅馬受審,在那裏殉道。他生前踏遍歐,亞,非三洲,去到安提阿,塞浦路斯,馬其頓……不念性命,廣建教會,被認爲是早期基督教最有影響力的領導者之一。像修華的外祖父母那樣,保羅亦終生致力向外邦人宣教,不以生理上的差異來區別人群,而強調在宗教信仰中同一。信仰者代代復述保羅的生平,好比修華告訴我他家族的故事:在後人的不斷敍述中這些歷史人物又重獲新生,而他們的故事又豐富了我們的生命。
除去強烈的宗教背景,這些時光的碎片拼湊出一個非常人間的故事:異邦的點滴已與他們不可分割。馬蹄遍踏,樓臺煙雨,千愁萬恨,都隨光陰蕭蕭去;而這些異鄉的什物(鐘錶,燈籠,瓷碗…)卻留了下來,作為他們用生命堅守信仰的見證。所謂傳家寶,流傳的不僅是古舊物品,也是先人如何理解與建構世界的紀念。
幾年前與朋友重觀《愛在黎明破曉前》(Before Sunrise),忽然留意到一個細節:兩人走進維也納城中的教堂,女孩道:「Even though I reject most of the religious things I can’t help but feeling for all those people that come here lost or in pain, guilt, looking for some kind of answers. It fascinates me how a single place can join so much pain and happiness for so many generations.」因為學習宗教學,經常被人質疑自己本身的宗教傾向,說「I keep an open mind」都被無神論者或堅信徒攻擊。而何不換個角度思考:一棟建築長久屹立,為無數陌生人提供一片空間,包容人間的得失與悲喜。
那麽也許是這樣:對 「物」的控制與佔有,終究脆弱。對 「物」背後的智慧的追尋與反省,通達與承擔,才可穿越時/空的物理限制,讓人心清朗,長久而永續的給生以力量。
注:部份文字曾發表於跨華文寫作互動平台游城客書 BlossonsEveryw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