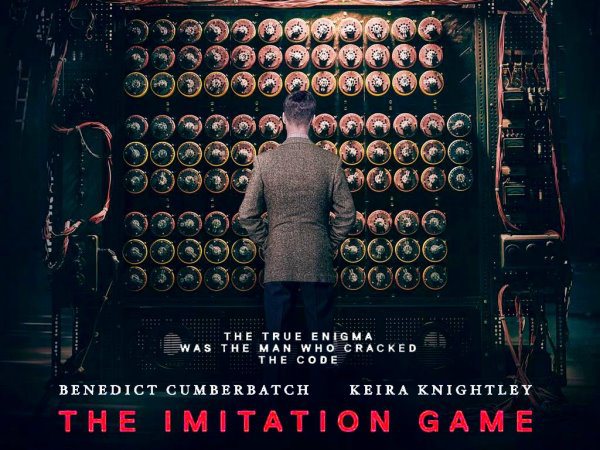如同風華絕代〔並內建票房吸金功能〕的大明星,電影工業也樂於打造獨樹一幟的「城市」品牌,那些由市井、文化、建築,甚至刻板印象所建構出來的神話性格,具有點石成金的優良成效。

電影地誌
伍迪.艾倫(Woody Allen)自然是理解此道的箇中高手,每一座受他欽點的城市,無論陽光或黑暗,都顯得如此強大,有稜有角,彷彿那些故事在其他地方發生就會失去了味道。李察.林克雷特(Richard Linklater)和荷索(Werner Herzog)同樣熱衷於援引地方特色;地景搶戲,人便顯得渺小,行色匆匆,有紅塵如夢、命運難抗之感。楊德昌與台北,小津與東京,王家衛與香港,他們的相輔相成,往往使人無法分辨到底是這些畸零或華美的地方襯托了故事,還是故事襯托了這些地方……
至於影史中前仆後繼使用巴黎城作為羅曼蒂克特效藥的導演,那更不必多說,可惜不是每個人都能把巴黎拍成《新橋戀人》(Les Aments du Pout-Neuf),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沒有靈光,有的城市就算灑補助金吸引外資到當地拍片,也可能不小心把特效藥拍成臭臭的狗皮膏藥。
以維也納為主題的電影極少,其中能把這座城市的戲劇特質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非《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莫屬。這部經典黑色電影由小說家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量身打造劇本,卡洛.李(Carol Reed)執導、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扮演靈魂人物,已經是千載難逢的奇妙組合,但是維也納之城所烘托出來的時代氛圍與空間感,更是這部電影充滿機鋒的關鍵。
在維也納的電影地誌中,「地下」場景一直扮演特殊的角色。二戰後黑影幢幢的《黑獄亡魂》融入了大量下水道追逐橋段,70年代的諜戰片《天蠍星》(Scorpio,港譯《龍虎雙霸天》)也透過許多地底下的場面來講述複雜的政治局勢與人際糾葛,只是下水道換成了當時施工中的地下鐵(U-Bahn)。

《黑獄亡魂》的斷壁殘垣與《天蠍星》道德掙扎
維也納到底為什麼總是留給人這麼多地底纏鬥的印象?或許和它的城市性格不無關係。奧地利身處歐洲中心的內陸國,在風起雲湧的世界政局中時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維也納的樞紐位置以及豐富的歷史與藝文活動,更使它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也是藝術家們借題發揮的重鎮。
《黑獄亡魂》與《天蠍星》引用了維也納的大量象徵元素,這麼做可是用心良苦。實際上,就和《黑獄亡魂》中的奧森.威爾斯與《天蠍星》的亞蘭德倫一樣,維也納也是這兩部片中的關鍵要角。故事和人物雖然都是虛構,維也納卻提供了相當「真實」的情境特效[1],戰後的維也納百廢待舉,新的建設塵埃未定,電影中所呈現的某些市景寫真,反而能製造出神秘而特殊的超寫實效果。
二十世紀的維也納在新舊交接之處,尷尬地與外來勢力斡旋,處於守舊與創新拉扯的陣痛之中,好不容易獲得獨立又成了間諜匯集的大本營,是個充滿對立的城市。也正是因為它的雙面性格,使得維也納的地下世界變成了電影〔尤其是這種善惡莫辨、謎雲重重的黑色電影〕中反覆使用的意象。
十九世紀的藝文評論家丹納(Hippolyte Taine)曾經在《藝術哲學》(Philosophy of Art)書中表示:「假使藝術家能掌握時代精神,便能發現整個世紀都將助他一臂之力。」卡洛.李和《天蠍星》導演麥可.溫納(Michael Winner)雙雙借用了大量屬於維也納的特質與時代氛圍,而維也納也不負眾望,替這兩部作品帶來無可取代的視覺和影射效果。
格雷安.葛林故意將片中的主角何利打造成一位二流偵探小說的寫手,還讓他在片中不斷強調自己寫的小說可是「有事實為依據(based on facts)的」,這麼做自然有點自娛娛人的諷刺意思,也替故事的懸疑留下伏筆和矛盾。無論如何,這兩部片的導演都企圖在電影敘事中編入大量的「事實」,以製造出偽記錄片式的風格〔《黑獄亡魂》的開場白便彰顯了這個企圖〕。

於二戰後拍攝的《黑獄亡魂》呈現許多斷壁殘垣場面,如實反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戰後氣氛。當時維也納被同盟國軍事占領,同時由美國、英國、蘇聯和法國瓜分掌控。當俄羅斯人闖進女主角安娜的房子搜尋非法文件時,安娜的房東以德文抱怨:「天啊這真是太糟糕了,我們根本不算房子的主人了嘛。如果來的是奧地利的警察也就算了,但卻不是,都是美國人、俄國人和法國人……你不能鳩佔鵲巢啊。」
何利與安娜初次見面時,安娜向對方展示了來自英國的茶,以及來自美國的酒,而她與來自同盟國的外國人交往,這些細節在在強化了戰後維也納劇情的真實感。另一方面,《天蠍星》則拍攝於冷戰如火如荼的時期,片中的道德掙扎和緊張的政治情勢,自然也影射了超級強國(superpowers)的角力。
這些生動而「貨真價實」的維也納城市景觀與歷史指涉,映照出現代維也納在短短幾十年間翻天覆地進行的地下改造。
十九世紀末開始,維也納開始一連串重要的「地下」建設,包括現代化地下排水道系統,以及更後來的地下鐵,這些工程間接但相當顯著地改變了維也納的地景,特別是惡名昭彰的卡爾廣場(Karlsplatz)廣場一帶。
二十世紀初,卡爾廣場是維也納現代主義份子的天下,也是傳統與現代建築爭奇鬥艷的戰場,頹圮之牆與絕美華廈並列,維也納分離派〔新藝術派〕的建築師奧托.華格納(Otto Wagner)和畫家克里姆特(Gustav Klimt)成功在維也納堅強的傳統藝術勢力中闖出一片天下。

「地底下」的維也納
約莫與此同時,橫越維也納的維也納河在都市計畫的規劃下也華麗變身,使得現代維也納的面貌產生一次關鍵性的改變。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十九世紀末之前,維也納河一直都是一條超臭的排水溝,因為維也納和郊區半數的廢水通通都直接傾倒至河中,還有水患的問題。為了防洪和衛生考量,維也納河在1889年加蓋封入地下,而原本河邊的傳統中央市場(Naschmarkt)則移到鄰近地點。
二戰時期,地下水道上方不但被四個同盟國軍隊的軍靴所踩踏,黑市交易者也開始盤據,因為1945年之後,卡爾廣場恰巧位於四國占領區的交界處,二戰過後物資缺乏的時期,黑市交易者便在這個灰色地帶盤旋不去。
於是,原本樸實的傳統市場壟罩上一層黑影,地下交易盛行,倖存者和機會主義者交織。卡洛.李在《黑獄亡魂》片頭所提到的那段「黑市的經典時期」,就發生在這個城市努力遮掩的加蓋臭水溝上方。
自從城市地景重建後,卡爾廣場「地底下」便出現了新城市空間。但這一面的卡爾廣場不太光彩,與地表中產階級聚集的空間大相逕庭,現代化之後的邊緣人,窮人、流浪漢與罪犯紛紛躲到地下空間去。也因此,就《黑獄亡魂》片頭獨白所敘述的,「戰前飄盪著史特勞斯音樂、風光又優雅迷人的老維也納」此時可以說是烏雲罩頂,內憂外患。
1955年奧地利終於獲得獨立並宣布成為中立國之後,卻不幸便成了那些「非中立國」特務和間諜的競技場,導致表面上看起來終於風平浪靜的維也納,實際上卻困在政治鬥爭的泥沼之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華沙公約組織(WTO)半公開地在維也納這塊中立點上相互刺探。美國特務和蘇聯間諜更於地底埋管,透過腳底掩藏的流竄纜線,竊聽最高機密。
在諜報最高峰的時期,在維也納匯集的超級強國間諜多達兩萬人,後來被歷史學者受封為「間諜首都」。70年代的《天蠍星》電影便是以這樣的歷史政治背景所攝製的成果。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維也納的地下鐵工程於1969年開始進行。維也納地下鐵也在卡爾廣場下方,距離下水道不遠,卡爾廣場自此的地下景觀又多了一層新面貌,地上景觀也做出調整,道路重劃,出現一條大馬路,鄰近的公園也完全翻新。
城裡最大的地鐵系統有三條主線以及延伸的網絡,這個巨大的工程就和下水道之旅[2]一樣,不但受到遊客的青睞,也獲得好萊塢的注意。《天蠍星》片尾安排了一場反目成仇的老友追逐戰,場景便是在維也納的地下鐵施工地點。雖然都是實景拍攝,但就像《黑獄亡魂》冗長的追逐戲一樣,反而有超寫實的戲劇效果。
簡言之,身為擁有雙面性格的維也納,二十世紀的都市「地景」和「地下建設」唇齒相依,如今的面貌很大一部分是由驚人的地下工程所支撐起來。這個城市的黑暗面經常被放大檢視,地底世界的呈現變成不可忽略的一個象徵手法。
《黑獄亡魂》片子開頭沒多久,一位英文不太輪轉的先生告訴何利:他要找的人(Harry Lime)已經死啦,現在不是在「上面的地獄」,就是在「下面的天堂」──透過這個小小的錯置玩笑,編劇意圖挑戰二元對立的絕對,並藉由電影印證天堂和地獄可能互為顛倒、活人可能生不如死,而死人可能透過某種方式活著的寓意。善惡掉進了灰色地帶,邊界模糊之中,所謂的真實與虛構亦敵亦友。

沉靜如空城︰詭譎的政治氣氛
回顧《黑獄亡魂》和《天蠍星》的歷史背景,不但能指出維也納當代史的歷史星圖,還能理解維也納戰後所面臨的詭譎政治氣氛。在這些片子裡,鏡頭下的維也納戴著平和而無邪的面具,而且似乎永遠的四下無人,沉靜如空城;電影中所使用的言語交鋒和視覺特效〔比如《天蠍星》中在地表與地底上下擺動的視角〕,卻又讓我們想起維也納令人困惑、受地下勢力所牽制的歷史位置,讓人重新審視所謂「中立」的意義。
二十世紀的尾聲,李察.林克雷特製作了後來聞名遐邇的愛情辯證電影《愛在黎明破曉時》,場景選的就是維也納;上個世紀少數以維也納為主題的電影,自此畫下一個輕巧的尾聲。男女主角輕輕一吻的那座摩天輪[3],同樣是《黑獄亡魂》裡諜對諜的那一座。在看過《黑獄亡魂》和《天蠍星》之後,或許會覺得這個同時擁有兩張臉的、暗潮洶湧的、充滿刺探性的、有許多秘密的城市,對於剛萌芽的愛情來說,剛好有一種啟示的作用,再好不過。

註釋
[1] 雖然《黑獄亡魂》不免也必須在真實場景上「加工」整理,製造出超寫實的效果,例如:石階路上大量噴水,使得路面濕潤,得以更戲劇化地映照出人影。
[2] 維也納也有依照《黑獄亡魂》打造的散步路線,包括下水道探訪。
[3] 那座摩天輪是1897年獻給當時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的金禧誌慶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