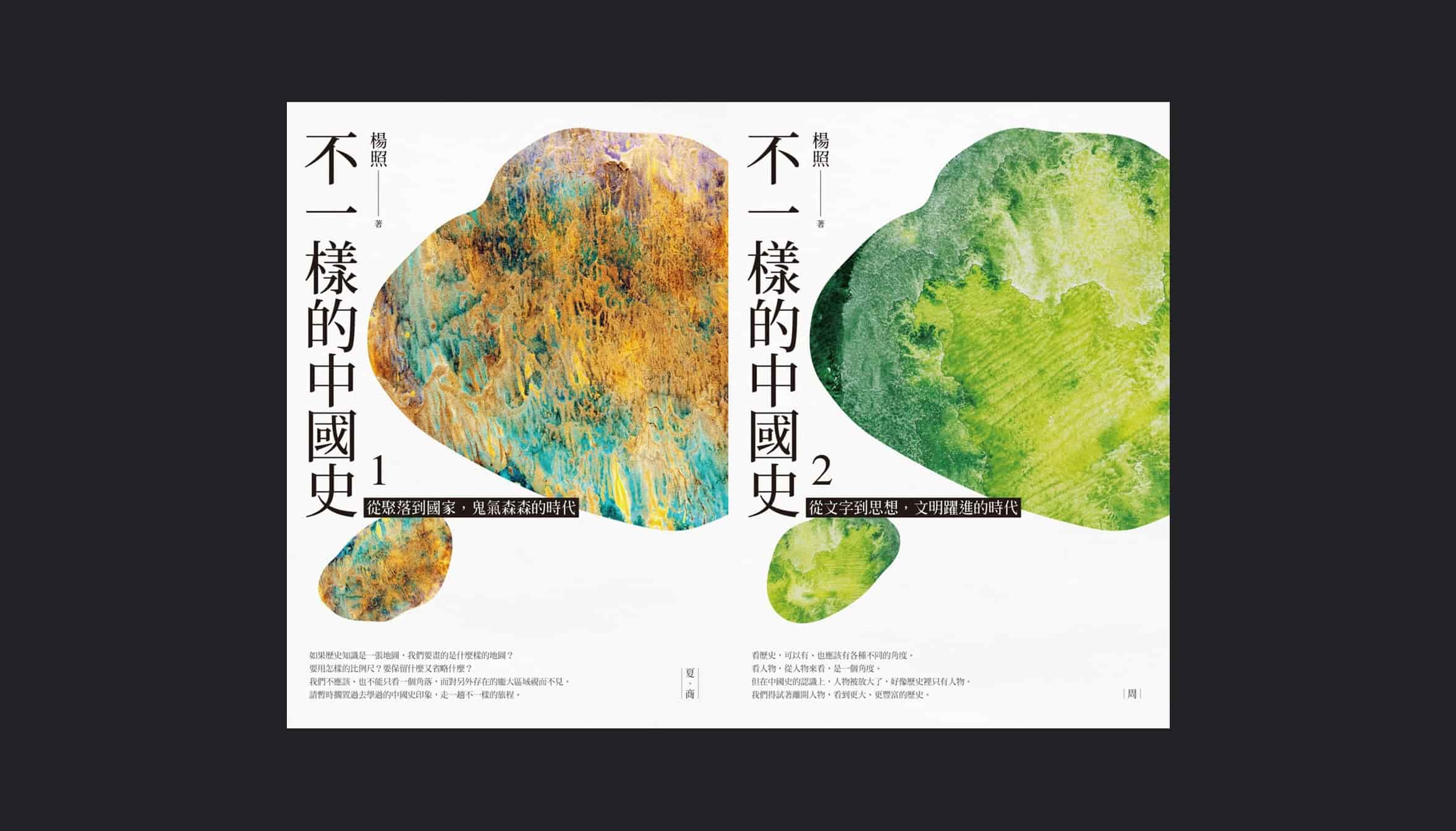《中國史新論》的其他分冊均為特定研究領域(如法律史、醫療史、宗教史等),或是特定課題(如基層社會、生活與文化),基本上都是跨時性且相當聚焦的「專史」,只有本冊將範圍集中在先秦,比較像是一個「斷代史」。
容我在此解釋「古代文明的形成」作為一個中國史新論的分冊以及內容安排的理由。
以下編者會針對性質相似的主要書籍,進行回顧,透過這些回顧,讓有心要進入此一領域的學生,或對於此一領域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比較快速的了解中國上古史這個領域過去近50年的發展,以及重要的著作。當然,也能藉由此一回顧,了解「古代文明的形成」要從哪裡開始?應該或可以包含什麼樣的內容?以及在結構上如何有系統地串起這些內容,當然包括尚未有合適內容的領域,未來可能進行更多的研究。
歷史語言研究所上回以集體的力量來撰寫中國上古史,要推到45年以前(1969),由李濟(1896-1979)主編,他過世以後由高去尋(1909-1991)接手的《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簡稱《待定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 1985)。這套書分成四本,分別是:「史前部分」、「殷商編」、「兩周編之一:史實與演變」、「兩周編之二:思想與文化」,原定一百個子題,是個宏偉的計劃。
「史前部分」在1972年出版,稱為《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史前部分》,後又經過十幾年,共完成了六十七篇(66+1),由於撰寫的時間很長,期間有不少新的資料出現,編輯委員原本考慮請作者增補,但是鑑於有些作者已經過世,最後決定以原貌問世,整體稱為《中國上古史待定稿》。
這套書撰寫者主要是本所研究人員以及重要華人學者,或許是因為名為《待定稿》,且僅由本所發行並未由出版公司印行,這套書一直以來並未獲得應有的注意。其中因為四十幾年來的考古新發現,以及相關研究的進展,史前與殷商兩本幾乎可以進行全面改寫,而兩周部分仍然有重要參考價值,但新出土資料也很可觀,新的看法與詮釋也不少。
從結構的角度看,《待定稿》雖然號稱「上古史」,其實不是傳統的上古史。
依據李濟的說法,傳統的上古史著重在政治史且完全依賴傳世文獻,《待定稿》則具有以跨學科的視野──包括古環境、考古、歷史、文學、思想等──重新改寫中國上古史的宏觀氣魄。而且放棄《史記・五帝本紀》與〈夏本紀〉中具有「神話」性質的諸種記載,以考古重建的「史前史」來替代。
《待定稿》的信史開始於商代(晚商),商代以前則使用考古資料,這是一個比傅斯年還要激進的態度,可謂新大陸考古學的精神。在李濟的上古史的構想裡,還認為需要跨出現在中國的框架,涵蓋東北亞(包括西伯利亞)、東南亞與中亞,徹底地了解不同史前文化的現象與關聯,這與「中國中心」的傳統中國史──局限在中國的地理空間之內,其登場上演的舞台是巨大又孤立的──有所不同。這幾點即使是現在也不易做到。
從「目標」上整體評估,《待定稿》所有的文章還處於描述與分析階段,可能描述還多於分析,很少有框架性與理論性的思考,這是李濟這一個世代未能做到的事,當然這樣的要求,對於開始起步進行科學考古的世代而言,是過度要求了。
李濟的學生張光直則很有意識地將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放在世界古代文明框架來考察,或者提出新的理論,或者用在其他地區形成的理論討論古代中國,進行對話,並修正既有的理論。所以持續張光直的路線,進一步跨出描述與分析的局限,深化理論性與框架性思考,和其他古文明、古文化研究進行對話,是我輩應當努力的目標。
中國傳統的古史觀以《史記》為例,在商代之前不僅有夏代,還加上了連司馬遷本人都質疑的〈五帝本紀〉,將歷史延長了將近1,500年。進入20世紀以後,一方面有顧頡剛等倡議的古史辨,提出古史的「層累地造成說」,指出古史成立的時代愈晚,古史所涵蓋的時間範圍愈長,藉此將早期不可信的部分徹底斬除。
同時也有如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引進了「神話」、「傳說」等概念,提出「神話(或傳說)時代」,於是出現「黃帝集團」、「苗蠻集團」、「東夷集團」等概念。他從歷史地理的分析認為豫西的伊、洛、潁水,以及晉南的汾、澮、涑水與夏族的關係密切,因而展開「夏墟」的踏察,發現了河南偃師二里頭等遺址,導引了二里頭、王城崗、東下馮甚至陶寺遺址的發掘。
他的貢獻為學術界所肯定,但是他將「神話傳說」與考古的概念結合,對於下幾代的學者而言,卻逐漸變成一種觀念上的障礙,無法讓考古學發揮應有的功能。比方,陶寺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在他的概念引導下,兩者都與「夏族」有關,然而從考古資料看來兩者的主要陶器類型截然不同,在方法學上很難想像同一個「族」,在前後相連的兩段時間使用截然不同的器物群。
陶寺的發掘者或許因為在時代與考古內涵上無法聯結夏(或二里頭文化)而改以「陶唐氏」(帝堯)來與「歷史」連結,基本上是走徐旭生的路線,不過無法證實或證偽,就無科學性可言。陶寺文化的內涵與其本體之意義,反而被掩蓋在與陶唐氏的連結之下。
為什麼要區分神話與歷史呢?
筆者認為神話與歷史是兩種不同的思維結構的產物,神話與薩滿式宇宙觀基本上是口傳時代的東西,與之相對應的是歷史與地理,是文字書寫系統發明後的產物。
中國古代文獻保留了一些口傳時代的內容,有些屬於神話,更多則屬於薩滿式宇宙觀,但兩者皆可歸屬於「神話性」的範疇。神話性與歷史性最關鍵的差別是它們的時間觀完全不同,神話時間是循環的,所以神話人物所處的究竟是什麼時代,這是無法確定的。
歷史時間則是線性的,有先後之別,有因果關係。薩滿式宇宙觀也不是地理,地理有絕對的方向與距離,而且都是實存的東西,但是薩滿式宇宙觀的空間是相對的,而且其元素包含實存的自然與人間元素,也包含超自然的鬼、神界事物共存於一個界面。
所以筆者認為古代文明的形成如果要利用文獻材料,必須有「解構炎黃神話」的一章,其主要目的是要把神話與薩滿式宇宙觀的內容,和歷史與地理進行切割。考古學所建構的古史(史前史+歷史)連結的是歷史而非神話,其依賴的連結主要是文字材料。但無論如何考古學絕對不是只為傳世文獻所建構的歷史提供註解,更不應將神話與考古學牽扯在一起。
《待定稿》的史前部分,是最早出版的,幾乎完全依賴考古材料,因為有太多新出土的材料,它的被取代性最高,但卻可以讓我們看出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課題之形成與發展。
史前部分李濟寫了三篇,阮維周寫了一篇,多與智人以前的猿人的討論有關,其餘九篇都是張光直寫的,涵蓋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狩獵採集,到農耕社會的出現,進入文明門檻,以及中原文化的擴張等,因為具有跨文明比較的視野,讓他對於中國早期文化的發展具有穿透性的洞悉力。
這部分更企圖涵蓋不同的區域,從草原文化到東北與南方,而非中原中心。以當時的條件,能寫出這些文章,並不容易。他所負責的部分,後來經過不斷的修正而逐漸穩定下來,形成了第四版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的主要內容,本文會在以下說明。
從《待定稿》開篇為環境議題,我們知道當時學者已經意識到環境變遷對古代人類的文化與文明可能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對於環境與人的關係還在摸索階段,兩者的連結並未真正建立。
阮維周的研究止於更新世(2,588,000-11,700 BP),並未延伸到新石器時代甚至青銅時代的環境變化,殊為可惜。Robert Orr Whyte在《起源》中有〈中國環境的演化〉一文,也有相同的問題。環境變化與人的關係近來逐漸受到重視,《中國考古》(詳下)有環境與生態一章,對於環境與生態,有比較好的整理,不過可增補的內容仍多。一個有系統的古代文明的形成,亟需要一篇比較全面的環境、氣候變遷與古代文明之研究。
一方面交代更新世晚期環境的狀況,特別是距今四萬年到更新世結束的這段期間,因為這很可能是智人出現在東亞地區的時代。這段期間東亞地區很重要的特徵是末次冰期將大量的水分鎖在地球的兩極,以致海洋水面下降,最多達130公尺以上,東亞大陸邊緣的陸棚多成為陸地的一部分,連結到島弧地帶的日本、臺灣、菲律賓,東南亞的島嶼群形成巽它大陸,與中南半島連在一起,但仍與澳洲、新幾內亞、塔斯馬尼亞島連結成的另一個薩虎爾大陸隔海峽分離。
白令海峽陸橋也讓美洲與亞洲連結在一起。更新世結束,進入全新世以後,先是暖化,然後出現一個小冰期,接著再回暖,此一變化,研究西亞地區農業起源的學者認為可能是農業起源的重要外在因素,這對東亞農業起源而言,也可能是重要因素。再緊接著是全新世大暖期,使得草原減縮,森林增長,人口也快速成長。大暖期結束使得資源緊縮,造成劇烈的競爭,此與所謂「文明」的出現有極密切的關係。
總之,溫度與乾燥度的長期性的起落,造成人類利用的資源的多寡,也一直牽引著人類使用不同類型資源群體的上下,甚至造成人類社會結構性的變化。
其次,地景元素的變化,也牽動著人類文化的發展,比方華北地區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黃河,黃河以及其他河流、湖泊在不同時期的狀況,及其變遷,都會對鄰近地區造成很大影響。因此環境、氣候變遷與古代文明之研究的關鍵是,氣候與環境變遷如何影響到古代人群。
其次,如何處理猿人與舊石器時代的問題。由於當時國際上關於人類起源的理論尚未成熟,所以即便這是李濟本人的專業,在當時亦無解。主要在於要不要把「北京人」與現代的中國人聯繫起來?
李濟一方面強調民族主要是依賴文化來界定,但是另一方面還是說:「講中國上古史,由北京人說起,我們確有很好的理由。」當時主要是依賴古代人骨的形態學比對,但是我們知道形態學的基礎是需要有很大的基礎樣本,但是古代猿人的化石是相當有限的,不可能有太多樣本,也就不可能讓人信服。所以形態學在基因研究出現後,就被完全地取代了。
李濟在〈史前文化的鳥瞰〉中論「史前史從何說起?」同樣討論的是在東亞地區發現的各種猿人的化石,然後從猿人跳躍到智人,究竟是在地的猿人演化成在地的智人,或有其他的可能性?
這個問題在當時無法解決。
W.W. Howells在《起源》中〈中國人的起源:近出證據的解釋〉則有不同看法,他與當時學術界的主流看法認為從頭骨的相似性看來,現代人(智人)都是源自同一祖先,而其祖先的年代當晚於北京人,雖然他支持此種看法,但仍採兩案並陳的方式交代。
過去二十幾年間古代人類的研究因為DNA的測序以及古DNA檢測,而起了很大的變化,母系遺傳的粒線體DNA以及父系遺傳Y-染色體單倍群的時空分析,使得智人(Homo sapiens)跨出非洲(out of Africa)的理論與來自人類化石的證據逐漸重合。依據現在的看法,智人大約在20萬年前在非洲出現,現在世界上所有的現代人的祖妣,大約是六萬年前跨出非洲,然後散布全球。
此一改變對於「史前史」的概念有何影響?
Colin Renfrew在Pre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Modern Library, 2008)一書中,重新檢視史前史的概念,他提出「思維方式的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mind)的概念,將智人出現以前的當作自然史,從宏大的理論角度來剝開智人思維方式演變的洋蔥。
據此,東亞的史前史,就應該從具有現代人的思維模式的人類到臨,也就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討論。北京人、尼安德塔人或其他人類,則基本上是演化中的失敗者,最終滅絕。
不過,有些與智人相近的人類,比方尼安德塔人,確定與智人有基因滲入。
有趣的是,尼安德塔人的發現地點多在歐洲附近,但現代的東亞人比歐洲人反而有更高比例的尼安德塔人基因滲入。總之,與古DNA有關課題的觀點還在快速轉變當中,上古史研究者需要持續地關注。
關於更新世到全新世早期間的狩獵採集者,《中國考古》(詳下)中〈更新世-全新世轉變下的狩獵採集者〉,根據考古資料作了不錯的綜合,比較重視幾個已經發掘的遺址的個別內涵的描述,及其分布的整體意義。
不過,從現在的觀點還可以寫一篇「智人到臨:東亞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狩獵採集群隊及其生活」,此一題目要討論的是所謂peopling,即智人在一個地區的出現以及散布的狀況。當人類跨出非洲時是狩獵採集者,而且可能的社會組織方式為「群隊」(band),他們的分布與生活如何?如何擴散?
此一問題現在有不同於早年的思維、方法與工具。一方面我們可以用地理資訊系統整合東亞各地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資料,以了解這些遺址的時空分布。其次,針對早期的人骨進行古DNA的分析,並且與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資料進行交叉比對。第三個步驟則可以針對不同地區的現代人進行系統性的DNA的分析,如果此種資料夠細,比方以縣為單位,有些古代曾經在此地生活者的後代就可以顯示出來。
這三種資料互相參照,應可以逐漸模擬出早期人類群體分布的狀況。

傳世文獻所楬櫫的中國上古史不斷地受到新材料的挑戰,
舊有的理解框架也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
一個新的「古代文明的形成」靜待學者開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