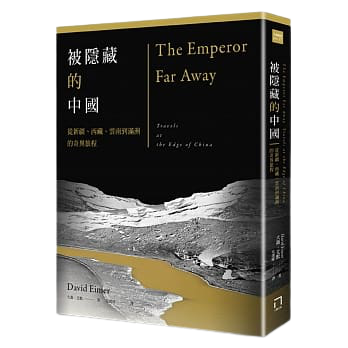阿峇(Aba)看起來就跟尋常的十五歲少女沒有兩樣,嬰兒肥的臉龐在在透露她相當稚嫩的事實。她穿著牛仔褲和短袖圓領衫,手上還握著一支珍貴的手機,臉上還帶著害羞的微笑,不過看起來比大多數的少女神色緊張得多,說話的聲音不過比喃喃自語高那麼一點。我推斷那是克欽族女孩首次遇到西方人時的天生反應。我對她的觀察,要到了後來她告訴我恐怖的遭遇之後,我才瞭解到阿峇對人如此羞澀和遇事狐疑的原因。

我們在一個邊界城鎮瑞麗(Ruili)相識,那是中國境內惡名昭彰的犯罪淵藪之一,隸屬於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一直都與走私和販賣婦女掛勾在一起──因為瑞麗就緊鄰著撣邦與克欽邦。它與緬甸的木姐(Muse)中間只有一道老舊的金屬圍籬為界。阿峇一直都住在木姐,當她十二歲時,第一次爬過圍籬千瘡百口中的一個破洞。隔壁女鄰居勸說她去一趟瑞麗,並且承諾當晚就會帶她回家。
那是個致命的謊言。阿峇自此三年內再也沒能見上雙親一面。就跟其他成千上萬的少女與婦女的遭遇雷同──她先被拐騙到中國,然後賣給愈來愈多在中國除了用這個方法以外都娶不到老婆的男人。
阿峇很快就越過邊界到達瑞麗,然後在中國走了三天,才被丟到一個她始終都不知道地名的漢人家庭之中。她被迫待在那裡時天天遭到毒打,也不能與家人聯絡或是獨自外出。最糟糕的是阿峇還被迫嫁給這個家庭的兒子當童養媳──他把她當成農場所養的雞隻一樣給買來。阿峇說:「我被以兩千元人民幣的價格賣掉了。當他們買我時,我還太小,不能結婚。之後他們才告訴我,必須嫁給她們的兒子。這樣還算是幸運的了,如果我再大個兩歲或三歲才被騙來,當時就得馬上嫁給他。」
一開始我聽到她說只因為年紀小而未能馬上被迫下嫁一事感到慶幸時,我還覺得古怪。如果是我,十二歲就被拐走並且被賣為奴,我根本就無法這麼樂觀以待。不過,我之後就瞭解她說的是對的。多數的克欽族和撣族婦女被賣到中國被迫為妻,都不會獲救也不會想方設法逃脫。她們永遠再也無法見上家人一面。如此說來,阿峇的確是幸運的。
德宏和瑞麗的少數民族就如同在版納地區的少數民族一樣,和國界外的遠房親族有著相同的民族性與文化。不過這裡的傣族是屬於傣那族,他們與撣邦親族之間的共通性要遠比跟版納地區說著不同語言的傣仂族緊密得多。德宏境內大約有一萬三千名景頗族人,他們與緬甸境內的克欽族是同宗。在這個區域內也可以見到傈僳族(Lisu),他們也遍及整個撣邦地區;還有德昂族,多數還是位於撣邦北部,被稱為巴朗族(Palaung)。
阿峇身為克欽族,又來自木姐,使她成為人蛇集團犧牲品的機會大幅增加。木姐緊挨著中國邊界,且幾乎就位於撣邦和克欽邦之間,如今把婦女販賣至中國的最主要來源地就是這兩邦。越南與北韓女子也會被賣為人妻或是性工作者,不過在近幾年中,這些非自願新娘的主要來源卻是緬甸──這也是由於木姐和瑞麗之間有著開闊邊界的結果。
分隔兩城鎮的邊界鐵藩籬根本毫無效用,人們可以上午從木姐跨越邊界來到中國工作,中午還可以回去吃個午餐,下午再回到中國。離正式的國境檢查哨大概幾百公尺的距離,那條生鏽的圍籬上有許多破口,隨時都可以看到成排的人群在穿越那些裂開的國境缺口。白天時,從木姐來到瑞麗的是擔任建築工人或是民家僕役的民工;入夜之後,來的就是娼妓了。反向從中國跑到緬甸的,則是無賭不歡的中國賭客,因為賭場就在不遠的邁扎央(Maijayang)。

***
每天晚上所有從瑞麗這端非法穿越邊界圍籬到緬甸的是雞、豬、米、電話、電腦,甚至還有輕型機具。開發落後又資金短少的緬甸是沒什麼能夠當成回饋的。不過,緬甸還是有三項市場大宗可以大量提供,那就是:毒品、寶玉,以及人數不斷擴充的漢族單身男性對於尋找老婆的需求。
中國的單身漢也被稱為「光棍」,而且娶不到老婆還是個很嚴重的污名。不過儘管中國人口極眾,適婚年齡的女性還是嚴重不足。超過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嚴格限制了多數的漢族家庭只生育一個小孩,再結合中國傳統上偏好男孩的習俗,因此造成了毀滅性的性別失衡現象。官方的統計數字指出,男女嬰的比例是一百二十名比一百名,這樣的比例在某些省分可能會更高。
重男輕女是傳統中國人的觀念。選擇性流產在技術上來說是非法的,不過許多即將成為父母的夫妻會賄賂他們的醫生,要他們說出嬰兒的性別,如果是女嬰,就會結束她們的生命,特別是在中國鄉下地區。不僅僅是因為男人能夠下田工作,而且能夠傳宗接代,還有至關緊要的是在雙親年長之後能夠照料送終。
在中國根本談不上有社會安全體系,照料年長者的責任就屬於各別的家庭。就算在大城市內,也常見到祖孫三代同住;當小孩的父母親外出工作時,祖輩老人家通常是孫兒輩的主要照料者。可是在鄉下地區,為雙親提供居所都是兒子的責任;因為女兒嫁出門時,她就是夫家的一分子,照料的對象從自己的雙親變成了公婆。
在過去,鄉村女子通常不會去上學,因為她們終究要跟夫家一起過活,上學被認為只是浪費錢。現在,教育機會普及,再加上極欲逃離單調乏味的鄉間生活的誘因,已有更多的女子搬離鄉下,往外尋找待遇更高的工作。只有很少數人會回到鄉下老家,在大多數的中國村落裡,碩果僅存的女性通常都是佝僂老嫗。

農業地區的男性數目不斷增加,現在面臨到一個艱困的抉擇環境:要不維持單身不娶,要不就是從其他地方買個新娘回來。這樣的地下產業應運而興,以能滿足他們尋找妻子的需求;而緬甸就是他們找到老婆最為理想的地點。在克欽邦與撣邦北部鄉下地區的平均收入,一天大概約一英鎊(約十元人民幣),這些人蛇很輕易就能說服女子離鄉背井,前去中國尋找那份其實並不存在的工作。當她們穿越邊界圍籬來到了瑞麗,這才發現她們都被騙了,此時要回頭已經太晚,只能面對成為禁臠般配偶的淒涼未來。
沒人能夠確切知道每年到底有多少萬名緬甸婦女被人蛇給賣到中國。顯而易見的是,人數還在攀升中。克欽族婦女茱莉亞(Julia)在一個協助極少數獲救婦女、或是幫助像阿峇這樣逃脫者的泰國機構工作。她告訴我:「我只能知道每年有多少婦女會來到瑞麗的『安全之家』,光是去年一年,人數就已經倍增了。」
茱莉亞二十七歲,個頭嬌小不過個性認真,又十分以身為克欽族人為榮。雖然她也相當偏執,可是卻有充分的理由如此。她跟那些走私販一樣都靠著穿過邊界圍籬的缺口,頻繁往來於瑞麗和克欽邦之間。人蛇集團販賣婦女方式不見容於陽光下,她的工作也一樣只能私下進行、無法聲張。緬甸當局對此毫不關心,因為這些被販賣的婦女都是來自和政府軍作戰對抗的少數族裔;而中國方面比較關心的是在中國境內發生綁架與販賣孩童的情事,婚姻買賣的防堵反而不那麼積極。因此,茱莉亞只能孤軍奮鬥。
被人蛇集團拐騙是個極端難受又備受羞辱的經驗,情緒上的傷痕會終生都跟著被害人。茱莉亞解釋:「緬甸的人蛇分子會把婦女帶往邊界,在那交給中國的人口販子。有時候會先安排好人口買賣,不過通常都是被送到瑞麗公園內的人口市場交易。這些人蛇會要她們打扮得漂亮些,還要化妝,這樣才能賣出好價格。這實在很殘忍,當這些女子開心穿上生平從來都買不起的漂亮衣服時,就是待價而沽的開始,她們接著就會被像販賣蔬果一樣,秤斤論兩地被賤賣掉。」
幸好阿峇不用走到一群潛在性買主面前,像是拍賣場上的動物一樣排成一排。不過,她被帶走的時候年紀非常小,這也就是她被當成童養媳給賣掉的原因。所有被非法買賣的女性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是未成年的。茱莉亞說:「買走這些女子的男人總是希望女人能幫他們傳宗接代。他們都會先問這個:他們想要年輕又健康的女孩。」
一名新娘的價格大概在六千到四萬人民幣之間,視女子的年齡和外表而定。根據茱莉亞的說法,有些女子完成生子任務後,甚至會被轉賣一次。她說:「他們把這些女子當成嬰兒製造機。一旦她們生完小孩,就會被賣到另外一個家庭,有的還會被賣到娼館成為妓女。」
中國雲南還是緬甸人蛇買賣婦女的最主要目的地,有些會像阿峇那樣被送往中國的其他地方。阿峇也不知道她到底被送到哪個省分。她用很細微的聲音說:「起初我花了一天的時間搭巴士到很遠的地方,然後換乘火車又是兩天的時間。那裡雪下得很大,冬天時非常寒冷,而且所說的普通話口音和雲南的很不一樣。」從她對氣候以及旅程長度的描述來判斷,我想阿峇應該是被載到中國北方或是東北的某處。這幾個省分的鄉下地區都缺少婦女,也最符合她的敘述。
離家幾千公里遠,還要和說著完全不同語言的陌生人同住,又把她當成不用支付薪水的奴僕,阿峇簡直就嚇壞了。「大多數時候我都很害怕,而且很孤單,因為沒有可以說話的朋友。我哭慘了。一開始他們還好言好語勸我不要哭。之後,只要我一哭,他們就會對我大聲咆哮。」她也遭到肉體虐待。阿峇說:「我一開始還不會說普通話,因此我不知道在農場上和家中有什麼農務雜事是我該做的,所以常常犯錯。然後,媽媽就會揍我。」
顯然她所經歷過的磨難還讓她揮之不去。她告訴我:「我也很害怕自己一個人出去,特別是晚上出門。」她被綁架前的生活並不輕鬆。阿峇的父親在木姐擔任臨時工,而且要養三個小孩。阿峇在那趟命定的瑞麗之旅前,就已輟學外出工作協助家計。
要逃脫農場是不可能的事。阿峇沒有錢,也不知道身在何處,她肯定無法逃走的。她說:「他們無時無刻都在監控我。不讓我單獨外出。」她也不能打電話給父母,因為那農場家庭窮到連電話都沒有。因此阿峇只能跟那個家庭苦苦哀求,讓她離開。
「我只想要回家,回到父母的身邊。我拜託他們讓我離開,但他們拒絕我,我就只能繼續留下來。」她最後終於發現她被誘拐,以及為何被牢牢看住不放的原因。有天,這個家庭透露她必須嫁給那二十一歲大的兒子。阿峇以幾乎無法聽聞的聲音說著:「我到了那裡幾乎快三年之久,他們才告訴我必須嫁給他。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為何會被帶到那裡。我當然拒絕了,不過,他們也說我非嫁不可。」
事實上這些被賣為人妻的女子並沒有選擇的權利,只能嫁給那些已經買下她們的男人,因為她們也沒有逃脫的機會。她們的狀況就和阿峇一樣,全都被困在一個家庭牢籠之中。茱莉亞說:「大多數被販賣的婦女都不會逃脫。我們根本就沒有線索可以幫助她們。」有些人面對這樣束手無策的狀況,會喝農藥結束自己的性命──這是中國鄉間最常見的自殺方式。
少數女子會想盡辦法試著逃跑,他們多半是住在離雲南還算近的家庭。茱莉亞說:「有時候會有善心人跑來告訴我們,他們的村子內有被販賣來的婦女;有些則是被賣的女子找機會主動打電話告知,我們才會打電話給當地的警局。除非我們確切知道是在哪個村莊的某處,否則當地警方通常不會積極協助。不然,我們只能告訴那名女子,得想盡辦法跑到最近的警察局報案。因為她們都沒有中國身分證,只要她們被逮捕,就能獲得遣返回緬甸的機會。」
沒有中國身分證的阿峇也是因此獲救。在得悉必須嫁給農場兒子的兩個月後,她跟這家人的祖母以及女兒在另外一個農場工作。他們每人每月的待遇是一千元人民幣,不過,阿峇的份得交給祖母。她說:「有一天員警來了,並且要求查看身分證。我沒有身分證,所以被員警給帶走了。」被警方帶走後,阿峇得跟他們解釋她的一切經過。「警方前去那個家庭,並且告訴他們:『你們不能買賣人口,她們又不是牲畜。』」警方問我,是否要對這個家庭提出訴訟。不過我回答:『不要。我只想忘掉這一切,趕緊回家。』」
警方對她妥善照料,這也是中國警方的新變化。直到前幾年,中國當局都將被拐賣婦女視為非法移民,在遣返她們之前都還關在監獄內。
跟父母分離三年之後,阿峇獨自一人走過木姐的官方邊境檢查站,回到了家中。阿峇說:「我爸媽驚訝地看著我。他們開始哭泣,我也跟著大哭。我很高興還能見到他們,他們對於所發生的一切都沒過問。我爸媽知道我是被帶走的,只說一切都過去了。」
在阿峇消失後,他們也曾經試著尋找。他們去了木姐的警局,不過警方告訴他們,她已經被綁架並且帶往中國了。阿峇說:「員警跟他們要錢,有錢才會調查。他們開口要六千元人民幣,我父母根本就付不起。」茱莉亞告訴我,這是緬甸警方對於販賣婦女案件的制式回應。她說:「除非你願意付錢,否則警方是不會把相關資料傳給中國當局的。」
***
早在 1980 年代末期,當中國開始放鬆邊界管制以來,瑞麗就一直以走私商品廣為人知。做為中國婦女買賣大本營的惡名,是近幾年才開始的。此一邊界在文革初期,技術性地加以封閉。但要關閉雲南的邊境根本就不是可行之事,人們還是持續穿越國界去拜訪親朋好友,或是躲避紅衛兵。尤其跟緬甸相鄰的邊界在 1986 年又正式開放後,瑞麗正式成為犯罪天堂的代名詞。

瑞麗可說是墮落的邊界城鎮的極端化身,原本也就是中國的罪惡淵藪之城;人們在周末時蜂擁而至,就是要來盡情地放蕩狂野。幾十年來,每個人都受制於中共嚴厲掌控之下,也都臣服在其扭曲又禁慾的道德規範之中,瑞麗接納生活中藏污納垢的方式並非獨一無二。但因為其位置緊鄰著緬甸目無法紀的邊界地區,使得中國境內其他地方都無法像瑞麗那樣,能夠對於那些前來尋歡享樂之人提供萎靡墮落的娛樂方式。
聚賭小屋和叢林賭場在邊界的對岸發展得欣欣向榮,在邁扎央這個村莊內,賭場多到讓它享有「緬甸的澳門」之名。當我首次踏上瑞麗時,幾百間漢人和緬甸人的妓院到處都是,全都臨著馬路,妓女就坐在那搔首弄姿,其中也有當地少數族裔的婦女。從金三角來的海洛因也是隨手可得,而且吸毒者就和這些女伴遊共用針頭,瑞麗自然很快就成為中國境內感染愛滋病密度最高的地區。
當地政府在過去幾年都試圖以「中國西南玉石中心」的招牌來延攬商機,從而擺脫庸俗污穢的形象。漢人對於玉石有著無法自拔的迷戀,既是一種代表身分與財富的珠寶,同時也象徵著誠實與崇高品德。漢族女性被教導應和玉一樣純潔,而孔子是用玉來做為人傑之象徵。
新疆和闐所出產的是白玉,是玉類中最珍貴的。而當地人都把緬甸玉稱為「綠金」,也同樣深受喜愛。和我上次造訪相比,瑞麗的玉市規模已經擴大了一倍。儘管賣玉的店家櫛比鱗次,交易商還是會說生意並沒有更好。其中一名漢族交易商解釋說:「價格上漲了,主要是因為緬甸囤積居奇。緬甸還是出產許多玉石,不過有出口限額。」
隨著收入提高,這些以往在中國只有帝王貴冑、達官顯要以及妻妾成群者才負擔得起的裝飾品,現在尋常人家也得以購入。正是因為這種對「綠金」永無止盡的需求,緬甸出口限額才促使玉石黑市出現,而且還大量、持續地非法出口到瑞麗。除了玉石之外,還有紅寶石和柚木。
許多緬甸人都搬到瑞麗以便加入玉石交易,甚至多到讓瑞麗市區內好幾條街看起來就像是在緬甸的前首都仰光一樣。身穿羅衣的緬甸男子會在餐廳內啜飲著冰奶茶,一直坐到深夜;而雙頰會塗上檀娜卡(thanaka)──緬甸婦女使用的天然防曬乳──的女性流動攤販賣著香蕉葉包裹的檳榔子。有些漢人會私下咕噥著,說大量湧入的緬甸人該為此地大多數的犯罪事件負責。但瑞麗的臭名已經積年累月,我認為那只是他一廂情願的觀點。

瑞麗除了玉石之外,還大肆宣傳它會是未來的度假勝地。中國當局指出,計劃中有條從昆明出發、通往仰光的高速鐵路,會途經瑞麗。不過,對於瑞麗能否搭上,或是終將搭上觀光熱潮的浪端,我是抱持懷疑的態度。因為直到 1960 年代末期,德宏這個地區還被漢人視為畏途,認為此地住著大量不為人知、又不友善的少數民族,而且滿是瘴氣泥沼。
西方旅客也會避開此區。馬可・波羅曾經寫到,「夏天的空氣十分污濁又惡劣」,同時還警告,外人「會因不明原因而亡」。當派駐中國的蘇格蘭外交官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在 1906 年要前往曼德勒而通過此區時,還得費力說服腳伕跟他一起穿越該區域。莊士敦後來成為末代皇帝溥儀的私人教師。在貝納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電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他的角色就是由知名影星彼得・奧圖(Peter O'Toole)飾演。
儘管瑞麗周遭有許多香蕉園,可是傣族人和景頗族人並未像版納地區的傣族人口那麼興盛。在跟某個漢人一道吃瑞麗最受歡迎的燒烤時,他告訴我:「這裡的傣族人跟版納地區的傣族人不太一樣。他們跟緬甸人比較像,景頗族人也是如此。」整個德宏境內,很難把傣族與景頗族和他們國外的親族在外觀上做出區隔,顯著的差別只在於雲南和緬甸之間貧富落差極大而已。
所有的少數民族都憎惡瑞麗走向井然有序的方式,不管怎樣看起來都顯得過於表面,而且他們也未蒙受其利。這樣的不滿就顯露在他們對於漢族與外國觀光客的矛盾情緒之上,他們可是一點都不歡迎這些觀光客。在我所探訪過的中國地區,只有瑞麗會讓我晚上待在外面時得時頻頻回頭,以提防任何危險發生。
瑞麗這裡並沒有美麗的傣族女子表演舞蹈,讓那些漢族觀光客目不轉睛地欣賞;反而有一堆妓女想賺足養家活口或是吸毒的花費。海洛因和鴨霸在此隨處可見,許多看起來平淡無奇的小店私下就有販售。某天傍晚走在瑞麗最熱鬧的大街上,我幾乎跌在三名靠著牆癱坐的男人身上。他們身上很髒,一付毫不在乎的態度,有根注射器就插在其中一人的手臂之上。離開了瑞麗,特別是位於邊界的景頗地區,到處都是管子內還遺有半管血液的廢棄注射器。
不過和販賣婦女相比,毒品、賣淫和玉石走私都顯得無足輕重。把無辜的年輕女孩給賣掉,使得她們陷入悲慘生活是如此卑鄙齷齪,以至於瑞麗其他所發生的一切幾乎顯得是有利身心健康的。讓人感到挫敗的是,這些把婦女給拐騙至中國的人蛇分子本身就是景頗族人。茱莉亞說:「有時候景頗族人還會跑到克欽邦來找新娘。因為我們把景頗族視為手足,當他們開口要求時,我們會同意。不過,那些通常都是假結婚,當他們去了中國時,就會把這些女人給賣掉。」
景頗族人會在販賣人口上合作,或許是因為他們和緬甸的遠親一樣一貧如洗,只要能改善這種狀況,他們什麼都肯幹;也可能只是因為他們個性冷漠。不過,貧困驅使他們販賣婦女是毫無爭論的。中國性別比例失衡的狀況驗證了這種非自願新娘是有市場的,然而,卻是撣邦和克欽邦告急的政經局勢才加速了年輕女子出走。即便木姐和瑞麗之間的邊界圍籬有十公尺高,而且還通了電,依舊阻止不了。人們為了追尋更美好的生活,還是會找出前往中國的方法。
阿峇重返瑞麗就是個鐵證。在她獲救三個月之後,又爬過邊界圍籬上的一個裂口。這次她是獨自前來,要找份工作好幫助雙親。她目前在一間餐廳當服務生,一周七天都在上工,一個月可賺六百元人民幣。她那段被賣掉的青少年歲月讓她能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也使得她得以融入當地人的生活。在她被拐走的三年時光中學會了中文,也勉強算是種慰藉。
我們上次碰面時,阿峇還告訴我:「我依然痛恨那個家庭對我的所做所為。我想我一輩子都不會忘掉。」
[1] 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早年在香港殖民地政府任職。 1919 年至紫禁城教授溥儀英語、數學、世界史、地理;師生感情甚篤,曾封「一品頂戴」、「毓慶宮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