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男生,是男生!」 6 日上午 8 時 50 分左右,日本各大頻道播出二皇子妃紀子產下男嬰的好消息,幾乎所有的播報員都提高了嗓門,向屏息以待的日本國民報告了這個消息。……這是日本皇室暌違 41 年之後,誕生的第一個男嬰,無疑解決了皇室長年以來沒有男嗣的皇位繼承問題。[1]
2006 年 9 月 6 日,日本皇室誕生了一位男嗣,舉國歡騰。對於這個消息,日本首相說這是「日本的喜慶之日」,一般店家則招待蛋糕或清酒共享喜氣。雖然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日本也身列民主多元的已開發國家之一,而且皇室並沒有政治實權,天皇的存在僅具象徵意義,可是皇室與許多人民仍然認為男嗣才能延續皇室正統。儘管日本史上曾出現過八位女天皇;儘管日本也有興盛的女權運動,但在皇位繼承上,女子仍未得到同等的權利。
在此之前,日本天皇明仁已有三位孫女,卻遲遲沒有皇孫延續所謂「萬世一系」的皇位。現在皇室與許多支持皇室傳統的保守派人士終於一償宿願,也有人預估日本的經濟將因此看好。皇孫誕生之後,普天同慶的畫面,透過電視不斷播送,像極了英格蘭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47)的時代。
在亨利統治近 30 年之時,他的第三任王后希摩爾(Jane Seymour, 1536-37)終於在 1537 年 10 月 12 日為王室產下一名男嗣,取名為愛德華,即後來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r. 1547-53)。王子誕生的消息公布後,亦是舉國歡騰,「全國各地施放煙火,人人充滿欣喜地感謝全能的上帝,因為祂賜與了一位尊貴的王子來繼承這個國家的王位。」[2]
據說連國王本人都激動得流下淚來,而臣民不分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也同感振奮,相信愛德華的誕生代表上帝不再讓英格蘭人遭受苦難,國家將會欣欣向榮。隨著王子誕生、受洗、受封(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歡欣鼓舞的氣氛在英格蘭延續數週,人們在街上隨處可以喝到熱心民眾提供的酒,倫敦塔上也不斷射出禮炮致敬,估計這段時間共發射了兩千響禮炮。[3]
在愛德華誕生之前,亨利王已有兩名女兒,分別是亨利第一任王后凱薩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在 1516 年 2 月 18 日所生的瑪麗公主(Mary Tudor, 1516-58),以及第二任王后安葆琳(Anne Boleyn, 1501-36)在 1533 年 9 月 7 日所生的伊莉莎白公主(Elizabeth Tudor, 1533-1603)。雖然亨利的嬪妃布朗特(Elizabeth Blount)在 1519 年曾為國王生下兒子,名為亨利.費茲羅伊(Henry Fitzroy),但他不具有合法繼承資格。
在愛德華誕生之前,亨利始終無法摒除對王位繼承的憂慮。
此憂慮其來有自,第一,英格蘭在法律上雖不排斥女子繼位,但歷史上從無女王主政。
第二,繼承危機總易引發內戰,殷鑑不遠。因為英格蘭在 1455 至 1485 年之間,蘭開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與約克家族(House of York)的繼承紛爭,即爆發了流血內戰,史稱玫瑰戰爭(Wars of Roses)。
都鐸王朝即是由此內戰脫胎而出,首位君主亨利七世(Henry VII, 1485-1509)即位之後,仍不餘遺力地確立統治合法性,並藉著與約克家族的伊莉莎白(Elizabeth of York, 1466-1503)聯姻,增進王位正統性。
至亨利八世繼承王位,兼具蘭開斯特家族與約克家族血統,都鐸王朝的正統性才毫無疑義。但都鐸王朝能否穩固延續,則需另一位合法男嗣繼承。
第三,君王不能育有男嗣,在當時被認為是「神譴」的象徵,必是君王犯了某種罪,使他的男嗣若非流產便是夭折。例如亨利的第一任王后凱薩琳,除了流產多次之外,在 1511 年曾幸運的生下王子亨利(Henry Tudor),當時也曾薄海歡騰,可是亨利王子七週之後瘁死,這個事件使得國王自省「他做了什麼觸犯上帝的事」?[4]後來,王后在 1515 年又產一子夭折,此後再也未能為國王產下男嗣。
到了 1527 年亨利已在思考是否與凱薩琳離婚,或更正確的說法是,他要請教宗確認他與凱薩琳的婚姻無效,因為這項婚姻觸犯了上帝的律法。根據《舊約聖經》〈利未記〉20章21節:「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亨利在 1528 年與法國使節會談時,以及在 1529 年離婚案件審判時,都提及這條律法使他深感良心不安。[5]
後來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亨利八世》一劇中,也從這個角度揣摩了國王的心境:
亨利王:「……我覺得上天不是用笑臉待我,它下了一道禁令,我的夫人的子宮如果會給我懷一個男孩,其作用只等於一座墳墓對死人所起的作用,因為她的男嗣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出世後不久就夭折。因此我想到這是上天對我的懲罰。我的國家本值得世上最好的太子來繼承,我卻享不到這個福。[6]
這段話或許更能生動的表達當時亨利王的恐慌。
亨利八世因訴求婚姻無效一案,與羅馬教宗決裂,並於 1533 年與安葆琳成婚。不幸的,安葆琳也無法為國王生下男嗣,她在產下伊莉莎白公主之後,流產兩次,而且第二次是個男嬰。看來亨利的罪仍然沒有完全清除,或者是犯了別的罪無法得到上帝寬恕。
但是這一次他不須經歷冗長的程序除去王后,因為安葆琳被控與五名男子通姦,包括與自己的兄弟亂倫,並企圖謀殺國王。這些指控是在國王默許之下,由安葆琳的敵對派陳訴,無力對抗的安葆琳最後在 1536 年 5 月 19 日被送上斷頭臺。[7] 不久亨利即與希摩爾成婚,愛德華王子隨之誕生。至此,亨利相信自己的罪已完全清除,英格蘭重新得到上帝的眷顧。愛德華的誕生一如日本男嗣的誕生,為統治者與人們帶來新生的喜悅和期待。
日本皇孫出生之後,日本政府原本要修改《皇室典範》,讓女子也能繼承皇位的提議暫時停滯。不過也有人提出警告,日本皇室未來終難避免繼承危機,因為皇孫不見得能順利孕育男嗣。
同樣的擔憂出現在都鐸王朝,雖然亨利有了男繼承人,但愛德華王子體弱多病,之後的三任王后無一能為亨利王再生一男,而瑪麗與伊莉莎白兩位公主又分別在 1534 年 和 1536 年繼承法案中,被認定為私生女,不得繼承王位。
亨利不得已在 1554 年要求國會通過新的繼承法規,明訂:萬一國王與王子愛德華未再有任何子嗣,王位傳予國王長女瑪麗及其後裔;若瑪麗也未有後,則傳予次女伊莉莎白及其後裔。[8]
此為亨利時代所通過的第三個繼承法案,法案中也給予國王未來透過特令或遺囑的方式,確認繼承人選次序。後來亨利在 1546 年 12 月 30 所頒訂的遺囑中,仍維持原案。
之後英格蘭歷史的演變,終究讓亨利八世的擔憂化為事實。愛德華六世於 1547 年即位,在 1553 年病逝,王位落到亨利八世的長女瑪麗手中,成為英格蘭第一位女王。瑪麗雖然成婚卻無一子半女,王位由次女伊莉莎白繼承,直至 1603 年英格蘭王位才轉回男君的手上。
總計達半個世紀之久,英格蘭都在女性統治之下。在這 50 年內,除了瑪麗即位之初爆發短暫的繼承戰爭之外,並沒有嚴重的內戰,但這已是後話。
亨利王時代或兩位女王的時代,英格蘭人民對女性統治有揮之不去的深層憂慮,這種擔憂主要來自心理層面與傳統文化,包括要有男嗣才能傳宗接代的觀念、對女人才德的鄙視,或對「牝雞司晨」的焦慮,這些心態在歐洲傳統社會,一如在傳統中國,均十分普遍。
若說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歐洲是一個女主的時代,並不誇大。
除了前文已提到的英格蘭女王瑪麗與伊莉莎白之外,在西班牙有依莎貝拉女王(Isabella of Castile, r. 1474-1504)、其女歡娜女王(Juana of Castile, r. 1504-16);在法國有攝政王太后路易斯(Louise of Savoy,攝政 1515-16;1525-29)及凱薩琳(Queen Catherine de Médici,攝政 1560-63;1574-75);在荷蘭地區有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攝政的女主,包括奧地利女公爵瑪格麗特(Margaret of Austria,攝政1507-15; 1519-30)、匈牙利女公爵瑪麗(Mary of Hungary,攝政 1531-55)、帕瑪女公爵瑪格麗特(Margaret of Parma,攝政 1559-67);在蘇格蘭則有攝政王太后瑪麗(Queen Mary of Guise,攝政 1554-1560)、女王瑪麗(Mary, Queen of Scots,親政 1561-67)。還有其他多位王后在君王出征或幼子在位時擔任攝政,可參見附表一。
這種由女人當家的局面,在 1559 年至 1600 年之間尤為突出,西歐地區此時期只有西班牙完全由男君統治。[9]
對近代早期的男性而言,一個女人站在整個政治結構的頂峰,當她是所有人的「頭」時,這情況與他心中奉以為常的規範和秩序背離。即使慣例上某些王國男嗣斷絕時由長女繼承王位;君主未成年或出征時,常由母親或妻子攝政,但傳統社會面對這樣的狀態仍會產生心理上的焦慮、理論上的困擾,或是實際的爭執。
史家很少能找到一般人面對女人執政的情況時,心中所產生的焦慮,不過政治菁英的感受則有痕跡可循,例如在英格蘭瑪麗女王登基之後,有一位新教徒說說:「啊!主,您把帝國從一個男人手中取走,交付給一個女人,似乎就是對我們英格蘭人非常不悅的表示。因為……當您的子民不值得擁有合法、自然而適切的統治者時,您就讓女人來統治他們。」他擔憂英格蘭人的苦難就此開始。[10]
又例如與亨利王同時期的蘇格蘭國王詹姆士五世(James V, 1513-42),在臨死之前得知他的王后產下一女(即後來的蘇格蘭瑪麗女王)的消息時,痛心長嘆:「這事有魔鬼跟著,它怎樣開始就會怎樣結束;它從一個女人來,也會斷送在一個女人手上。」[11]
雖然蘇格蘭司徒亞特王朝(Stuart Dynasty)並未在瑪麗女王手上結束,後來其子詹姆士六世(James VI, 1567-1625)反而承繼了英格蘭王位,統治英、蘇兩國。但詹姆士五世當時的憂慮是許多政治菁英共同的憂慮。
除了心裡的焦慮之外,女性統治時常產生實際的內戰或政爭。例如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Henry I, r. 1100-35)駕崩之後,僅遺一女瑪堤爾達(Matilda, 1102-67)可繼承王位。但英格蘭貴族不願接受女子為王,在溫徹斯特主教亨利(Henry of Blois)運作下,共同推舉國王的外甥史蒂芬(King Stephen, r. 1135-54)為王,並獲得教宗的承認。
瑪堤爾達眼見王位被奪,隨即由安茹地區(Anjou,為瑪堤爾達第二任丈夫〔Geoffrey V, Count of Anjou and Maine〕所居地)率兵進入英格蘭,與史蒂芬王之間爆發長達十八年的內戰,至 1153 年才完全結束。瑪堤爾達在內戰中雖偶有勝利,但未得到足夠的支持,在 1147 年被迫逃回法國。
這場內戰由其子亨利(Henry,即後來的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 1154-89〕)延續下去,最後是在史蒂芬同意任命亨利為繼承人之下,才結束了這場內戰。瑪堤爾達的失敗終使她無緣成為英格蘭第一位女王。
因女人攝政而導致的政爭更是不勝枚舉,例如法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çois I, r. 1515-47)的母親路易絲(Louise of Savoy, 1476-1531),在 1515-1516 及 1523-1529 之間因國王出征而兩度擔任攝政。路易絲攝政期間即遭受不少來自男性貴族的阻力,對她的職權多所限制;最嚴重的鬥爭是在 1525 年時,反對派推出與國王血緣最近的男性親屬查理(Charles de Bourbon),要求路易絲退位改由查理擔任攝政。[12]
其他相似的狀況在歐洲各地都曾出現,反對女性攝政的一方多是與王室血緣相近的男性貴族,他們提出的理由不外是女人無權掌有公共權威,或女人天性不宜主政等。這些女攝政常則需要支持者利用各種說法來支持統治的正當性,例如母后與國王之間血緣的親近性,天生的母愛所產生的保護之心與謹慎、細膩等特質,都可用來說服或降低反對的聲音。
但是歐洲中古或近代早期,整體的政治理論背景對女性統治偏於不利。就以英格蘭中古末期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家佛特斯鳩(Sir John Fortescue, c.1395- c.1477)為例,[13]他在 1462 年左右年討論到王位合法性時,他以國王手觸治病的神蹟(the King’s touch)作為說明的範例之一。
他認為只有正統合法的君王行此儀式時,才能真正治癒患腺病(scrofula,當時的人也稱之為國王的病 the king’s evil )的人,因為只有合法的君主才會得神的恩賜,而擁有神奇的治療能力。[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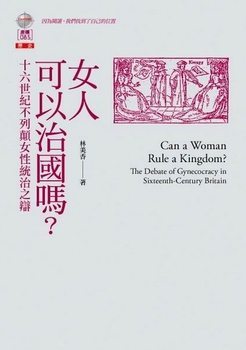
佛特斯鳩在作品中也提到女人與此儀式的關係。他說:「英格蘭的國王在王位上負有許多的職責,這些職責是女人的天性做不到的。」所以他認為一個女人即使貴為王后(或女王),來執行這個儀式都不可能有效。他寫道:
英格蘭的國王因受上天特殊的恩惠,具有某些能力(powers),而這些能力也是這個國家內的王后(queens 也可指女王)無法擁有的。英格蘭的國王用他們已被抹油的手,碰觸患了某種疾病的人民,即可去除並治癒這種疾病,這種病痛一般稱之為國王的病(the King’s Evil),除了此法無藥可救。而這種神賜的能力是王后(或女王)所沒有的。[15]
如果女人無法具有這種神奇的能力,就代表她不可能得到神特殊的眷顧,那麼女人的統治究竟是不是合法的?
統治者沒有了神的眷顧,也就令人不得不擔心,人民的苦難就此降臨。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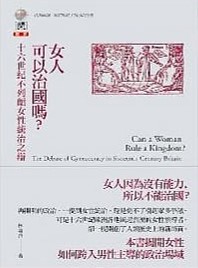
無論是引用聖經文獻,或是訴諸古老的傳統,這場辯論並不是單純的言詞交鋒而已,背後更牽涉當時宗教和政治利益的衝突。作者將這場辯論匯入十六世紀的思想文化脈絡中,還將視野擴大到同時代的歐洲大陸,增加了「女性統治」這個當代議題豐富的面向。
附表一:十六世紀歐洲的女王與女攝政
| 女王 (Queen Regnants) |
攝政的女主 (Queen Regents) |
|
|
西班牙 (Spain) |
Isabella of Castile (Queen of Castile, 1451-1504) Juana of Castile (Queen of Castile, 1479-1555) |
Isabel of Portugal (1503-39) Maria of Austria (1528-1603) Juana of Spain (1535-73) |
|
葡萄牙 (Portugal) |
Catalina of Spain (1507-77) | |
|
荷蘭 (the Netherlands) |
Mary of Austria (1505-58) Margaret of Parma (1522-86) Isabel Clara Eugenia (1566-1633) |
|
|
法國 (France) |
Anne of France (1461-1522) Louis of Savoy (1476-1531) Catherine de’ Medici (1519-89) Marie de’ Medici (1573-1642) |
|
|
納瓦爾 (Navarre) |
Catherine of Foix (1468-1517) Jeanne d’Albret (1528-72) |
|
|
英格蘭 (England) |
Jane Grey, 1537-54) Mary Tudor (1516-58) Elizabeth (1533-1603) |
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 Katherine Parr (1512-48) |
|
蘇格蘭 (Scotland) |
Mary Stuart (1542-87) | Margaret Tudor (1489-1541) Mary of Guise (1515-60) |
|
義大利 (Italy) |
Caterina Sforza (1462-1509, regent of Imola and Forlì) Caterina Cornaro (1454-1510, regent of Cyprus) Juana of Aragon (? -1517, regent of Sicily) |
|
|
波蘭 (Poland) |
Isabella Jagellion (1519-59) |
說明:表中所列年代為生卒年,而非統治或攝政時期。
[1] 《聯合報》2006 年 9 月 7 日,A8。
[2] 引自 David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Gloucestershire: Sutton, 1996), 104.
[3]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105.
[4]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21.
[5] Mortimer Levine, Tudor Dynastic Problems, 1460-1571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3), 55.
[6]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Henry VIII, II-4, 文見阮珅譯,《亨利八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466。
[7]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82-89.
[8] XXXV, Henry VIII, cap. 1,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3, 955.
[9] Lisa Hopkins, Writing Renaissance Queens: Texts by and about Elizabeth I and Mary, Queen of Scots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9. 關於十五、十六世紀的女主參見:M. B. Ryley, Queens of the Renaissance (Massachusetts: Corner House Publishers, 1982); Liza Hopkins, Women Who Would Be Kings: Female Rul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1); Sharon L. Jansen, The Monstrous Regiments of Women: Female Rule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0] Thomas Becon, An Humble Supplication unto God (Strasburgh, 1554), in Prayers and Other Pieces of Thomas Becon, ed. John Ayre (Cambridge, 1968), 227.
[11] John Knox,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Scotland, in The Works of John Knox, vol. 1, ed. David Laing (Edinburgh: James Thin, 1845; reprint, New York: AMS Press, 1966), 91.
[12] 參見Elizabeth McCartney, “The King’s Mother and Royal Prerogative in Early-Sixteenth-Century France,” in Medieval Queenship, ed. John Carmi Parsons (UK: Alan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94), 117-141.
[13] 佛特斯鳩在玫瑰戰爭時期,在蘭開斯特家族與約克家族的鬥爭中,他擁護前者的王位正統性,並曾隨亨利六世(Henry VI, r. 1422-61, 1470-71)流亡到蘇格蘭(1461-63)。他在這段時間寫了多部支持蘭開斯特統治權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有二:《讚頌英格蘭的法律》(De laudibus legume Anglie, 1468)及《論英格蘭的統治》(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1471)。參見Shelley Lockwood, Sir John Fortescue: On the Laws and Governance of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John Fortescue, De titulo Edwardi comitis Marchie, in The Works of Sir John Fortescue, ed. Lord Clermont (London: printed for private distribution, 1869), 70. 相關討論見Marc Bloch, The Royal Touch: Monarchy and Miracl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trans. J. E. Anderson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61)及Raymond Crawfurd, The King’s Evi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
[15] John Fortescue, Of the Title of the House of York, in The Works of Sir John Fortescue, 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