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八日那天,電台廣播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時,也指出大學生、專校生、中學生和小學生一律不受整肅。
毛澤東直接面向學生,把這些年輕人視為他最可靠的盟友。他們天真無知、容易操弄,而且很好鬥。最重要的是,他們渴望冒險與行動。「要靠這些娃娃們造反、來革命,否則打不倒這些牛鬼蛇神。」他對他的醫生這麼說。
八月一日,他發了一張私人便簽給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年輕人,表達支持之意。「造反有理!」毛澤東這麼告訴他們。兩個月後,這些學生已經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叫作「紅衛兵」。不是只有他們這麼做,北京其他地方的學生都集結起來,成立了名為「紅旗」或「東風」的組織。他們全都是受到一封廣為流傳的信件所啟發,這封信是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他在信中強力主張人民要和軍隊融為一體,在日常工作之外還要學習軍事技巧──此舉是沿用數十年前延安創下的典範。
然而工作組並不容許任何組織未經官方認可便成立。在解放後的那些年裡,公民社會已經逐漸被納入黨的控制之下,從獨立政黨、慈善組織、宗教社團和商會到工會,不是被除掉,就是受到黨的正式監督。中學和大學也一樣,地位受到認可的組織只有共產黨、共青團與少年先鋒隊。工作組命令毫無經驗的紅衛兵解散。
現在,紅衛兵在毛澤東的認可之下再度出現,他們誓死捍衛毛主席和他的革命。紅衛兵自視為毛澤東忠心的戰士,捨棄了他們平常的裝束而開始穿起軍裝。少數人的軍裝是從年紀較大的家人那兒找來的。張戎一加入紅衛兵後便趕回家,從舊箱子底層找出一件灰白色的外套,那是她母親在一九五○年代所穿的軍服。有些人則將工人所穿的長褲及棉襖改成樸素而鬆垮的制服,其中有部分還刻意做成破舊的樣子。一般而言,太合身的制服和光鮮的裝束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打扮,會引發不滿。皮帶是必備的,方便用來鞭打階級敵人。最後再戴上一枚有金色「紅衛兵」字樣的紅色棉布臂章,就是一套完整的制服。

然而並非每個人都能加入紅衛兵。最早組織紅衛兵小隊而受到毛澤東讚揚的那批年輕人,都是清華大學附設的菁英中學的學生。他們是高幹和軍官的小孩,而且都從父母那裡知道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是反毛主席的。其他中學裡力挺毛澤東並組成紅衛兵小隊的學生,其核心成員的父母也同樣是黨內官員。他們在充斥政治謀略的環境中成長,而且能透過其他人沒有的管道來取得機密情報。
最重要的是,他們早已相當具備組織能力,因為他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就參與過許多活動,從夏令營的軍事訓練到射擊會的射擊課程都有。在這個以無止盡的階級鬥爭的角度來描繪世界的政治環境中,他們都因為自己屬於革命階層而自覺生來便高人一等。
其中有許多人認為,只有家世最純正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紅衛兵,他們是資深革命分子的子女,只有他們才具備領導文化大革命所必要的階級背景,他們生來就是根正苗紅:「我們誕生在這個世界,就為了造資產階級的反、扛起偉大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兒子必須繼承他們父親奪來的權力。這就叫作權力的代代相傳。」有一句順口溜廣為流傳,內容是呼籲將所有階級背景較差的人排除在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北京,不到五分之一的中學生有資格進入以血統為標準、限制嚴格的團體。
紅衛兵一聽到毛澤東「造反有理」的戰鬥口號,就開始攻擊老師和校長。八月四日,即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收到毛澤東的鼓勵信三天之後,他們迫使校長和副校長掛上標牌,上面寫著「黑幫首領」。隨後數日,紅衛兵輪流毆打他們,有些學生使用棍棒,有些選擇拿鞭子或銅扣皮帶。副校長的頭髮也被燒焦了。

第一個死亡案例發生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六月下旬時,副校長卞仲耘已經在工作組的監督下遭受凌虐,學生朝她的臉吐口水、在她口中塞滿泥巴、強行把代表羞辱的高帽子戴在她頭上、將她雙手反綁並打得全身瘀青。現在工作組離開了,紅衛兵更堅決要除掉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八月五日下午,他們指控學校有五名管理人員集結成「黑幫」,朝那五個人潑墨汁、強迫他們跪下,用狼牙棒毆打他們。卞仲耘遭受數小時的凌虐後昏了過去,被丟進垃圾推車。兩小時後她終於被送到對街的醫院時,院方宣告她已經死亡。
從運動開始以來,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一直到處巡視,會見一批又一批的紅衛兵。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就已經去過北京大學,告訴群眾:「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她還提出了更深入的見解:「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
八月十三日,工人體育館舉行了群眾集會,此時出現了更多鼓勵。五個曾在數週前恐嚇過紅衛兵的平民,在數萬名學生面前被帶到台上示眾,並且被斥為「流氓」。他們遭到痛毆,被人以皮帶鞭打。主持這場批鬥大會的周恩來和王任重,完全沒有制止這些暴行。
隨後數日,北京的校園中瀰漫著一陣恐怖浪潮。在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的子女所就讀的名校北京一○一中學,十幾名教師被迫在鋪滿炭爐渣的小路上爬行,直到他們的膝蓋和手掌都血肉模糊。中南海對街的北京市第六中學,紅衛兵在審問室的牆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後來他們把這句標語重漆了一次,用的是受害人的血。
不過,最大的刺激出現在八月十八日,當天有超過一百萬名年輕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擠滿了所有空間。這些紅衛兵在剛過午夜時成團出發,並於破曉前抵達廣場。有些人分配到紅色的絲綢臂章,取代他們自製的棉布製品。他們在黑暗中焦急等待著,然後,就在耀眼的太陽於廣場東方升起之際,穿著鬆垮軍裝的毛澤東走下了講台。他在人群中走動了一下子,和他們握手。數小時後,一些學生被挑選出來面見毛澤東和他在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林彪發表了一段很長的演說,呼籲在場興奮激動的年輕人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當天的高潮是一個名叫宋彬彬的學生得到殊榮,她在毛主席的袖子別上紅衛兵臂章。宋的父親是資深軍官,自己則就讀於兩週前將卞仲耘虐死的那所學校。宋彬彬和其他紅衛兵首領已經私下把那則消息通報給北京市黨委了。毛澤東在此起彼落的閃光燈前問她的名字有什麼含意,她回答是「文質彬彬」,毛澤東便說:「要武嘛!」於是「宋要武」一夕成名。

* * *
天安門廣場的集會過後,一陣暴力的浪潮吞噬了北京。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被打死,教務主任上吊自殺。在另一所位於北京師範大學附近的中學,校長被命令站在烈日下,紅衛兵拿沸水往他身上澆。還有一所附屬於北京師範學院的中學出現了更恐怖的手段,一名生物老師被推倒在地上毆打,並被人拉著雙腳拖行過學校大門、拖下樓梯,頭部不停碰撞水泥地,遭受數小時的折磨後死去,接下來,其他被抓起來批為牛鬼蛇神的老師則被迫輪流毆打她的屍體。在小學裡,學生的年紀都不超過十三歲,卻有老師被迫吃下指甲和糞便,也有些老師被剃頭並被逼互相掌摑。
紅衛兵也會對付自己的同學。多年來他們一直對家庭背景不好,但通常表現優異的學生滿懷怨恨,這些學生只能靠成績出人頭地,而非身分地位。短短兩年前,毛澤東才對他眼中極度菁英取向的教育制度表達過反對之意,要求限制「剝削家庭」的孩子入學。紅衛兵現在非常想要一個永久歧視的體制。紅衛兵生來就是紅的,而他們的敵人生來就是黑的。階級背景差的學生被關押、被迫在校園中做苦工、遭受羞辱,更有些人遭凌虐致死。出身「不紅也不黑」的學生,例如文書人員、辦公室職員、技師和工程師的子女,則獲准協助紅衛兵。
暴力也蔓延到街頭。「資產階級學閥」是紅衛兵的首要目標之一,他們被指控的罪名是「毒害社會主義制度」。學生們追查吳晗、鄧拓及其擁護者達數月之久,審視他們的文章、短篇故事、劇作和小說,想找出任何一點修正主義意識形態的線索。現在,等待多時的他們終於可以出手了。鄧拓已死,吳晗也已入獄,但是還有許多其他目標。劇作家田漢寫過劇評讚揚《李慧娘》,這件事惹怒了毛澤東,屢次被拖到臨時搭建的台上,脖子上掛著沉重的標語牌,被迫下跪並遭到毒打,在場群眾則高喊著:「打倒田漢!」
其他著名的知識分子也是這波暴力浪潮中的攻擊目標。著有小說《駱駝祥子》的知名作家老舍曾在一九二○年代時擔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講師。他和其他許多人一樣,1949 年後都滿腔熱情地為新政權服務,然而他的背景卻使自己惹禍上身。天安門廣場的大集會後數天,他和其他二十人被卡車載到孔廟;在那個寧靜大院的古老柏樹蔭下有幾百座石碑,上面刻有歷代以來成功通過科舉考試的秀才之名。
一百多名第八中學的女學生站成兩排,形成一條人廊。當受害者被推著走過這條人廊時,紅衛兵對他們拳腳相向,同時高喊著:「打倒黑幫!」接著,他們的脖子被掛上標語牌,上面寫了姓名與罪狀,同時有一名官方攝影師全程紀錄。毆打持續了數小時。一天後,老舍的屍體在他童年住處附近一座湖的淺水區被人發現,口袋裡還留著一本毛主席的詩集。

被認為階級背景不好的平民也會遭到公開迫害。一週前在工人體育館被貶為「小流氓」的受害者當中,有一名的家人也被紅衛兵追查到了。他們住在離發現老舍屍體的那座湖不遠處,家中的父親是個貧困老人,名叫南保山,被人拖到街上亂棒打死。他的第二個兒子則遭到毆打並關在家裡,數天後在家中渴死。
當地街委會早已經向紅衛兵告發過南保山及其家人了。整個北京的牆上都貼出了地方黨委會或警察廳簽發的名單,列出許多人的年齡和階級背景。有時候他們的罪狀會被詳列出來:「解放以來一直懶散誤事。」不過他們更常被直接打成「地主」、「反革命」或「壞分子」。
隨著紅衛兵追捕特定目標,「通緝」告示也出現了。在公園、皇宮庭園和古剎,到處都看得見受害者遭人以繩索抽打、用棍棒痛毆或以其他方式在歡呼群眾面前受到羞辱和凌虐的場面。一名英國領事館的職員便看到一個老人步履蹣跚地走出一棟被紅衛兵改成臨時監獄的室內市場,寫著罪狀的牌子垂得跟膝蓋一樣低,他臉色發黑,上衣背後還有血跡。「悲慘程度僅次於這個場面的,就是兩位老太太被幼小孩童丟石頭的情景。」
翟振華是菁英學校裡加入紅衛兵的女孩之一。她第一次見到朋友解下皮帶把一名受害者打得衣服上滲滿血跡之後有些畏縮,但她又不想落於人後,所以還是打了下去。一開始她避免和受害者四目相對,只能靠著想像他們都是密謀復辟舊社會的罪犯,來合理化自己打人的行為。但是打過幾次之後,她就知道訣竅了:「我的心腸變硬了,我也看慣了血。我像機器人一樣地揮動皮帶,打下去時腦中一片空白。」
另一個紅衛兵後來回想,自己起初對學校中爆發的暴力行為感到震驚,但很快就體驗到血腥滋味的情形:「我剛開始打人時,不知道該怎麼做。我很軟弱。但我很快就能比其他學生打得更凶猛了:無論你打得多用力,我都會打得更用力,就像野獸一樣,一直打到我的拳頭疼痛為止。」孩童是最狠毒的,對少數孩子而言,把階級敵人打得不成人形是在玩遊戲,就和鬥蟋蟀一樣。
街委會和警察所列出的目標人物,許多都被捕並遭到下放。紅衛兵在北京清除階級敵人,要讓首都「更加根正苗紅」。老人脖子上掛著標語牌,雙臂以繩子綑綁,被帶去遊街示眾。不久之後,北京的火車站便有大批衣衫襤褸的人被送到鄉下;這些受害者估計有七萬七千名,只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略少。
最嚴重的殺人行為發生在北京市郊。在大興這個擁有砂質土壤、能種出甘甜西瓜的縣裡,地方幹部下令消滅所有地主和其他壞分子,包括他們的子孫。這些幹部的理由是,傳聞階級敵人即將強行報復,推翻地方黨支部並殺死往日折磨過他們的人。

接下來,幾個人民公社謹慎協調,發動了一夜大屠殺。黨的激進分子與地方民兵聯手將受害者關在家裡,或臨時權充的牢房中。他們逐一被殺掉,有的被棍棒打死,有的被鐮刀戳刺而死,或者被電線勒死。有幾個人是被電死的。孩童被倒吊起來鞭打。一個八歲女孩和她的祖母則遭到活埋。一共超過三百人被殺,有些是全家遇害,包括小孩在內,因為凶手要確保不會留下任何活口,以免日後遭到報復。屍體多數被丟進廢棄的水井和亂葬崗。其中一處的屍臭味強到令人無法忍受,村民只好把屍體挖出來,改丟進水塘裡。
一名人民解放軍軍官致電北京,通報大興的屠殺事件,立刻便有一份報告送到了文化革命小組,但沒有人出面制止屠殺。
一週前,公安部長謝富治已經指示過一批警官要「支持紅衛兵」。他囑咐警察要「跟他們說說話、交交朋友。不要命令他們。不要說他們打壞人是錯的。如果他們一怒之下打死了人,那就算了。」他這次的演說內容廣為流傳。
北京的受害人數並沒有確切統計數字,但是八月下旬時,每天都有超過一百人被殺。一份黨內部文件就報告了八月二十六日有一百二十六人死在紅衛兵手中;翌日有二百二十八人;再隔天是一百八十四人;八月二十九日則是二百人。根據一項保守估計,到了九月下旬,第一波暴力浪潮減弱時,至少已經有一千七百七十人喪命,其中尚不包括那些在北京市郊遭到屠殺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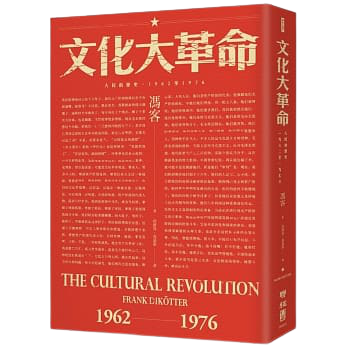
在共黨幹部、政府官僚、解放軍和紅衛兵的鬥獸場之外,還有一段真正屬於普通中國人民的文革史。普遍中國人民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究竟遭遇到怎樣的衝擊?他們如何面對毛澤東一人由上而下發起的報復清算運動?如何自保、甚至從中尋求新的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