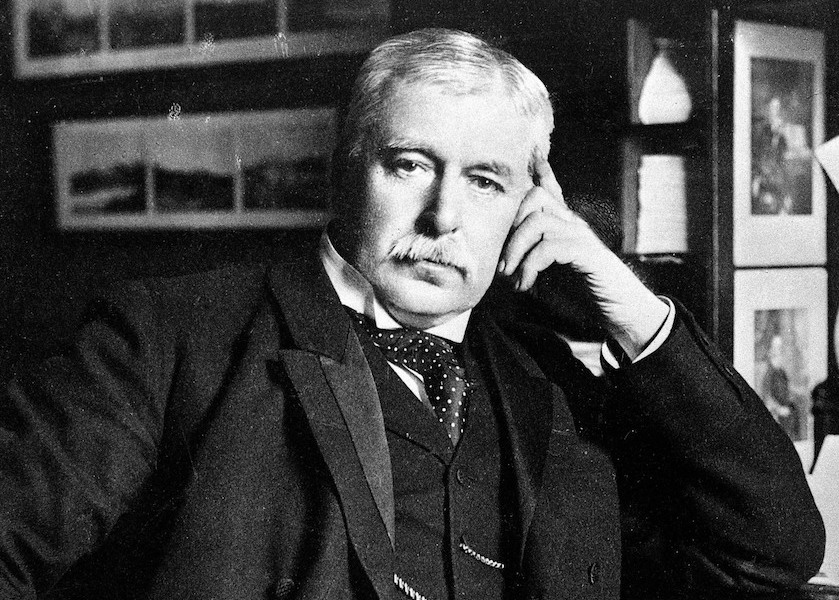絕世好官,卻困擾於自己的容顏
宋朝有一位名叫劉宰的文人,歷經艱辛考上科舉,最終實踐他的夢想,為地方百姓造福。他為官時,舉凡地方上自稱「空雲子」、「寶華主」等以妖術惑眾的 seafood(師傅),都被大力整頓,一律禁止;凡是有假借神明之意,胡作非為者,則拆毀邪廟。
劉宰視人民為子女,若轄區內有適齡的少年少女未嫁,他甚至會親自過問作媒,解決在地生育率和未婚問題。如此這般的好官,卻有著「天黥」的顏損障礙。
天黥是指臉上布滿痘疤因病毀容,導致的原因可能是感染水痘,也可能是其他疾病。從劉宰的著作中,可以知道他染病後鬱鬱寡歡,即使已經做出一番政績,在官場頗有聲望,但臉部外觀的變形,使劉宰對自我認知產生了變化。
劉宰曾經只是走在路上便驚嚇到路人。他多次哀嘆年輕時無緣遇到良醫能改善自己容顏,但是等到了年華老去,求醫又有什麼意思呢?[1] 情緒低落跟憂鬱,加上疾病導致他身體功能的衰退,「某病惟日甚,貌若天黥,加之髮脱,而不可勝冠,手顫而不可執筆」,也降低他繼續任官的意願。[2]
歷任地方官多年後,劉宰決定辭官回到老家江蘇金壇隱居,朝廷屢詔出仕不到,但仍有諸多官員願意引薦他。他總是對引薦他的官員委婉表示,因為自身個性(當然還有政治鬥爭等問題)以及天黥的關係,所以不適合當官云云。[3]
<當官致仕與否,是個人選擇。但是以天黥作為理由,表示當時的人認同顏面損傷不適合做官的說法。雖然宋代已經沒有像唐朝那樣採用身言書判來任官,而是以科舉取士,但是外貌仍被視為個人評價的一部份。官場上的送往迎來、日後的升遷、人際關係的互動,無不跟人的形象外貌有著一定的關係。

更何況,傳統儒家觀點認為,外貌是內心的投射,當身心受到道德的浸潤時,外在會展現內在精神的樣子,所以要求君子要有威儀,舉手投足都要合宜。[4] 但是實際上,氣質的展現是很複雜的一件事,也不能保證人們不會因為外在而倒過來認知對方的內心。
也許對劉宰來說,除了政治理念的問題,還要想辦法抵抗對外貌的自卑和外界的歧視,對他而言實在是太大的負擔。最後,劉宰在家鄉隱居,讀書著文作詩,度過餘生,享年 74 歲。
人帥真好,人醜吃草,顏面損傷則是……?
大家看完這個故事,是不是會覺得當事人想太多了呢?劉宰遇到的歧視看起來還好吧?他隱居都是因為政治鬥爭啦!容貌真的有醜到不想當官?因容貌歧視常遭遇的情況,可能因為個人而異,以下有一些案例,可以讓我們能體會外貌對心理層面的影響:
一、質疑當事人能力不佳
東漢明帝時期,有一位操守品行優秀,受到朝廷徵召入朝為官的文人,名叫承宮。他多次針砭時政,對朝政提出諸多建言,頗受敬重,名聲甚至傳入匈奴之地。
當時北單于派遣使者求見承宮,明帝指示承宮,要他好好打扮,承宮說:「夷狄迷惑於臣的虛名,並非真正知道臣是怎樣的人。臣容貌醜陋,難登大雅之堂,還是選擇相貌威儀的人接見才好。」於是明帝改派大鴻臚魏應代替他。
類似的故事還有歷史上曹操要接待匈奴使臣,但自認容貌醜陋,擔心匈奴使節瞧不起,便請崔琰假冒他,接見匈奴使臣。
曹操的容貌如何?《三國志》以魏為正統,均有提及劉備跟孫權的長相,反而是曹操的相貌沒有記載,可知曹操的長相長得不如孫劉,還是不提為妙。而崔琰是當時的美男子,《三國志》裡記載他「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由此觀之,也不意外曹操要請崔琰假冒自己。

就好比現代奧運開幕式要找人演唱主題曲,爆牙的天籟之音主唱也只能默默地躲在幕後,讓電視上的漂亮小美女使用她的聲音對嘴,這告訴我們:無論哪個年代,長相很重要,重要到連假冒國家門面都可行的程度。
二、訝異當事人竟然可以表現的這麼好
明代徐大山在龍泉縣時,曾經有一僧人獻給他一床楮做的被子,還題詩拍馬屁讚美徐大山。徐大山非常高興,舉辦宴會招待僧人,並讓一名婢女隔牆唱歌助興。僧人聽聞這曲調悠長美妙,忍不住偷窺,發現是一名年老的婢女,而且滿臉痘子(天黥),醜得不可言喻,所以又做了一首詩說:偶然聽見隔壁傳來一首歌,優美精巧宛如七寶堆砌的簾幔中藏起來的花,看了一眼才知道還是不見最美。[5]
婢女唱歌給一位心猿意馬兼拍馬屁的僧人聽,還要慘遭對方羞辱?
三、對當事人施加肢體暴力
歷史上知名的帥哥潘安出門閒晃,妹子們都爭相迎接。左思醜陋無比,想效法潘安帥氣出遊;卻遭遇一群歐巴桑吐口水,他只能沮喪而歸;晉朝張載(張孟陽)則是乘車出門時被小孩兒扔石頭亂砸,只因為他是醜男。單單因為容貌,就得無條件遭受他人暴力相向。
四、對當事人十分不客氣
三國時代的管輅容貌醜陋,讓人覺得沒什麼威嚴,大家都喜歡管輅,但是不怕他。即使他已經是當代最偉大的算命師,堪輿、相術、卜卦無一不精,人又孝順,友愛兄弟。不過這些還是沒有讓他贏來大家的尊重,對他沒有半分敬畏之心。
五、感情或婚姻總是出問題
魏晉時代,阮德如的妹妹要嫁給許允,《世說新語》對於她的長相只有兩個字形容:奇醜無比。可以想見的是,新婚行完交拜禮後,許允一見新娘的長相就逃出新房。家人對此都十分擔憂,畢竟是世族聯姻,得罪親家就不好了。
後來許允的朋友桓範勸許允說:「阮家既然嫁個醜女給你,必定是有原因的,您應該仔細觀察。」許允轉身回房,一見新娘,立刻又想逃出去。新娘反應很快,知道他這一走再也不可能進來,馬上死命拉住他的衣襟要讓許允留下。
許允在死命掙扎中問她:「婦女應該有四種美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妳有其中的那幾種?」新娘繼續拉著他不放:「我缺少的只有容貌!可是讀書人應該要有各種好品行,你有幾種?」許允自豪地表示說:「樣樣都有。」新娘十分激動大喊:「品行當中以美德為首,可是你貪戀美色,不重品德,怎麼能說樣樣都有!」許允聽了,臉上露出慚愧的神色,從此夫婦倆便互相敬重。
以上的案例都是當代十分優秀的人才,可惜容貌和社會偏見連結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的專業已經不重要了。即使是現代的開放社會,根據陽光基金會針對顏面損傷者的調查,他們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歧視狀況就跟上述的各種情況一樣。[6]為了身體特徵而遭受不友善對待的情況,從古自今都沒有改變。
社交問題對於顏損者心靈的影響
因為燒燙傷、口腔癌、小耳症,或者天生胎記等各種原因而產生的顏面損傷者,對於身體與外貌的自我認知,以至於他們的生活品質、自尊與人格,以及社交上都會產生各種問題。
許多顏損者像劉宰一樣,身心狀況越來越糟,甚至有的成為多重障礙者。這時候對顏損者來說,重新建立自我認知是非常重要的。來自朋友或社會的支持當然能減少他們的焦慮;但是有時候,朋友的支持也會增加他們的情緒困擾。陽光基金會研究報告指出,朋友的存在對顏損者的內心造成了複雜的情緒,雖然朋友的支持有鼓舞士氣的作用,但於此同時,患者本身也會想起自己的社交地位跟容貌,使他被迫面對現實,受創的真實自我以及希望成為的理想自我之間造成的落差,產生患得患失的情緒。

近代的顏損者生活困境
有留下記載的顏損者大多是仕宦家庭,生活無虞。如果換成社會底層民眾,他們的狀況又是如何?
古代對這方面資料並沒有太多,在《本草綱目》當中的確記載不少遭受燒燙傷患者的醫療狀況,但是病患之後的生活狀況到底如何,我們並不清楚。或許從近代臺灣的記載,可以略窺一二。
1980 年,臺灣的沈曉亞女士,為了家庭經濟,放棄上學的機會,但她沒有放棄學習,自己買器材在家中做工科實驗,卻發生燒傷意外導致大面積燒傷。在漫長的復健後,她重新振作走出家門,可是總有人對她口出惡言,日常生活常遇到商店及服務人員不公平地對待;被陌生人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找工作時也總是被拒絕。
這一切使得她自卑又孤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最後,沈女士決定在勵友中心當電話志工,運用她的經驗幫助他人。某次她得到記者訪問的機會,將自身經驗出版成《怕見陽光的人》一書。

在那個大部分顏面損傷者閉門不出的年代,第一次有人公開詳細敘述顏損者的心路歷程,沈女士表達了受創之後的心境、工作困境、愛情關係上所遭遇的苦痛,引起了媒體記者的探訪,及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在 1981 年由熱心公益的大眾及燒燙傷友協助,成立了陽光基金會,1989 年則有羅慧夫基金會成立,專注於先天顏損者的醫療。
社會大眾的關注使得顏損者的困境開始轉變,1980 年各個領域指出顏損者所遭受的問題,包括學校拒收,就業問題。尤其臉部受損者在就學、就業時往往被視為身障者,一開始就被學校及工作拒之門外;可是在身障鑑定時又被判定為正常人,無法享有身障福利。
曾有傷友遭遇工作意外,全身遭受程度不一的灼燙傷,歷經多次手術,仍臉部攣縮、手指扭曲,之後十年他到處求職,但沒有人願意用他;也有小耳症患者,特地從基隆趕到臺北,打算參加鐵路局招考,但是一開始的「體檢」便讓他無法報考,[7]這些都是很常見的情形。
何況當時顏損者們的教育程度大多不高,甚至只有小學程度,不但無法為自己爭取權益,對於如何獲得醫療與社會福利方面的門徑,他們茫然無知,到最後就算想找份安定的新工作,也十分不易。沒有相關社福機構,也沒有庇護工廠,他們求助無門。
所幸,近幾十年開始有相關庇護性職場成立,顏損者開始能在社福機構的附屬單位工作,政府跟社福機構合作提供工作機會。[8] 比起 1980 年代,因為大眾對於顏損者態度有改善,較以前相對容易找到工作。這時候主要差別在於只要態度積極,具備基本核心能力,雖然生理功能有所損傷,但較容易返回職場。
社會福利或法律幫助得了他們嗎?
早期對顏損者的關注對象都是後天顏損者,焦點在於如何醫療,以及法律權益的維護。
《唐律疏義》提及在打鬥或群毆中,若是損傷當事人容顏,讓傷者失去耳朵、鼻子、眼睛、用燒開的液體潑人致傷等,都必須由官府開啟訴訟進行司法程序,不可以私下解決。訴訟結果確定,傷害他人者必須服徒刑跟刑罰。現代臺灣的民法及刑法中,也能針對致人顏面傷殘部分提起訴訟,有助於維繫傷者的利益。
至於天生的顏損者,或是沒有造成肢體損害的顏損,一直以來並沒有獲得太多關注或是協助。
在社會救助方面,1980 年臺灣政府公布殘障福利法,最初提到的身心障礙範圍,並沒有包含顏面傷殘,而殘障福利法本身偏向宣示意義,內容並不明確。因此政府於 1990 年再次修訂殘障福利法,制訂細項服務內容,將顏面傷殘納入身心障礙的範圍(殘障福利法第三條)[9],顏面損傷者才得以享有各項福利以及政府的救濟措施,甚至是就業服務。
遺憾的是,除非是因病或受創導致的多重殘障者,否則顏損者能取得身障手冊或證明的機率極低。首先,相關單位發給手冊,主要針對失能的部分評鑑,而顏損者並不完全等於身心障礙、工作能力或其他方面有任何問題,。
其次,站在醫療的角度來講,整容或治療手術若是能修補當事人顏面,回復正常使用功能,便已達成目標,美觀不在討論的範疇當中。因此,部分顏損者是沒有身障手冊,或者是領取其他障別手冊的資格。[10]

在社會保險部分,早期燒燙傷無法申請勞工保險殘廢給付,這是相當不合理與不公平的規定。1998 年在大眾的關注之下,陽光基金會與傷友們共同辦理了「燒死悲哀,燒不死含眼淚」公聽會,為身體燒傷者爭取權益。
在公聽會之後,政府修改了相關規定:1999 年行政院勞委會函公布:「補充、增列勞工保險殘廢給付障害項目『身體皮膚、排汗功能喪失者』及審查標準。」[11]從此以後,顏面損傷也被納入保險給付的部分,比如民眾若因交通事故造成頭部、顏面部或頸部受傷,經治療一年後仍留下有礙外觀的顯著醜型時,可申請強制車險的身障給付。
法律的修正使得顏損者處境改善,健保也能給付整型治療費用,但仍有不少需要自費的部分,且一般私人保險公司也並不給付。甚至,顏損者想要保險時,可能會面臨保費增加,或是保險項目排除的情形。
因此,顏損者之中能享受到社會福利的人,與其他障別人士相比,其比例較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因為顏面損傷所帶來的負面困境並沒有消失,原本需要的心理諮商或社會福利支持,卻常因沒有身障手冊的緣故,無法獲得合理的援助。
顏損者的處境會因為大眾的關注而有所不同
政府曾經在北高兩地,調查社會大眾對顏面損傷者的接納度,發現與顏面損傷者接觸過的民眾,之後會展現出較高的接納態度,其中有高達七成以上的填答者,對顏損者的接納態度是正向的。
分析結果後也發現,如果有接觸過陽光及羅慧夫基金會,或是聽過臉部平權的民眾,對於顏損者的評價會比較高,他們清楚認知到:顏損者實際上跟大家並無不同。
從以前到現今,我們能發現顏損者的處境是可以越來越好的,從早年顏損者大多躲在家中,無法社交,沒有工作;1980 年代出外工作被拒,上學被霸凌;到現在能有機會讓他們證明自己與常人無異,這都是你我以及無數的人士協助而成的。
臺灣的人情味一直都是我們最引以為傲的無形資產,即使每個人的外貌不同,可是內心都是一樣溫暖柔軟的。當其他人想走出黑暗,站在陽光之下的時候,我們都將成為太陽,照亮他們。

黃博煒 八仙塵燃事件傷者/《但我想活》作者
▌主持人:胡川安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主編
▌時間:1/17 (三) 7:30-9:00PM
▌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敏隆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9號12F)
▌報名表單:https://goo.gl/1GbeJ8
[1] 宋.劉宰,〈謝薦醫〉,《漫塘集》,卷1。
[2] 劉宰,〈回知盱貽劉都統倬賀除司令〉,《漫塘集》,卷16。
[3] 劉宰,〈趙守賀除司令〉,《漫塘集》,卷15。
[4]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頁29-31。
[5] 明.葉子竒,《草木子》,卷4。
[6] 陽光基金會,〈社會大眾對於顏損或燒傷者接納度調查思考〉,《陽光基金會九十三年度執行成果報告》,臺北:陽光基金會,未出版,2004
[7] 聯合報,〈四肢正常不被視為殘障,就學就業,處處受到歧視〉,1983-09-05,第三版面。
[8] 孫鶴珍,《生命樂章之合奏——專業團隊成員為燒傷者提供服務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85。
[9] 何華國,《傷殘職業復健》(高雄:復文圖書,1991),頁53;459。
[10] 江佳鍬,《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協力關係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附錄訪談。
[11] 民國101年,農民健康保險也新增「皮膚障礙」之身心障礙給付等要項,《內政部101年10月5日台內社字第1010316557號函》。
- 沈曉亞,《怕見陽光的人》,臺北:聯亞,1980。
- 何昭中,《燒傷病人急性期身體心像改變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臺北:國防醫學院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何華國,《傷殘職業復健》,高雄:復文圖書,1991。
- 林淑英,《顏面傷殘者自我概念與社會適應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 林珍妃,〈顏面傷殘者的社會心理問題〉,6;1《長庚護理》(桃園: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1995),頁51-53。
- 約翰.奧尼爾(John O'Neill)著,《身體形態:現代社會的五種身體》,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
- 孫鶴珍,《生命樂章之合奏——專業團隊成員為燒傷者提供服務之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陳惠萍,〈常體之外:「殘障」的身體社會學思考〉,發表於「2003年社會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臺北:政治大學,2003。
- 陽光基金會,〈社會大眾對於顏損或燒傷者接納度調查思考〉,《陽光基金會九十三年度執行成果報告》,臺北:陽光基金會,未出版,2004。
-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