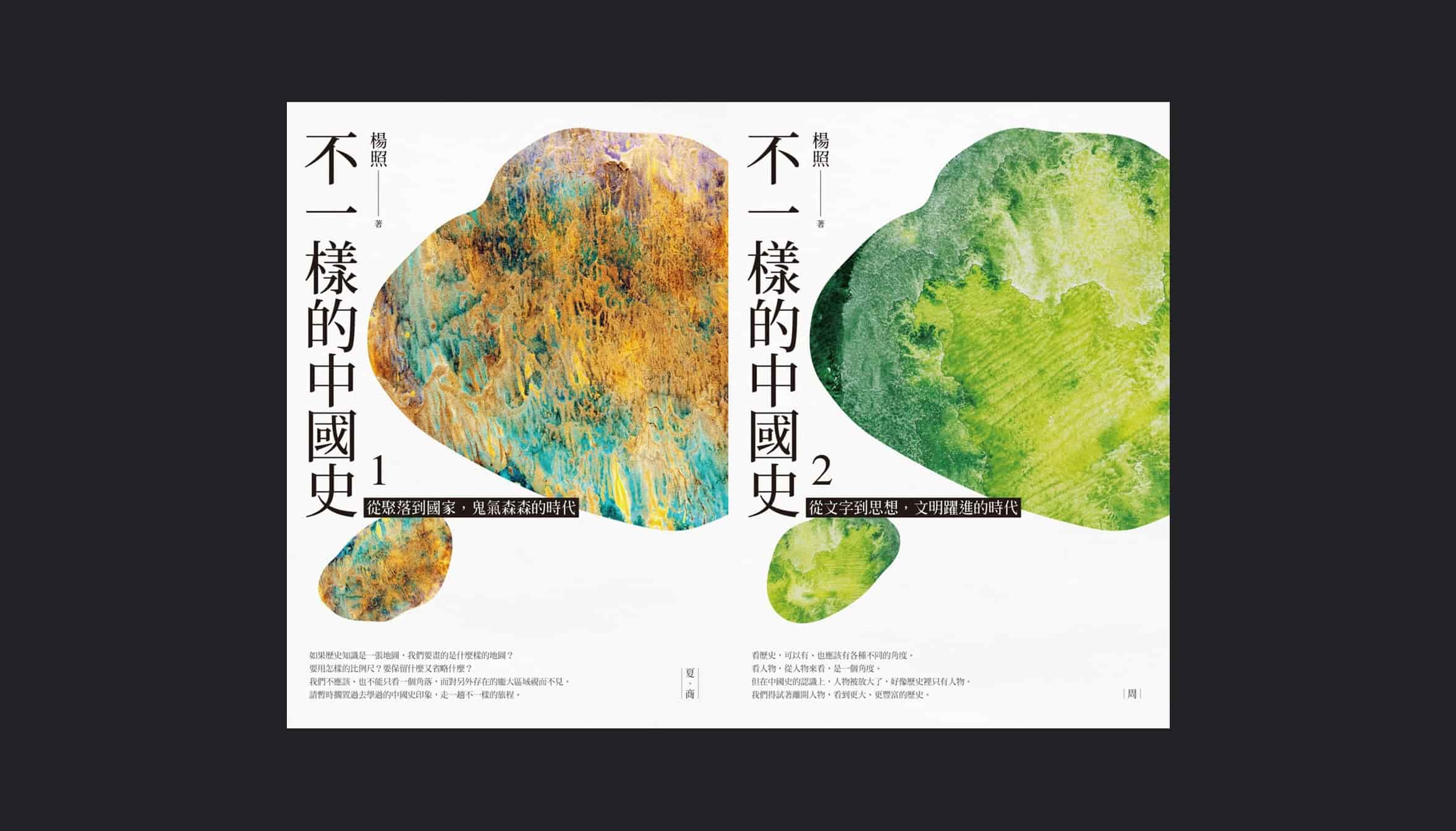在當今的書市中,《不一樣的中國史》罕見地以系列套書問世,引人注目。從序文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宏大企圖,不僅頻以錢穆《國史大綱》說明「通古今之變」的重要,似也隱含此系列著作的本意。
不過即使如此,作者仍為這套「通史」打了預防針:「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訴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這句話頗是微妙,似乎可以推測出兩層意思,表面指的是本書的論點並非權威,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潛台詞似乎頗有比肩前輩之意:《國史大綱》是一家之言,我亦一家之言耳?後者是筆者妄圖猜測,還請作者見諒。
無論作者意圖為何,書評檢視書籍撰寫內容與目的是否相合,自是第一要務。筆者的研究領域主要著力於先秦,對其他未出版的部分不敢置喙,只檢視前兩冊的情況,在拜讀過後,發覺書中不僅有許多說法與現今學界主流認知不同,有的甚至與學界共識大相逕庭。以下提出本書一些問題,將書中內容與學界認知有明顯落差之處,與作者討論,也供讀者參考。
本書的一個問題是過度詮釋,作者可能依賴二手研究,未查一手資料,因此某些說法顯得天馬行空。其中一個比較明顯是「商人鬼神論」。
本書反覆講商人的鬼神世界裡充斥著「我的祖先比你的祖先強」(頁 159)、「今天我要攻打你,當然說你的祖先不在我的祖先的神靈領域裡,所以我一定會打贏你。」(頁 170)、「我可以靠我的祖先之威壓過你的祖先,我可以讓你的祖先降禍於你,不保佑你!」(頁 249)、「要確定誰比較厲害,最徹底的方式就是比比看,你後面的神和我後面的神,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盟主。」(頁 268)
這種聽起來像是通靈王大戰的詮釋敘事,固然有趣,卻嚴重偏離資料反映的現象。事實上,商人祖先有後代子孫添亂、降憂、降禍的現象,但商人求祖先去給敵人搗亂、作祟者,卻十分罕見。此外,商人固然會求神明庇佑軍事行動,但神靈之力也就限於己邦、己身,沒有「我祖先壓過你祖先」這種超譯說法。
又如本書提及:「祖甲改革建立一個鬼神系譜,只有這幾個祖先是被承認的,確定下來後就不能輕易更改,變成一個封閉體系。」(頁170)此段是指祖甲的周祭,但這種說法也背離甲骨文材料,因為周祭並不封閉,只要後來有商王過世了,他就會被納進周祭體系(除了廩辛,但他的存在是個謎)。祖甲死後還有康丁、武乙、文丁繼位為王,他們及其配偶都會被納進周祭系統裡祭祀啊!怎麼就封閉了呢?
而且,商人不是只有祖先神,還有自然神。作者只看到商人崇拜祖先,而沒看到商人祭祀社稷河岳,於是說出:「周原甲骨中,多次出現『相土』的名字。這正是商人先公中和動物關係最密切的一位。到周代的文獻中,『相土』轉型變成了『社神』,這是最早的土地公。」
這段不到百字的論述,就有好幾個問題。比如周原甲骨沒有「多次」提到相土之名,最早的土地公也不是相土,而是早在殷墟甲骨就有祭祀的「社」,它才是真正的土地神。
本書另一論點是「青銅器皆禮器論」(第一冊頁 137、頁 142、頁 308)。作者認為,青銅器絕大多數都沒有實用功能,甚至說青銅兵器未必是用於實戰(頁 137)。但是只要對青銅器稍有認識的人便知道,不少青銅器的器底都有炭火煮食的痕跡,青銅鼎也有類似今日臭臭鍋、小火鍋的溫鼎。隨著考古發掘,這些知識已經越來越豐富,也越來越普遍。好奇的讀者在網路上就可找到不少相關學術資訊。

此外,本書有些關於傳世文獻的論述,也讓人感到疑惑,如第一冊論《尚書》語言詰屈聱牙,主張《尚書》中文字和語言的關係疏遠,又說「像〈盤庚〉中那樣的文字,怎麼讀都覺得困難,感覺與後來的文字不是那麼親近。」(頁194)甚至牽合道士符籙為說,暗示這些文字不是真實語言而是神秘語言。
然而,甲骨卜辭之所以難讀,一是殘片殘辭多,二是這些記錄流通範圍只在王廷與貞人機構使用,你知我知王知即可,有語法規律,但不必寫得特別清楚。而金文難讀,與《尚書》類似,一是古語與今語懸隔太遠,很多文字已經斷絕不用,今人難以查考。二是古代貴族好用成語,如綽綰、屯魯、前文人、余一人等,此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成語書〉已有詳說。
甲骨、金文、《尚書》並非是神秘文字,它們亦有書面語的成分,需要接受訓練,才能解讀。我們後代人看不懂,不代表那些文字就是脫離實際語言。筆者直接將材料攤開在這裡,給大家挑幾個句子翻譯:
- 《尚書‧康誥》:「嗚呼!封,汝念哉!」(哎呀!阿封你牢記啊!)
- 《尚書‧費誓》:「嗟!人無嘩,聽命!」(哎呀!大家不要吵,聽我說!)
- 《尚書‧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嘩!」(欸!將士們,聽我說不要吵!)
讀者覺得,這是脫離實際語言的文字嗎?《尚書》中有些篇章有口語的成分,有些篇章很官方文書,不能一概而論。說《尚書》是種神秘語言,只是因為它難讀懂,是古人不想讓文字被別人掌握,這樣的說法很可能會誤導讀者。
再舉一個誤解之例,本書第一冊提到:「對待人方、鬼方、共方,那是『伐』,行動之前要進行的是關於戰爭、戰事的卜辭。然而,對待『羌』以及其他幾個今天無法傳寫為現代中文的民族,甲骨文的用字卻是『獵』,行動前的卜禮內容也是『卜獵』。」(頁 213-214)
這段話有幾個問題,首先,就筆者目力所及,幾本常見的甲骨文字典中,都沒有「獵」字,一般抓羌人動詞是用「獲」、「圍」、「執」等字[1]。再來,武丁時期的甲骨卜辭,就有「伐羌」的記載,並非如文中所說對人類用伐,於獸類用獵[2]。
最後,在本書中,「商視羌非人論」是個重要的觀念,但從甲骨卜辭證據上,並沒辦法印證這種說法。假設商王朝從不把羌人當人看,那麼該如何解釋「令多馬羌禦方于……」(合 6761,賓組)這條卜辭呢?這是一個羌人在商王底下當官的明確例子,似乎看不出來商人有哪裡不把羌人當人看了。
事實上,商人對於異族的處置方法,往往採取分化與鎮壓並濟的模式,因此也有不少羌人歸順商人,甚至就在商王手底下做事情的。實在很難用作者的「商人不把羌人當人看」一言以蔽之。
當然作者的說法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其來源是對「羌」字形體的理解,認為「羌」這個字就是寫成「羊角人身」,由此推出「羌人非人」的論述。只是,古族屬的名號來源多樣,可能是展現商人看待外族的視角,但也有可能只是音譯,若拿著後代對字形詮釋,就去推敲歷史的發展,其中難免有「葡萄長牙就是葡萄牙」的誤解存在。
說到底,「羌」這個字雖然寫成「羊角人身」的樣子,但董作賓就提過,羌也可能是只牧羊人[3]之類的意思。從字形揣想而無實例佐證的說法,是解讀古文字及古代史最需避免的事情。
本書還有一些論述是內部自相矛盾的,如第一冊講姓與氏的問題,到了第二冊卻換了一種說法。
本書所徵引的研究成果大都較為陳舊,這是可惜之處。當然,學術不是舊的一定好,也不是新的一定對,然而,像第二冊論《老子》晚於《莊子》說,這是錢穆先生的著名論點,但 1993 年郭店楚墓《老子》出土後,這問題已經有了結論,很少有人再提及這種「莊在老前論」了。
總結來說,筆者完全贊同歷史書寫可以風趣,可以幽默,甚至可以容許一點歷史想像。但無論是嚴謹的學術著作,或是普及的歷史讀物,都須秉持負責嚴謹的態度,不能輕忽怠慢、隨意說說。一般讀者很難有能力與時間反查材料與學界說法,不容易判斷論述的對錯,寫作者務必要謹慎小心,以免率爾操觚。
蘇建洲教授曾言:「社會上有影響力的賢達,您的一句話勝過我們寫禿十支筆,下回稱引某個意見或是推薦某本書籍,請善盡查證的職責,唯有如此您的推薦才有加乘的效果,也才能讓更多的追隨者因為您的推薦而讀到更多的好書。」這句話,與所有歷史寫作者共勉之。
[1] 對羌的軍事行動有:征、伐、獲、禦、追、執、幸、翦、蔑。參見劉新民:《甲骨刻辭羌人暨相關族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2] 見《甲骨文合集》519、6619、6620等片,例多不及備載。
[3] 董作賓《獲白麟解》:「羌字從羊從人證為牧羊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