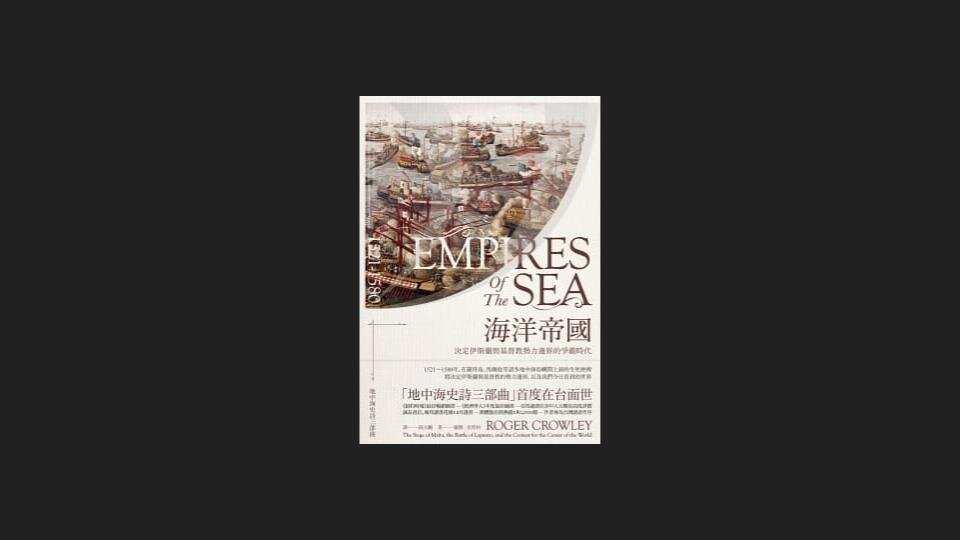在十六世紀中葉,地中海周邊的人口失蹤已經是家常便飯,在海邊勞作的人會突然間蹤跡全無──單獨駕船出海的漁夫、在海邊放羊的牧人、收割莊稼或者料理葡萄園的工人(有時甚至在內陸幾英里處也不安全)、在島嶼間不定期航行的船隻上的水手,全都是海盜綁架的對象。
被海盜劫持後,幾天之內他們就可能出現在阿爾及爾的奴隸市場上,或者被關押在海盜船上,隨著為尋找更多戰利品的海盜船進行漫長的航行。在途中身體變虛弱或者死亡的人會被丟到海裡。
在特別殘酷的情況下,俘虜可能會在一、兩天後就重回自己的村莊。海盜會在近海現身,升起停戰旗,展示俘虜,索取贖金。哀痛無比的親屬們會有一天的時間去籌集贖金。有的人家可能會將自己的田地和船隻抵押給當地的放債人,於是自此陷入無法逃避的債務漩渦。如果他們沒能籌到贖金,人質就會徹底消失。那些非常貧窮且目不識丁的農民很少有機會被贖回,因此很少能再次看到自己的家園。
這種突來的襲擊讓基督教海域陷入了深深的恐懼。那些在海上或者陸地上被擄走的人,永遠不會忘記被俘的創傷。
「至於我。」法國人杜.沙斯特萊(Du Chastelet)回憶那個噩夢時道,「我注意到一個高大的摩爾人向我走來。他的衣袖一直捲到肩膀上,只有四根指頭的大手握著一把軍刀;我害怕得說不出話來。這張烏黑的臉奇醜無比,帶有兩顆象牙白色的眼珠,醜惡地轉來轉去,他帶給我的恐懼遠遠超過人類先民目睹伊甸園門前帶火寶劍時的恐懼。」

這種恐懼因種族差異而加劇。
在狹窄的地中海上,兩個文明透過突來的暴行和復仇相互接觸。歐洲人此時正在西非劫掠黑奴,但在地中海,他們自己卻是被奴役的對象,儘管在十六世紀,被伊斯蘭世界奴役的歐洲人的數量遠遠超過歐洲人擄走的黑奴。在大西洋上的奴隸貿易是一種冷酷的生意,而在地中海,奴隸貿易卻受到雙方宗教仇恨的激發。伊斯蘭的劫掠不僅僅是為了損害西班牙和義大利的物質基礎,也是為了打擊對手的精神和心理基礎。
熱羅姆.莫朗於 1544 年所目睹,土耳其人對墓園的洗劫和對教堂的儀式化褻瀆,是有其深意的。
義大利詩人庫爾蒂奧.馬太(Curthio Mattei)曾哀嘆「上帝蒙受的凌辱」──聖像被用匕首插在地上,聖禮和祭壇遭到嘲諷。他還為土耳其人挖掘死屍、搗毀已經辭世數代的人們遺骸的惡行感到震驚不已:「我們死者的遺體已經入土十多年,在地下也不得安寧。」海盜在義大利民間傳說中成了地獄的代理人,而讓人愈發無法忍受的是,這些撒旦的使節往往是為形勢所迫,又或心甘情願改宗伊斯蘭教的叛節基督徒,而這些人對自己的家園非常熟悉,因此更能夠大肆破壞。
在這種大環境下,查理五世在 1541 年沒能收復阿爾及爾,就顯得尤其嚴重。
這座城市現在得到了一座防波堤和強大防禦工事的保護,成了海盜活動的中心。這是座充滿淘金熱的城市,任何人在這裡都可以夢想變得像巴巴羅薩那樣富有。來自貧瘠大海的各個角落的冒險家、私掠海盜和浪蕩子,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都爭先湧向這座城市,打算在「擄掠基督徒」的生意上試試身手。
這座城市有的地方像是一座俗艷的大市場,奴隸和戰利品在這裡買賣轉手;有的地方則像是蘇聯的古拉格(Gulag)勞改營。成千上萬的俘虜被關在奴隸營地裡。這些營地由澡堂改建而成,黑暗、擁擠、臭氣熏天。奴隸們每天都戴著鐐銬,從這裡被領出去做苦工。富有的俘虜,例如在阿爾及爾被關押五年的西班牙作家賽凡提斯(Cervantes),在等待贖金的日子裡或許會得到相當程度的善待。而貧窮的俘虜就必須搬運石頭、伐木、採鹽、修建宮殿和壁壘,最糟糕的情況是去船上划槳,直到疾病、虐待和營養不良奪去他們的生命。

我們無從得知,1540 年之後的歲月裡究竟有多少人被賣為奴隸,但這並不是只有一方在做的生意。雙方在整個地中海都在進行「擄掠人口」的活動,如果說伊斯蘭世界的販賣奴隸活動很猖獗的話,基督教世界也進行了小規模的以牙還牙。聖約翰騎士團就是冷酷無情的奴隸販子,尤其是拉.瓦萊特,那個年輕時曾在羅得島作戰的法國騎士。
騎士們以馬爾他為基地,派出一小群配備有重型武裝的槳帆船,重新回到了他們在愛琴海的舊有活動範圍,襲擾著鄂圖曼帝國在埃及和伊斯坦堡之間的航道。騎士們和海上的任何海盜一樣心狠手辣、毫無顧忌。熱羅姆.莫朗抵達威尼斯所屬的蒂諾斯(Tinos)島時,騎士們剛剛「拜訪」過這裡。
島民們歡迎了這些「朋友和基督徒」,直到一天早上,島民們在離開城鎮,下地幹活時,「這個騎士和他的部下看到城堡裡人很少,於是殺了他們,洗劫了城堡,擄走婦女、男孩和女孩做為奴隸」。這些醜惡行徑很快就遭了報應。這名騎士被土耳其海盜抓獲,送往伊斯坦堡,莫朗在那裡目睹他被處決。命運無常,風水輪流轉。

騎士團不是基督教方面唯一的奴隸販子。任何小規模的基督徒海盜都可以試試身手,劫掠地中海東部;義大利海岸上的利佛諾(Livorno)和那不勒斯都有生意興隆的奴隸市場。不少穆斯林被擄走,關進馬爾他的奴隸營,或者押上教宗屬下的帝國槳帆船,但穆斯林奴隸的數量遠少於被抓到馬格里布或者伊斯坦堡的基督徒奴隸。關於被賣身為奴的基督徒,留下了海量的文字敘述,但關於穆斯林奴隸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資料。偶爾有模糊不清的關於個人苦難的記述會打破這普遍的沉默。
1550 年代末,一個名叫胡瑪(Huma)的女子不斷向蘇萊曼哭訴,請求追回自己前往麥加朝聖時被聖約翰騎士團擄走的孩子。她的兩個女兒已經被劫持到法國,改宗基督教,嫁了人。在伊斯坦堡,呼天搶地的胡瑪成了路人皆知的人物,她堅持不懈地守候在大街上,一旦蘇丹騎馬經過,就把請願書塞到他手裡。
在她的孩子失蹤二十四年後,蘇丹穆拉德三世(Murat III)仍然寫道:「名叫胡瑪的女士一而再、再而三地攔住我的坐騎,呈上請願書。」據我們所知,這兩個女孩始終沒有被追回來;她們的兄弟可能被賣做划槳奴隸,死在一艘馬爾他槳帆船上。在基督教和伊斯蘭世界,類似的悲劇數不勝數,都是關於劫持和喪失親人的故事。
所有這些暴力活動的工具都是槳帆船。海洋條件造就了這種快速但脆弱的低矮船隻,成為地中海的戰爭機器。海戰如何進行、在何時何地進行,同樣也取決於海洋條件。槳帆船吃水淺,因此可以輕鬆地靠岸,有利於兩棲作戰;它們可以潛伏在近海,準備伏擊;也可以在笨重的帆船(其機動性完全受制於變幻難測的風向)周圍任意旋轉。
與此同時,槳帆船的適航性驚人地差,而且依賴於不斷地補充淡水(以供應槳手飲用),所以只能在近海活動。槳帆船每隔幾天就要靠岸一次,因此它們的作戰半徑有限,部署也受到季節的制約。冬季的暴風意味著每年十月至四月,海戰都要暫時偃旗息鼓。
最關鍵的是,海戰的發動機是人力;在十六世紀擄掠人口活動的所有動機中,抓人當划槳奴隸是重要的一項。

在十五世紀,威尼斯的海上霸權正處於顛峰的時期,槳帆船的槳手都是志願者。
到十六世紀,槳手主要是徵募來的。另一方面,鄂圖曼海軍很大程度上依賴每年從安納托利亞和歐洲行省徵募來的槳手。各國也都使用強制勞役──如俘虜、罪犯等。在基督教國家的船上,還有因為生活貧困、無以為繼而賣身為划槳奴隸的人。這些可憐蟲每三、四個人被鎖在一條約一英尺寬的長凳上,正是他們使得海戰成為可能。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苦幹到死。他們的手足都戴著鐐銬,坐在槳位上拉屎撒尿,吃少得可憐的黑餅乾,忍耐著口渴,有時甚至去喝海水。划槳奴隸的生命常常是悲慘而短促的。
他們只穿著亞麻馬褲,除此之外一絲不掛,皮膚被烈日炙烤;他們被鎖在狹窄的長凳上,長時間無法睡眠,有些槳手因此發瘋;在一艘戰船努力俘虜敵船或者拚命逃跑時,需要長時間的劇烈勞動,這時保持節拍的鼓點和監工的皮鞭(由曬乾的公牛陰莖塗上焦油製成)鞭策著他們拚命划槳,哪怕筋疲力竭了也不能停歇。
槳手拚死划槳的景象可怕得令人不敢直視。
「對被剝奪自由的人來說,划槳是最無法忍受和最可怕的工作。」英格蘭人約瑟夫.摩根(Joseph Morgan)描繪了這樣的景象:「一排排身子半裸、忍飢挨餓、部分皮膚被曬得黝黑、身體精瘦的可憐人,被鎖在木板上,有時一連幾個月都無法離開……裸露的皮肉遭到殘忍、持續的鞭打,被催促用力划槳,甚至超過人力可承受的範圍,不斷地持續最猛烈的動作。」人們從基督教國家的港口啟航時,常常聽到這樣的祝福:「願上帝保佑你,不要落到的黎波里的槳帆船上。」
有時由於疾病蔓延,一支艦隊在幾週內就能損失慘重。槳帆船是一個死亡陷阱、一條海上的臭水溝,它的熏天臭氣在兩英里外就聞得到。當時的習慣是,隔一段時間就把船體沉入海底,以清洗上面的屎尿和老鼠。但如果船員們沒被疾病打倒,活了下來,參加了戰鬥,槳手們就只能坐在那裡,等待被自己的同胞和相同信仰的人殺死。
鄂圖曼帝國的大部分槳手在名義上都是自由人,但他們的處境也好不了多少。蘇丹從內陸省分徵募大量槳手,其中很多人之前從沒看過大海。他們做為槳手沒有經驗,效率也不高,由於條件惡劣,往往大批死去。
槳帆船以各種方式消耗著人力,就像消耗燃料一樣。每個死去的可憐槳手被拋下海之後,就必須有人接替他,因此總是缺乏足夠的人力。西班牙和義大利官方的備忘錄總是不厭其煩地報告槳手的缺乏,因此船隻建造的速度常常超過槳手配置的速度。
1555 年,聖約翰騎士團的槳帆船艦隊突然遭到一場災難,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現象。
10 月 22 日夜間,騎士團的四艘戰船安全地停泊在馬爾他的港口內。槳帆船群的指揮官羅姆加(Romegas,騎士團經驗最豐富的船長)在自己旗艦的尾部睡覺。這時一場詭異的旋風從海上颳來,吹斷了船隻的桅杆,將船隻打翻。破曉時,四艘槳帆船底朝天地漂浮在灰色的海面上。營救者乘小船去尋找生還者,並查看船隻的損失情況。他們聽見其中一艘船內傳出沉悶的敲擊聲,於是在船體上鑿了一個洞,在黑暗中往底下張望。
船上的寵物猴子迅速跳了出來,然後是羅姆加,他在一個水淹到肩膀、但是有空氣的狹小空間內熬了一夜。直到用浮筒將船隻扶正,大家才清楚地看到一幕可怕的景象──三百名溺死的穆斯林划槳奴隸的屍體仍然被鎖在長凳上,像白色的鬼魂一樣在水裡漂浮著。
修理和更換船隻還算是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尋找新的船員卻是真正的難題。
教宗打開了那不勒斯大主教屬下的監獄,提供了一批划槳奴隸;騎士們隨後不得不乘船出海去抓捕更多的奴隸,來填滿槳手長凳。這對雙方都是一樣。多次的劫掠僅僅是為了補充人力,以便開展新的襲擊。
暴力是無止盡的惡性循環。槳帆船對人力的需求就是發動戰爭的一個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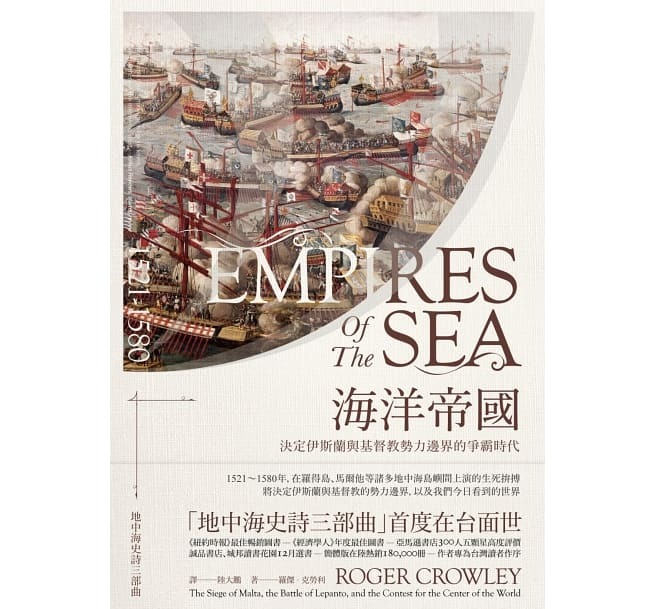
長達數十年的殘酷鬥爭,
戰場東起伊斯坦堡,西至直布羅陀海峽,
有著數十篇關於帝王、將相、海盜、十字軍、
穆斯林、教士的傳奇故事。
此外,本書除描述東西方兩大帝國間軍事上的武力衝突、
外交上的爾虞我詐外,
也點出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間的歧異與隔閡。
而直到今天,東西文化之間的齟齬,仍尚未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