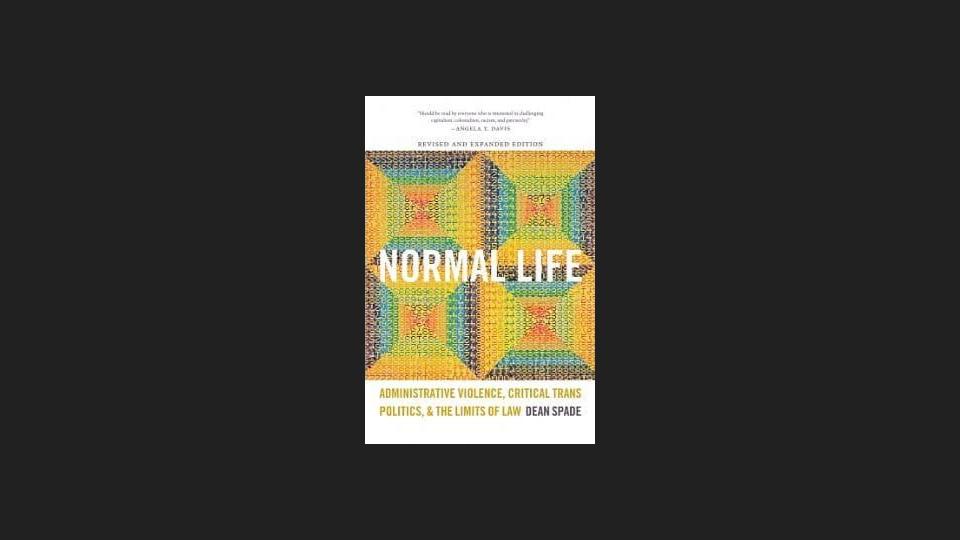喬治.歐威爾曾說:「誰能控制現在,誰就能夠控制過去。」隱藏史實、編撰歷史,為了迎合自己的正當性,這些慣用的手法,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一再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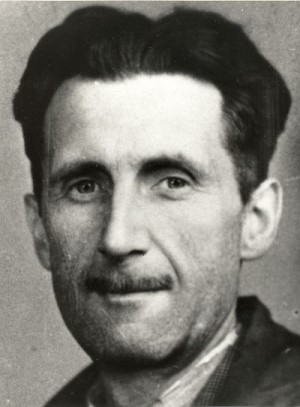
超過百年的歐洲獵巫熱對於女性而言,無疑是一場大災難,然而歷史課本卻仍在吹捧著那個光榮的時代,將一切目光聚焦在地理大發現、啟蒙運動,那些男人的歷史。
「她們因潑辣及巫術而受到的懲罰如此嚴苛,以致於接下來幾個世紀裏,女人都保持低聲下氣。」在獵巫熱中,女性被有意識清洗,使男性當權者牢牢地守住了地位。
這樣的事情一直在歷史中反覆上演發生,當特定族群持續把持著權力時,他們握有的不只是物質資源,他們更掌握了政治力、話語權等全方面的文化詮釋權。他們鎖定了人們的視野,要求人們用他們的價值觀裡損益利弊、看世界。
這樣的結構被學界稱為「父權社會」,「美國女性主義者凱特·米爾利特(Kate Millett )於 1970 年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書中,將父權定義為老男人控制年輕男人,男人控制女人的權力關係。」

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從女性的觀點來看歷史?女性什麼時候才開始擁有「權利」為自己發聲?換言之,女性主義何時萌芽?
大多數人同意,女性主義是從十八世紀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發表《女權辯護》開始。
女性從幼年時代開始就被教導:美貌是女人的權杖,因而心靈要為身體塑造自己;心靈只能在它的鍍金鳥籠里徜徉漫步,並且只能努力去讚美它的牢籠。
在《女權辯護》中,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經精準指出女性的悲哀,在父權結構底下,女性無從得到「人」的待遇,所謂「人權」的發展都是以男性為出發點,女性永遠是在父權的框架下辛苦跟在後頭,或者被「物化」成可以帶出門或者鎖在家裡的擺設品。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仍然得要難過地承認──這些事情還在持續發生。「婦女成為不受尊重、無從得利的群體,她們總共合起來才擁有世界財產和資源的百分之一,但卻要付出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勞動。」在 2011 年〈台灣國際研究季刊〉中記錄下了這殘忍的事實。
我們可以說,隨著所謂的「社會進步」,如獵巫般大規模的血腥屠殺似乎不存在,但女性的不平等待遇仍在持續,同工不同酬、性侵害及性騷擾、性暴力及性招待問題、性別天花板等,而這樣的壓迫的根源,如同《獵.殺.女巫》中提到的──「只要有權力的落差就有可能勾動敵意,形成抵抗。」
經歷了好幾世紀的壓迫,女性主義終於在十八世紀開始萌芽,父權體系的迫害則隨著社會的變動以不同形式展現,過去,曾以最直接的集體霸凌展現,而近代,尤其偏愛以「保護」為名進行,「『解放』與『支配』這兩個對立概念在此有所混雜與糾結,上位者時常以為弱勢者、或者社會秩序著想的藉口來支配,常見的論述俯拾即是。
工業革命時期,高喊男主外女主內、中國長達數百年的纏足酷刑,大戰期間是以救亡圖存和強種救國為目的、現今則是要女性多自愛以保護自己不被侵犯等,檢討受害者的言論漫天飛舞,其中有意無意的透露出對男性強勢的肯認,更偷渡了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運作概念。

而這樣的公式出現在各種迫害當中──比如十九世紀以來白種人是怎麼樣扛起了使有色人種進化的負擔、中國政府「再教育」新疆的維吾爾族人。掌權者將迫害合理化的論述,其核心價值都如出一轍。
性別間的不平等仍然持續,說明了女性主義必須繼續辛苦奮鬥。許多反對者會主張女權者不過是一群「自助餐」,只挑對自己有利的說、只挑對自己有利的做,批判女性主義者是在無限上綱,更甚至大吐苦水這是一個男性被女性霸凌的時代。
事實上,女性主義要的是翻轉男女關係、並且「報復」父權的迫害嗎?
絕對不是,在各種議題上的被迫害者想要的無非是「平等的待遇」,而不是「無盡的復仇」;因為作為被霸凌者的痛楚,很顯然地,女人比誰都明白在這個社會裡被壓抑了幾千年以後,女人要的,也只是像人一樣的平等。
- 《獵.殺.女巫》,Anne Llewellyn Barstow,1999
- 《友善的邪惡——台灣女性主義的忌性論述》,黃亦宏,106
- 《女權辯護:關於政治和道德問題的批評》,Mary Wollstonecraft,1792
- 《性與性別社會學》,張晉芬,2003

將在2019年5月11日(六)於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演出
下午場:13:00進場 13:30開演
晚上場:18:00進場 18:30開演
歡迎各位蒞臨觀賞!
免費索票表單:http://bit.ly/2Di3f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