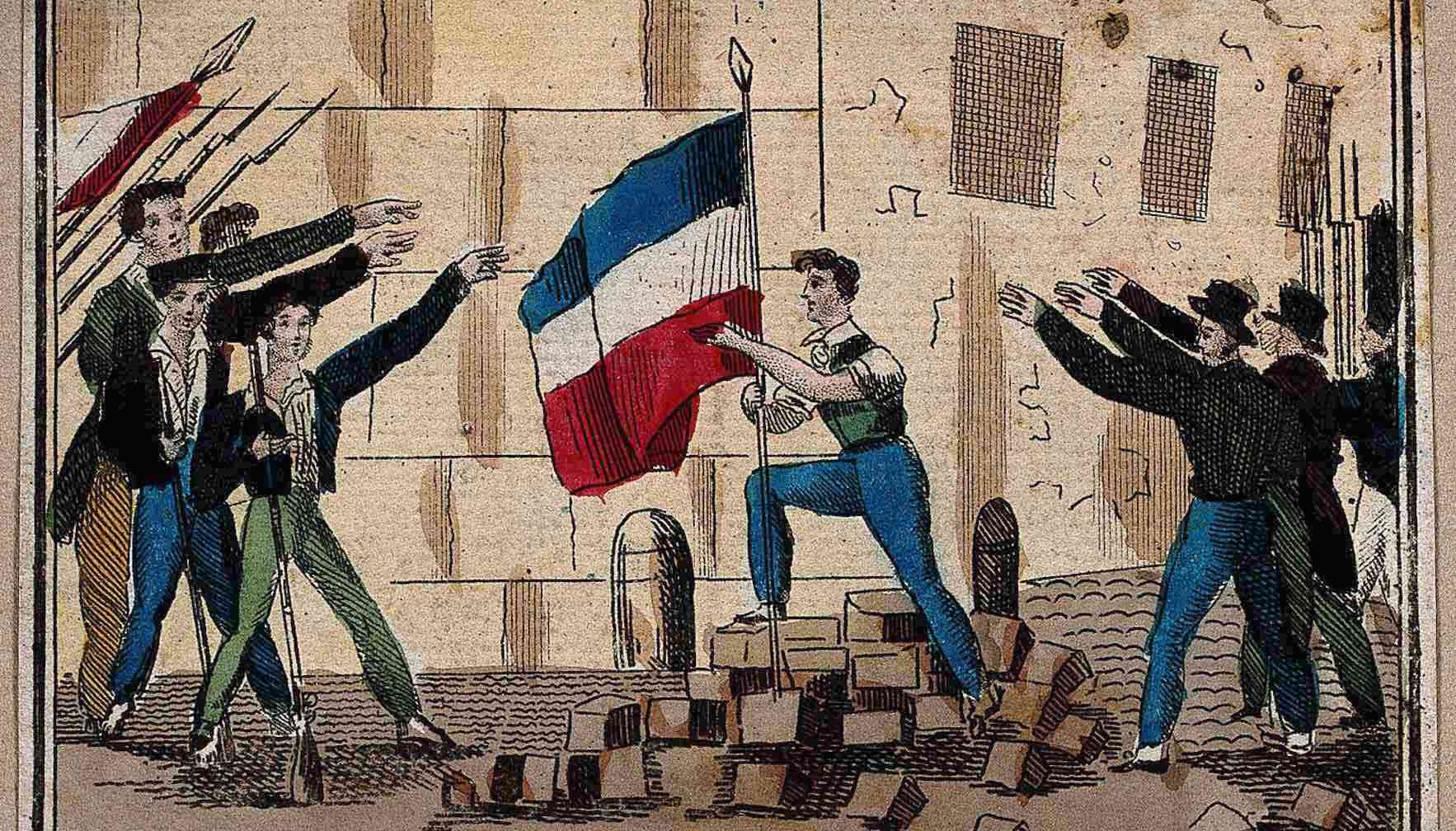英格蘭人已敗壞了我王國內的人心;我們可不能讓下一代人暴露於被其語言引入邪路的危險。──路易十五
和英國人提起戰爭,他會勇往直前,一個英格蘭士兵能擊敗十個法國人;縱使吾人將豪誇之物由劍尖轉為筆鋒,我們的勝算仍然更高,更高啊我們……莎士比亞與彌爾頓一馬當先,有如戰爭中的神祇,令法人全本劇作與史詩逃竄……還有詹森,彷彿往昔之英雄,已經打倒四十個法蘭西人,接下來還要再打倒四十個!
──大衛.蓋瑞克,〈論詹森字典〉(On Johnson’s Dictionary)1756年
七年戰爭期間,似乎能算是英語開始成為第一種世界語言的時間點,雖然法語在歐洲仍占據主導地位。伏爾泰沒有說錯:莎士比亞的語言並不優越於拉辛的語言。但語言的傳播不是憑藉文學、甚或是時尚,而是靠權力與金錢。
法語甫在十八世紀初確立其作為外交語言的地位。《烏特列支條約》(1713 年)以法文寫就。使用拉丁文的舊習仍持續了一段時間,西班牙、日耳曼與義大利地區的政府仍短暫使用本地語言。但在十八世紀的頭幾十年間,法語因其重要性與便利性,逐漸成為國際交流的媒介──尤其是因為英國人只能說一點法語,別的都不行。這種習慣大致上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歷史學家尚・貝昂傑(Jean Bérenger)與尚・梅約(Jean Meyer)指出,法語霸權確立之時,恰好是法國霸權正要開始衰落之時。大衛・休謨在七年戰爭後自滿預測道:「所以,就讓法國人在當前其語言的傳播上取勝吧......。我們在美洲穩固、逐漸發展的基礎......將為英語許下更優越的穩定性。」不過,英語後來雖然傳播到世界各地,但鮮少有地方是因為受到美國直接影響。反而是因為法國戰敗、英國海外帝國隨後的擴張,以及英國貿易與交流的相應宰制,才確保了英語能在大半個世界成為實用的溝通媒介。

長久以來,作為文化與社會上層語言的法語,可謂難逢敵手。有人把高乃依的劇作《熙德》(Le Cid)英譯本送給高乃依,高乃依覺得這語言相當古怪,把書跟另一種奇特語言──土耳其語的譯本擺在同一個書架上。
1680 年至 1760 年間,法國是最大的書籍出口國。斯圖亞特宮廷的常客文人夏爾・德・聖艾雷蒙(Charles de Saint-Évremond),在他待在倫敦的四十年間都沒有學英文──此番豐功偉業,幾乎可以跟二十世紀長久出任大使的保羅・康朋(Paul Cambon)相提並論。有個故事說,1740 年代的凡爾賽宮除了一位出身加萊的滑膛槍手之外,就沒有人有能力翻譯英語文件。路易十五反對讓英語進一步推廣。
在英國,通法語始終在一般受人稱許的修養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二十世紀亦然。旅遊作家葛羅里甚至認為英格蘭會重新使用法語,一如諾曼人統治時代;當時也確實有股流行,將詞彙與拼法加以高盧化(較古老的拼法如「honor」、「center」仍流傳至今,或是在美洲重新開始使用)。
學法語是「壯遊」中重要的一面。多數英國知識分子多少都能來點沙龍對話,即便這相當費勁(如大衛.休謨與亞當.斯密的例子)。安東尼・漢彌爾頓與威廉・貝克福特(William Beckford)更是以法語作家身分聞名。十九世紀中葉,有志成為家庭教師的年輕女子,通常都會到法國學校裡學如何教書,因為英格蘭上流家庭對「在法國學到的法語」有高度要求。

出於時尚與價值觀因素而對英語有興趣的法國人,在十八世紀期間變得愈來愈多。伏爾泰對於法語在歐洲的普及貢獻良多,而對於英語在法國的流行,他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主張自己是法蘭西學院中第一個學英語的人,這話應該不假,但孟德斯鳩旋即跟上腳步。
沙特萊侯爵夫人(Marquise du Châtelet)是伏爾泰過從甚密的贊助人,她把英語學到好得足以翻譯牛頓得著作,而且還能跟伏爾泰用法腔英語吵架。由於學校裡不教英語,愛爾蘭與蘇格蘭裔的詹姆斯黨人便開班私人講授,許多語言教材因而出版。
百科全書作家德尼.狄德羅設法用拉丁─英語字典學英文。但一直要到 1770 與 80 年代,英文才搭上「盎格魯狂熱」的其他面向,變得足夠流行。在小姐們心中,英語取代了義大利語,成為高雅的文化素養。比索先生(M. Pissot)因為「近年來英語在法國如此普及」,開始出版低價版的英語經典作品。1770 年代,一位諷刺作家嘲弄那些能「糟蹋幾個字」的人:「O di dou miss, kis mi」(噢,小姐打哪兒來啊,吻我)。
來到宮廷裡,普羅旺斯伯爵(Comte de Provence,後來的路易十八)決定學英文──法國大革命期間,他長期流亡在外,證明這個決定的好處遠比他過去所想像的更多。對英格蘭又愛又恨的路易十六,則是自學英語,違逆母親的意願──她認為這是種煽動叛亂的語言。他譯過幾段彌爾頓,而他翻譯何瑞修.沃波爾所寫的理查三世聲明,則在他死後出版。他等待上斷頭臺之前,還研究了斯圖亞特王朝的歷史。
用盎格魯化的表達方式或字詞成為一種流行,甚至連國王都這麼做:site(所在)當作situation,用prononcer(表達)取代exprimer。此舉惹惱了純粹主義者,尤其當這類用詞具有社會或政治意涵時更是如此:tolérance(寬容)、budget(預算)、vote(投票)、opposition(反對)club(俱樂部)、pétition(請願)、constitution(憲法)、législature(立法機構)、convention(協議)、jury(陪審團)、pamphlet(宣傳小冊)。
人們難免比較起這兩種語言。有些啟蒙哲士對英語表示讚賞──伏爾泰則是一改早期的稱許,轉為挖苦:
英語之靈魂在於其質樸,但免不了最卑下或最荒謬的思想;其靈魂在於其活力,但其他民族或許認為那是粗野;其靈魂在於其勇氣,但對於異國語法不習慣的人,恐怕會當那是胡說。
盧梭的影響多少扭轉了人們的價值觀。優雅的法語交談開始遭受批評為過度矯飾、話多、不真誠而「缺乏男子氣概」。此前人們抨擊為英式淺白與沉默的對話,如今則能詮釋為真誠與質樸。也有人有意採取措施,讓這兩種語言淺明易懂。塞繆爾・詹森在他的《詹森字典》(Dictionary, 1755)裡努力收錄流行於社會上層的「高盧語法結構與片語」。詩人克里斯多福.斯馬特(Christopher Smart)則希望「英格蘭人之語言」有朝一日能成為「泰西之語言」。
1783 年,一份備受矚目的法語跨國保證書出爐了──柏林的皇家科學院舉辦一場論文比賽,題目為〈法語何以如此普及?它何以得享如此特權?其地位可能保持嗎?〉主辦單位只接受以拉丁文、德文或法文(當然囉)提交的論文。來自各國的參賽者大致同意法語有獨特的吸引力、廣受歡迎、偉大的文學成就,其優越地位歷久不衰。
獎項的共同得主之一是安東萬・里瓦羅(Antoine Rivarol)──「當代髮型最好看的人」──斷言德語太多喉音,西班牙語太過嚴肅,而義大利語不夠陽剛。至於英語,除了會讓說英語的人自己感到不快之外,英語太近於野蠻、對歐洲來說太邊緣、其文學缺乏品味、文法「古怪」,發音更是低人一等。法語不只有文學上的豐功偉業,還有某種獨特的「靈魂」:其他語言也許更具詩意、更富音樂性,但法語的客氣、邏輯、清楚皆獨一無二,因而帶來舉世無雙的「剛直」。更有甚者,法國知識領袖維持法語的地位,近年的美國獨立戰爭為法語加冕,讓英語文學和英格蘭人的力量黯然失色。
里瓦羅以精妙的方式總結早已廣為人所接受的看法,將這種語言與生俱來的美德確立為固定的看法。用他最有名的話來說:「如果不清楚,那就不叫法語。」對於馬克・弗馬洛里來說,這種語意上的精確,與他形容為「柔弱的透明」的二十世紀全球英語大相逕庭──英語只能在缺乏風格的情況下傳達大致意義,無以為二十一世紀帶來一種文雅的全球語言。英語的角色確實與盛極一時的法語難以相比,當時的法語讓人聯想到影響力與高雅文化。法語始終是獨特的標誌;英語呢,則是「自我進步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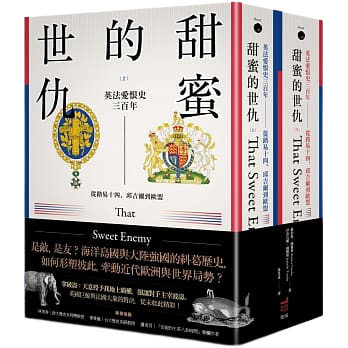
作者羅伯特與伊莎貝爾分別來自英、法兩國,這對史家夫妻檔走筆寫過海峽兩岸三百年來的生死貧富、勝敗興衰,字裡行間結合英式幽默與法式瀟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