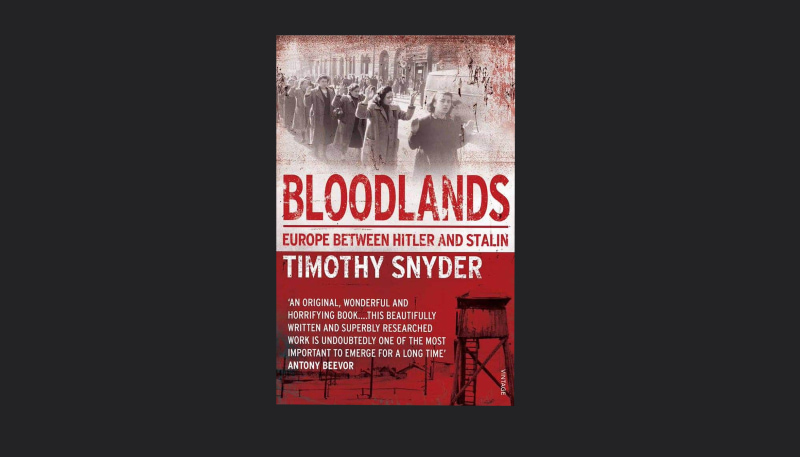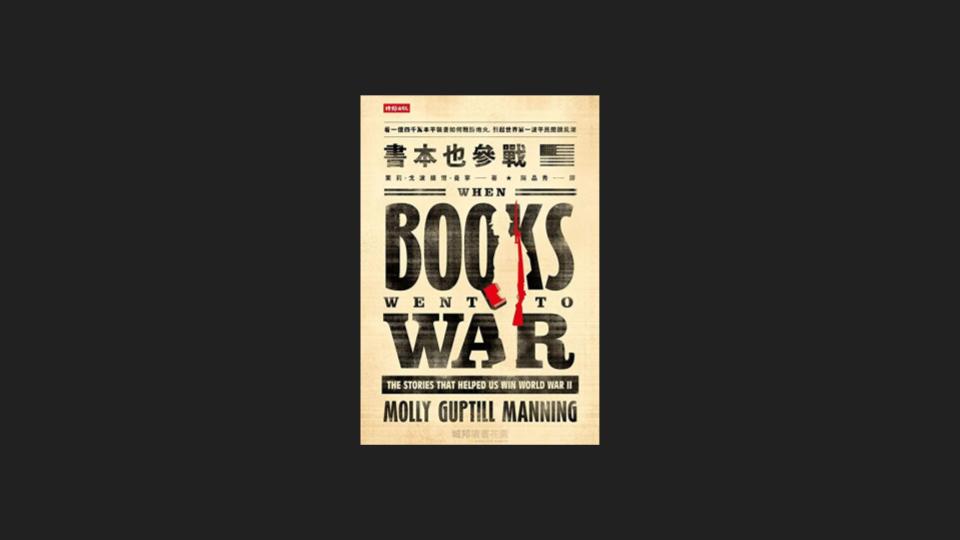在戰爭結束時,納粹親衛隊放火燒了位於弗次瓦夫(Wrocław)的親衛隊暨警察法院(SS-und Polizeigerichte),大火從窗戶竄出,許多紙張散落到街上,有些燒焦,有些則成了碎片。落在路上的紙片只有少數幾張完好無損。
有位長期遭受納粹親衛隊折磨的男子保留了其中的八張。這位名叫埃米爾・烏爾坎(Emil Wulkan)的男子保守了這個秘密許多年,直到自己與《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的某位記者彼此建立了足夠的信任感,他才向對方出示那些發黃了的紙張。預先打上的信頭依然清晰可辨。
那是一份很有條理的文件,上頭還有留給檔案編號與專員分機號碼的空白部分。信頭的部分還包括了預先打上的日期行:「奧斯威辛,XX 年 XX 月 XX 日」。
那位《法蘭克福評論報》的記者,湯瑪斯・格尼爾卡(Thomas Gnielka),隨即就在 1959 年 1 月 15 日將那些紙張轉寄給弗里茲・鮑爾。鮑爾在 1956 年的復活節時已從布朗史威克轉往法蘭克福任職,從「偏遠地區」的邦檢察總長變成「大都會」的邦檢察總長。他不僅在這些紙張中看到了爆炸性的原始文件,而且還看到了一個自己由衷歡迎的機會:一個可藉以將整個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議題拉上法庭的小支點。
那些紙張是 1942 年集中營指揮部的來函。關於殺害「逃跑」囚犯的文件。
弗里茲・鮑爾曾回憶道:「像那樣的文件,從那時起,就完全不為人所知。那是一些預先打好的表格;它們表現出了『千年帝國』(Tausendjähriges Reich)的整體性格的特徵。第一頁上寫著:『衛兵某某某在囚犯(以代號稱呼)逃亡時將其射殺。』第二頁,同樣也是預先打好的:『這份公文是為了啟動過失殺人或故意殺人的訴訟而寄往弗次瓦夫,給親衛隊暨警察法院。』第三頁,同樣又是預先打好的:『訴訟被停止。』我之所以點出這件事,那是因為它以很特殊的方式表現出了權利外觀的外部維護的特徵。這件訴訟從一開始就被停止。」
鮑爾表示:「這份文件到了我們的手中,於是我們就這樣在法蘭克福得知了一批在囚犯『逃跑』時,開槍射殺他們的那些衛兵的名字。我們把這些送往卡爾斯魯爾(在那裡,聯邦法院對於行為地在國外的案件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3a 條的規定自由指定一個管轄法院),卡爾斯魯爾方面則把它們送了回來;法蘭克福的檢察署這時可以去把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案子查個明白。」
落入弗里茲・鮑爾手中的那些東西其實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幸運。在那個時候,只要願意動手,每位檢察官都能有類似的斬獲。那個滅絕營周邊,直接知情的人數量依然十分龐大。
根據今日我們所知,當時有七千多人任職於奧斯威辛集中營,他們的家人並沒有住在離他們很遠的地方,許多人就住在他們附近;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是在戰後的回首中,才被描繪成位於東方某處的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地方,然而,在「第三帝國」時期,那裡其實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交通樞紐,誠如歷史學家諾伯特・弗萊(Norbert Frei)所強調:「奧斯威辛位於上西里西亞(Oberschlesien)的柯尼希許特(Königshütte;意即「國王的冶煉廠」)。」在 1950 年代時,尚在人世的前囚徒數量同樣相當可觀。而且,並非所有的倖存者都想忘記這段過往,事實上,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在尋找聽眾。人們其實只要聽他們說就行。
舉例來說,在 1958 年 3 月 1 日,斯圖加特的檢察署收到了關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某位罪犯的線報。這位罪犯名叫威廉・伯格(Wilhelm Boger),當時任職於斯圖加特祖芬豪森(Zuffenhausen)的一家汽車公司。
伯格是在 1933 年春天從符騰堡邦的政治警察做起,也就是在他們把斯圖加特的地方法官弗里茲・鮑爾從他的辦公室裡抓走不久之後。在奧斯威辛,伯格則隸屬於蓋世太保營(也就是警察部門),他們得藉由比滅絕營裡日常的殘酷更為殘酷的審訊,來防止越獄與扼殺監獄暴動。
伯格以他在刑求方面如惡魔般的創意而臭名昭著。他最有名的一項發明被囚徒們稱為「伯格鞦韆」。那是一種將囚徒綁著吊起來的支撐桿,如此一來,人們就能毫無阻礙地一次又一次朝他們的生殖器毆打他們;伯格甚至還在法蘭克福的法庭上表示,這個方法很有效。
在 1958 年時,曾被關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一位囚徒,阿道夫・羅格納(Adolf Rögner),透過信件為斯圖加特的檢察署指出了伯格的下落。可是偵查工作卻未被積極地進行。負責偵辦的人員與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另一名倖存者,「國際奧斯威辛集中營委員會」(International Auschwitz Committee)的秘書長赫曼・朗貝恩(Hermann Langbein),冷冷地進行了長達數月的書信往來;他們請問對方,是否能夠在證人與情報上提供一些協助?可是朗貝恩是位難搞的伙伴,因為他提了一堆條件。
另一方面,負責偵辦的人員這邊自己也是意興闌珊。直到過了將近半年之後,他們才在 1958 年 8 月 19 日去拜訪阿道夫・羅格納這位線民。
那時候,就連在小城烏爾姆(Ulm),人們也都得考量,那會在巴登—符騰堡邦的司法界引發多大的反彈聲浪。那裡有十名男性遭到指控,過去在擔任親衛隊保安處(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簡稱:SD)所屬別動隊的成員時,曾經參與將十三萬名男女老幼(其中有一半以上是立陶宛的猶太人)槍殺於萬人坑的行動。
十名被告僅被指控執行了這場在立陶宛的種族滅絕行動的一小部分,受害者的人數大約為五千人,他們在吼叫與毆打下將受害者驅趕到現場,然後逼迫他們挖掘坑洞,接著再以十人一組的形式將他們射殺,過程中還不時會呼喝:「快點、快點,這樣我們才能早點下班!」烏爾姆的一位目擊證人曾表示:現場看起來「就像是個屠宰場」。
然而,這一切卻幾乎永遠也不會被起訴。
烏爾姆的檢察官們早就打算擱置偵查程序。直到斯圖加特的邦檢察總長埃里希・內爾曼(Erich Nellmann)得知這個案件出手干預,更以「偵辦不力」為由將該案從當地檢察官的手中抽走,事情才有了轉圜。內爾曼特別派遣自己的同事埃爾文・舒勒前往烏爾姆接手案件的偵辦與起訴。
因此,這場審判,無論它在 1958 年時有多重要,依然只是一場「偶然的司法偶然的產物」,誠如《南德意志報》的記者所言,一場罕見的失控,最終,有七名被告被判處了三至五年的有期徒刑,只有三名被告被判處了十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無論如何,這場審判倒是阻止了與奧斯威辛集中營有關的案件偵辦,在斯圖加特完全停頓下來。被派往烏爾姆辦案的檢察官埃爾文・舒勒,接著受命在路德維希堡成立一個「納粹犯行調查中央辦公室」;這是一個得為全國各地的檢察機關提供協助的單位。發生於烏爾姆的那些血腥犯罪在民眾間引發的驚恐,促使共和國的十一名邦司法部長決定一同撥款,藉以針對納粹的犯行進行系統性地調查。不過,設於路德維希堡的中央辦公室最多卻也只編制了十一名檢察官,為的是避免他們的工作「氾濫成災」。
此外,這些檢察官不單得要關注所有納粹的罪行,同時還得關注對於德國的戰俘與流亡者犯下的所有罪行。弗里茲・鮑爾曾在 1958 年時批評說:「在那裡,性質不同的事情被連在一起;一方面是納粹不正義國家的行為,另一方面則是其後果。這樣的結合可能給人一種印象:人們想要製作一個借貸雙方在其中相互平衡的國家與國際不正義資產負債表。」
從 1958 年 12 月起,斯圖加特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調查人員雖然得到了新成立的路德維希堡中央辦公室的協助,然而,經過幾過月的通力合作,他們卻只得出了短短一張,除了威廉・伯格以外或也曾任職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十八人名單。一個簡直微不足道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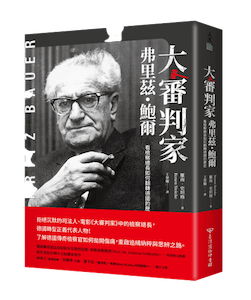
德國轉型正義代表人物!
了解德國傳奇檢察官如何拋開傷痛,重啟追緝納粹與思辨之路。
弗里茲・鮑爾是一位偉大的法律工作者與人文主義者,
他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大審判家》,獲獎無數!
他不只翻轉了戰後德國的命運,讓德國走上反思之路,
他的傳奇一生也成為德國多部電影的重要題材!
一位打破沉默圍牆、扭轉當代德國的關鍵人物,
一本令國際矚目的傳記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