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以改造同性戀為異性戀知名的紐約精神科醫師歐文・畢伯(Irving Bieber)發表了影響深遠的著作《同性戀:男同性戀的精神分析研究》(Homosexuality: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Male Homosexuals)。畢伯主張,男同性戀是由家庭扭曲的動力所造成,來自於教人透不過氣來的母親,她對兒子就算不是明顯誘惑,至少也是「緊密束縛和性方面親密」,再加上孤立、疏遠,或「情感上敵對的父親」這種致命的結合。
男孩對這些力量的回應,就是展現神經質、自我毀滅和瘸跛的行為(畢伯在 1973 年曾說出這段名言:「同性戀是異性戀功能殘障的結果,就像小兒麻痺患者的腿。」)最後,有些這樣的男孩,因為認同母親和閹割父親的潛意識欲望,而選擇以非常態的生活方式表現。
畢伯認為,這些性「小兒麻痺患者」採取了病態的生存方式,就如小兒麻痺患者以病態的方式走路。到了 1980 年代後期,同性戀就等於是選擇離經叛道的生活方式,這種觀念深植人心,變成教條。因此,1992 年,美國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宣稱「同性戀是選擇,而非生物現狀。這是一種錯誤的選擇。」
所謂的同性戀基因在 1993 年 7 月發現,掀起遺傳學史上社會大眾對於基因、身分認同和選擇最激烈的討論。這個發現證明了此基因左右輿論的力量,幾乎完全顛倒了討論雙方的條件。專欄作家卡羅・薩勒(Carol Sarler)那年十月在《時人》(People)雜誌(在激進社會變革方面,這本雜誌並不算是很強力的喉舌)上寫道,「我們該怎麼評斷這樣的女人,她寧可選擇墮胎,而不願養育一個溫柔體貼、長大後可能(注意只是可能),會愛另一個溫柔體貼男孩的男孩?這樣的母親是功能失調的扭曲怪物,如果她被迫生下那個孩子,只會讓那孩子活在地獄裡。我們要說,任何孩子都不應被強迫擁有這種母親。」
選擇「溫柔體貼的男孩」的說法形容孩子天生的傾向,而非成人扭曲的偏好,說明了論點的反轉。一旦性偏好的發展牽扯到基因,同性戀的孩子瞬間就變為正常,他可惡的敵人才是異常的怪物。

尋覓同性戀基因的動機並非一股行動主義,而是出於無聊。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研究員狄恩・哈默(Dean Hamer)並無意找碴,他甚至也並不在乎自己的身分,雖然他已出櫃,但對任何形式的身分認同、性或其他遺傳學並無特別興趣。他大半生都舒舒服服地坐在「通常都很平靜的美國政府實驗室,裡面從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滿了燒杯和玻璃瓶」,研究一個名叫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ine,MT)的基因調控,這個基因被細胞用來回應銅和鋅等有毒的重金屬。
1991 年夏,哈默赴牛津參加基因調控的科學研討會,發表報告,這是例行的研究報告,一如往常,聽眾反應良好。只是在開放提問時,他卻體驗到教他倍覺無奈的似曾相識之感:聽眾提的問題似乎和十年前演講後提出的問題一樣。下一位發言者是另一間實驗室的競爭對手,他提出的數據證實並延伸了哈默的研究成果,教哈默覺得更加無聊和沮喪。「我明白即使我再堅持這個研究十年,頂多也只不過是為我們小小的遺傳模型打造出立體的複製品,談不上是什麼終生目標。」
在兩場會議之間的休息時間,哈默茫然地走出會場,思緒翻騰。他走進了高街(High Street)別有洞天的布萊克威爾書店(Blackwell’s),走入了同心形的房間,瀏覽生物學的書籍,最後買了兩本書。第一本是達爾文的《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這本 1871 年出版的書因為聲稱人類是來自如猿般的祖先,而掀起論戰風暴(達爾文在《物種起源》,刻意迴避了人類起源的問題,但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他卻一針見血,提出了這個問題)。
《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之於生物學家,一如《戰爭與和平》之於文學研究生:幾乎每一位生物學者都宣稱讀過那本書,或者看似知道其基本主題,但很少有人真正的打開書頁。哈默也從沒有讀過這本書。可是教哈默驚訝的是,他發現達爾文花了很多篇幅談性、性伴侶的選擇,和它對支配行為和社會組織的影響。達爾文顯然認為遺傳對性行為有強烈的影響,然而,性行為和性偏好的遺傳決定因素,也就是達爾文所說的「性的最終因素」,在他看來依舊神祕。
不過,性行為(或是任何行為)都和基因有關係的觀念,已不再風行。哈默買的第二本書,李文汀的《不在我們的基因中:生物學、意識型態和人性》(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則提出不同的觀點。這本在 1984 年出版的書攻擊了人性是由生物學決定的觀念,李文汀主張,被視為由遺傳決定的人類行為元素,其實往往都只是文化和社會為了鞏固權力結構的隨意解釋或操弄。他寫道,「沒有可信服的證據證明同性戀有任何遺傳的基礎,這種說法純屬捏造。」他說,達爾文對生物的演化大部分是對的,但對人類身分認同卻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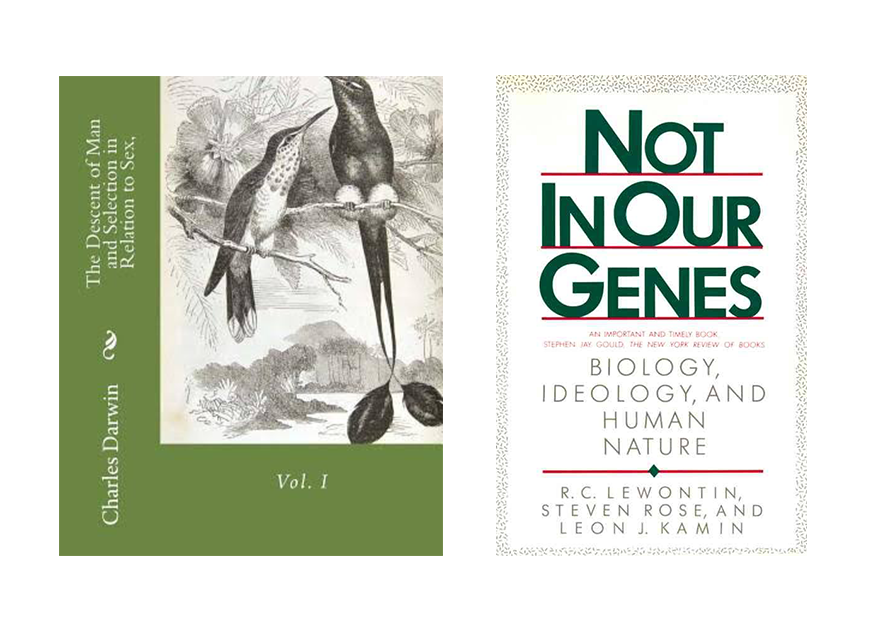
這兩個理論哪個正確?至少在哈默看來,性取向似乎太重要,無法完全由文化的力量建構。「為什麼李文汀如此教人敬畏的遺傳學者,會如此堅定地否認行為可以遺傳?」哈默疑惑,「他不能在實驗室否定行為的遺傳,因此寫了政治文章論戰攻擊?也許這其中有空間,可做真正的科學研究。」哈默打算對性遺傳學做一番速成的了解。他回到實驗室裡探索,但無法由過去學到什麼。哈默搜尋了自 1966 年以來所有科學文獻的資料庫,尋找關於「同性戀」和「基因」的文章,找到十四篇,但搜尋「金屬硫蛋白基因」,卻有六百五十四篇。
不過,哈默還是找到了一些誘人的線索,即使它們被湮沒在科學文獻之中。1980 年代,心理學教授麥可・貝利(J. Michael Bailey)想用雙胞胎實驗研究性取向的遺傳學。貝利採用傳統的方法:如果性取向部分來自遺傳,那麼同卵雙胞胎兩者皆為同性戀的比例,就該比異卵雙胞胎高。貝利在同性戀雜誌和報紙刊登策略性的廣告,招來一百一十對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同性戀的雙胞胎兄弟。(如果現在進行這樣的實驗很困難,不妨想想如果身處 1978 年,那時幾乎沒有男人公開出櫃,而且在某些州,同性戀性行為是犯罪,會受處罰。)
貝利在雙胞胎中尋找同性戀的一致性,結果驚人。在五十六對同卵雙胞胎之中,兄弟兩人都是同性戀者比例為 52%。五十四對異卵雙胞胎中,兩人都是同性戀的比例為 22%,低於同卵雙胞胎的比例,但仍然明顯高於一般兄弟都是同性戀的 10%。(數年後,貝利會聽到如下的驚人案例:1971 年,兩名加拿大孿生兄弟在出生後數週內被分隔兩地,一個被富裕的美國家庭收養,另一個則由他的親生母親在環境截然不同的加拿大養育。兩個外表幾乎一模一樣的兄弟對彼此的存在一無所知,直到他們在加拿大的同性戀酒吧邂逅。)
貝利發現,男同性戀的原因不僅僅是基因,家庭、朋友、學校、宗教信仰和社會結構的影響也明顯會改變性行為,以至於同卵雙胞胎中,一個是同性戀,另一個是異性戀的機會高達 48%。也許需要外部或內部的觸媒,才會釋出不同性行為模式。毫無疑問,圍繞在同性戀周遭無孔不入的壓抑文化信念十分強大,足以影響雙胞胎之一選擇「異性戀」身分,但另一個不受影響。
但是這個雙胞胎研究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基因影響同性戀的力量高於對其他的影響,如第一型糖尿病(雙胞胎的一致率僅為 30%),且對身高的影響差不多(雙胞胎的一致率約為 55%)。貝利大幅改變了關於性身分認同的討論方向,由 1960 年代「選擇」和「個人偏好」的修辭,轉為生物學、基因學和遺傳。如果我們不認為身高、閱讀障礙或第一型糖尿病是源自選擇,那麼就不該把性身分認為是選擇。
但是,它是由一個或多個基因造成?那個基因是什麼?位於哪裡?哈默如果要找出「同性戀基因」,就需要更大規模的研究;最好能找到可以追蹤多個世代家族的性取向。為了這個研究,哈默需要尋找新的補助經費;可是研究金屬硫蛋白調節的聯邦研究員要到哪裡找經費,來追獵影響人類性取向的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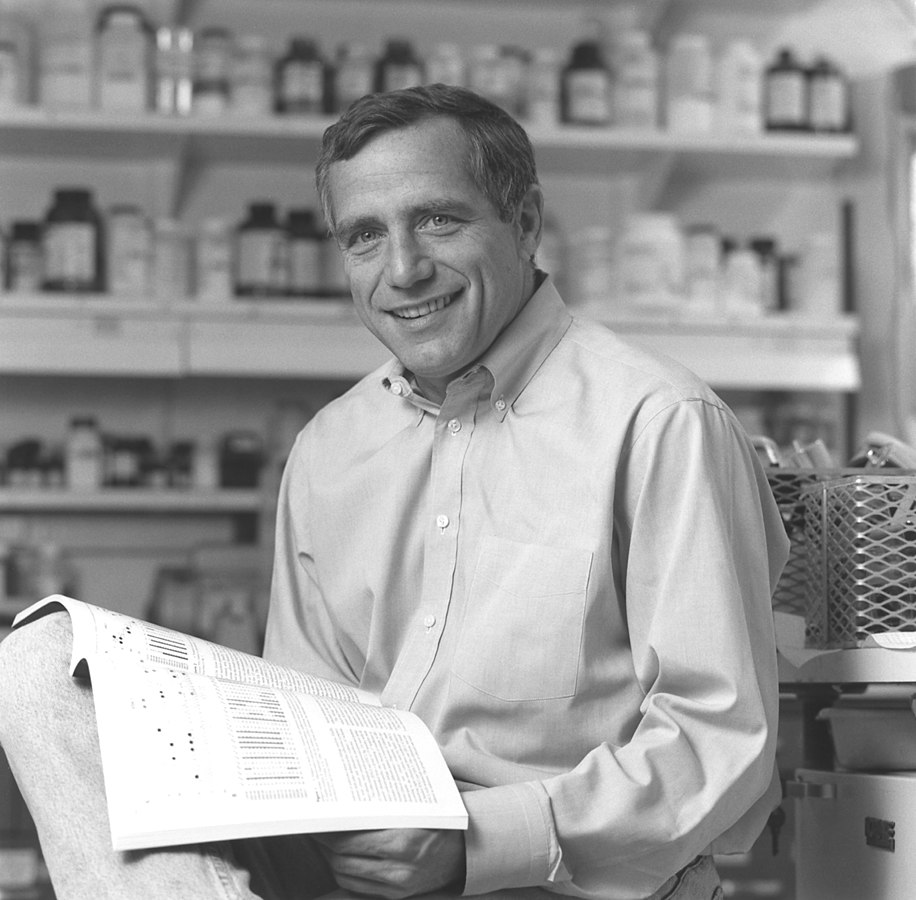
1991 年初,兩個發展使哈默得以展開追獵。第一個是人類基因組計畫的宣布。儘管人類基因組的確實序列在十年之內都還不能確知,但順著人類基因組繪製關鍵遺傳路標,使尋找任何基因都變得容易許多。哈默要繪製和同性戀相關基因位置的想法,如果在1980 年代,就方法論而言還很難作業,但十年之後,遺傳標記就像標誌燈,沿著大多數染色體發光,至少在概念上,找出同性戀基因是可行的。
第二個發展是愛滋病,這種病在 1980 年代後期席捲了同性戀社群,再加上運動人士和病人經常以公民不服從和對立抗議的方式煽動,使國家衛生研究院終於撥了上億美元進行愛滋病研究。哈默就以愛滋相關研究的藉口追尋同性戀基因。他知道卡波西氏肉瘤這種從前很罕見,也不會疼痛的腫瘤,以相當驚人的頻率出現在罹患愛滋病的男同志身上,因此他推斷,或許這種肉瘤的進展和同性戀有關;如果真是如此,找出和其中之一相關的基因,就可能會引導我們辨識出另一個基因。
這個理論大錯特錯:後來發現卡波西氏肉瘤是由病毒引起,經性行為傳播,主要發生在免疫缺陷的人身上,這也說明了它為什麼會和愛滋一起發生。不過,哈默的這種戰術極巧妙,1991 年,國家衛生研究院撥了七萬五千美元給哈默進行新研究案,也就是要找出同性戀相關基因的研究。
1991 年秋,#92-C-0078 研究案開始進行。到了 1992 年,哈默已招募一百一十四名同性戀男子參與研究。他打算用這些人創造詳細的族譜,決定性取向是否發生在家族之內,描述它的遺傳模式,並為這個基因定位。但哈默知道,若是想要找出同性戀基因的位置,遇到同性戀的一般兄弟會容易得多。雙胞胎基因相同,而一般兄弟卻只有基因組的某部分段落相同。如果哈默能找到都是同性戀的兄弟,就可以找出兩人共有的基因組段落,而隔離出同性戀基因。那麼在族譜之外,哈默還需要這種兄弟的基因樣本。他的預算足夠讓他請這樣的兄弟搭機來華盛頓,並提供四十五美元的津貼,讓他們度過一個週末。這些兄弟通常都分隔兩地,如此一來,他們得以團聚,而哈默則可以採得他們的血液。
1992 年夏末,哈默已經收集了近千名家庭成員的相關資料,也為一一四名男同志做好家譜。6 月,他坐在電腦前準備看資料,幾乎馬上感到理論得到驗證的喜悅:就如同貝利的研究,哈默研究中,手足之間的性取向一致性較高,約 20%,幾乎是一般人(10%)的兩倍。研究已有了真實的數據,只是,他的喜悅很快就冷卻了。哈默檢視這些數字,卻看不出還有什麼奧妙。除了同性戀手足之間的一致之外,他找不出明顯的模式或趨勢。
哈默洩了氣。他試圖把這些數字分門別類,但無濟於事。他把這些人的家譜畫在一張張紙上,正準備把它們放回檔案堆裡時,卻發現了一種模式,一種唯有人眼可分辨的微妙區別。原來他在畫他們的家譜時,把每一個家族的父系親屬畫在左邊,母系親屬放在右側邊,並以紅色標出男同志身分。而在整理這些紙張時,他本能地辨識出一個趨勢:紅色標記往右集中,而沒有標記的男性則往左集中。男同志較常有同性戀的舅舅──只限母系。哈默在同性戀親屬的家譜上下搜尋,他稱之為「同性戀尋根計畫」(gay Roots project),這個趨勢越看越明顯。母系表親有較高的一致性,但父系堂親則否。

這樣的模式代代相傳。在經驗豐富的遺傳學者眼裡,這個趨勢意味著同性戀基因必然是由 X 染色體攜帶。哈默現在幾乎可以在腦海裡看到如同朦朧陰影的它,世代傳承的遺傳元素,雖然不像典型的囊狀纖維化或亨丁頓氏症的基因突變那般外顯,但卻確實循著 X 染色體的軌跡。
在典型的家譜裡,某位舅公也許有可能是同性戀(家族史常常模糊不明,歷史的同性戀衣櫃往往比如今的黑暗得多,但哈默已由一些家庭收集到兩代甚或三代的性身分資料),那位舅公兄弟的兒子全都是異性戀,因為男人不會把 X 染色體傳給兒子(所有男人的 X 染色體必定來自母親),但他姊妹的兒子卻可能是同性戀,而那個兒子的姊妹的兒子也可能是同性戀:這是因為男人和其姊妹及姊妹的兒子有部分 X 染色體相同之故。
如此這般,舅公、舅舅、最年長的外甥、外甥的手足,世代橫向發展,朝前橫向行進,就像西洋棋騎士的走法。哈默就這樣突然由一種表現型(性偏好)轉移到染色體上的潛在位置──基因型。他還不能確定同性戀基因,但他已證明與性取向相關的一段 DNA 可以確實在人類基因組定位。
但是在 X 染色體的哪裡?哈默的研究對象轉為四十對同志兄弟,他採取了他們的血液。如果我們暫時假設同性戀基因確實位於 X 染色體的一小段上,無論它在哪裡,四十對兄弟分享這一段 DNA 的頻率都應該比一個是同志,一個是直男的兄弟高得多。哈默沿著基因組計畫定義的路標,透過仔細的數學分析,持續地縮小 X 染色體上可能的區域,讓它越來越短。
他沿著這個染色體的整串長度,穿過了一連串二十二個標記。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四十對同志兄弟中,哈默發現三十三對兄弟都有 X 染色體上一段稱為 Xq28 的段落。如果是隨機分布,那麼應該只有一半的兄弟(也就是二十對)會分享那個標記。額外十三對兄弟攜帶同一標記的機會微乎其微(不到萬分之一)。因此,在 Xq28 附近的某處,應有一個確定男性性別認同的基因。
Xq28 立即造成轟動,哈默說,「電話鈴響個不停,實驗室外都是電視臺的攝影記者,信箱和電郵都爆滿。」立場保守的倫敦報紙《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寫道,如果科學能隔離出同性戀基因,那麼「就能用科學消除它。」另一份報紙則寫道,「許多母親一定會內疚。」還有報紙用了「遺傳暴政!」的標題。
倫理學家想了解身為父母的會不會藉著測驗胚胎,「了解其基因組成」,以避免生下同性戀的孩子。有位作者寫道:哈默的研究「的確辨識出男性個體可以分析的染色體區域,但這項研究為本的任何測試結果只不過是再一次提供了某些男性性取向的概率工具。」哈默名副其實地遭左右夾擊,反同性戀的保守派認為,哈默把同性戀歸為遺傳,用生物學為同性戀辯護;而擁同性戀派則指責哈默進一步推動「同性戀測試」的幻想,可能因此推動新的檢測和歧視同志的機制。
哈默自己的作法中立、嚴謹、科學,且常常到了極端的地步。他不斷改進自己的分析,用各種測驗測試 Xq28 這一區段。他考量 Xq28 編碼會不會並非同性戀基因,而是「娘娘腔基因」(只有男同志才敢在科學論文中用這個詞)。可是並非如此:共同擁有 Xq28 的男性在有關性別的行為上,或者在傳統的陽剛表現上,並沒有特別明顯的變化。它會不會是「肛交接受方」(receptive anal intercourse)基因(他的措詞是「是否底部朝上(bottoms up)基因?」)可是同樣也沒有關聯。會不會與叛逆有關?或者是反抗壓抑社會風俗的基因?違規行為的基因?他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假設,可是都沒有聯繫。他徹底消除了所有的可能,只剩下一個結論:男性的性認同有部分是由 Xq28 附近的一個基因所決定。
(哈默談「同性戀基因」。)
自 1993 年哈默在《科學》發表論文以來,也有幾個團隊試圖驗證哈默的數據。1995 年,哈默自己的團隊發表了規模更大的分析,印證了他們原來的研究。1999 年,一個加拿大團隊想在一小群同性戀手足身上印證哈默的研究,卻未能找到和 Xq28 的連結。2005 年,在可能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研究中,共有四百五十六對手足參與了研究,雖然並沒有發現與 Xq28 的連結,但發現了和第七、八、十對染色體的關係。2015 年,在另外四百零九對手足的另一項詳細分析中,再度證實與 Xq28 的關連(儘管微弱,而先前證明和第八對染色體的關係也再經驗證)。
在所有研究中,最有趣的特點或許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分離出影響性認同的實際基因。連鎖分析並沒有辨識出基因本身;它只是辨識出可能找到基因的染色體區域。在將近十年密集的搜尋之後,遺傳學家找到的並不是一個「同性戀基因」,而是一些「同性戀位置」。位於這些位置的某些基因確實很像是性行為規範者的候選人,但這些候選基因沒有一個經實驗證明和同性戀或異性戀相關。比如一個位於 Xq28 區域的基因編碼一種能夠調節睪丸酮受體的蛋白質,而眾所皆知,睪丸酮正是性行為的掌控者。但這個基因是否就是學者長期以來一直在 Xq28 上尋找的同性戀基因,依舊不得而知。
說不定「同性戀基因」根本不是基因,至少不符合基因的傳統定義。它可能是一段 DNA,可以調節坐落在它附近的基因,或者影響離它很遠的基因。也許它位於內含子之中(是打斷基因,把它們分解成模組的 DNA 序列)。無論這個遺傳因素的分子身分為何,有一點可以確定:我們遲早會發現影響人類性別認同的遺傳元素確切的本質。
哈默對 Xq28 的看法是對是錯並不重要。雙胞胎研究已清楚顯示,幾個影響性別認同的決定因素是人類基因組的一部分,而隨著遺傳學家找出更有力的方法為基因定位、識別和分類,我們終將找到其中一些決定因素。就像性別,性身分認同不太可能只由一個單一主調控因素規範,這些因素可能按階級組織,主要調節者在上方,複雜的綜合和修正者在底部。不過,和性別不同的一點是,性別認同不太可能由單一主調節者進行管理。發揮許多小影響力的多個基因,尤其是調節和整合來自環境資料的基因,較有有可能牽涉性身分的決定。不可能會有異性戀男人的 SRY 基因。
.png)
作者穆克吉醫師以一場感傷的家族探病之旅為始,細細描述破譯遺傳基因之謎的百年過程,數以千計的科學家如何透過不斷實驗及互相合作、彼此競爭,解開一道道謎題,又衍生一項項謎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