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6 年 9 月 2 日,星期天稍早,國王的烘焙師傅湯瑪斯.法爾諾(Thomas Farynor)在位於普丁街(Pudding Lane)的家中,被濃煙給嗆醒。他發現火焰在樓梯間中快速延燒。法爾諾叫醒他的兒子女兒以及女僕,要大家從樓上的窗戶爬出去。那位女僕因為有懼高症,因此堅決留在家中。法爾諾領著一對兒女,從屋頂邊緣安全抵達鄰居家中。而那位女僕,就是「倫敦大火」(Great Fire of London)的首位罹難者。

三小時後,在倫敦另一端的席斯巷,賽謬爾.佩皮斯與妻子被女僕搖醒。女僕珍.畢爾齊(Jane Birch)表示自己從房間窗子往外看,發現遠方有一場大火。佩皮斯套上睡袍,走進女僕的房間看了一眼後,覺得這只是一件小事,就回房繼續睡覺了。
早上七點,佩皮斯起床後,珍告訴他昨晚大概有三百間房子被大火摧毀,佩皮斯才注意到事情的嚴重性。
他步出屋外,徒步走到河邊,從較高的位置往倫敦橋看去,眼前「是一片無盡延燒的大火,燒遍倫敦橋北側的街道。」他觀看情勢,發現火已經沿著河岸燒到斯蒂爾雅德。民眾都急著將個人物品搬出家中,把行李拖到河邊放上船。
佩皮斯往回走的時候,看見街上有不少人將貴重物品搬到教區教堂,認為石造建築能抵禦烈火。此外,他還發現窮人怎麼樣也不肯棄家逃生,等到火勢對生命構成威脅,才跑到離最近的河岸階梯,努力攀上逃生船。佩皮斯注意到鴿子也不願離開屋子,只是在窗戶與陽台邊盤旋,直到翅膀被火苗燒傷,墜地而亡。
其實倫敦人對火災習以為常,在佩皮斯的日記中,就紀錄了另外十五起火災意外,但從來沒有一場的規模像倫敦大火如此驚人。當時因為氣候乾燥、強勁東風吹拂,再加上民眾為了迎接冬天而囤積在地下室與後院的木材,火勢才會如此猛烈。此外,因為起火時間是半夜,所以烈火就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大肆蔓延。以上就是倫敦大火之所以難以撲滅的原因。
政府當局自以為能夠成功滅火的態度,也讓情況雪上加霜。倫敦市長湯瑪斯.布魯茲沃斯爵士(Sir Thomas Bludworth),太晚才下令用槍砲將房屋擊垮。
不過最根本的問題,其實是房屋的結構。起火的房子皆歷史悠久,而且它們都是用木頭搭建而成。另外,每間房子還緊密相依,建築與建築間的巷弄空間相當狹小。木造建築起火時,樑柱與牆壁會往外崩解,加速火花與火苗的擴散。河邊的這排住宅,裡面還堆放不少燃油、瀝青、焦油、樹脂、麻線、繩索、白蘭地還有其他易燃物品,這些物品也全都堆放在一起。
綜合以上因素,許多街道就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際成為火海。湯瑪斯.文森(Thomas Vincent)回想當時狀況,表示:
嘎噠、嘎噠、嘎噠,這是烈火在耳邊燃燒的聲響,彷彿有幾千架鐵馬戰車在石子路上狂奔。如果你看著街上一排房子的窗戶,突然間,火苗會從窗戶竄出來,整排街開始燃燒,好像每戶人家都是生火打鐵的鐵舖似的。火焰在路中央融合,眼前變成一片火海。接著房子會轟隆、轟隆、轟隆地倒塌,街道兩側的建築向彼此倒下,露出房屋的地基。
9 月 2 日黃昏時分,佩皮斯乘著小船,在河面上觀察火勢,但是現場溫度過高,而且空氣中飄著燃燒中的碎屑,他只好返回岸邊。佩皮斯走在未受火勢波及的河岸邊,隨後往一家酒館走去。他在那裡看著燃燒中的倫敦,寫道:
天色越來越黑,火勢越來越大,在街道轉角、屋頂尖塔之間,在教堂與房舍之間,最遠到城市邊緣的小土丘,都籠罩在猛烈豔紅的火光之中。這場火的殘暴程度,完全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火苗可以比擬。
我們站在遠方,太陽西下,從橋的這頭到彼端,全都被烈火所覆蓋,連後方的小丘也冒著熊熊烈火,延燒有一英里遠。見到這番場景,我不禁落淚。教堂、房子,全都付之一炬,烈火的聲響、房屋崩毀的聲音更令人惴惴不安。
隔天,9 月 3 日星期一,約翰.伊弗林也從泰晤士河南岸望向窗外,看著城市裡的慘況。他說:
火勢熏天,蒼穹如同燃燒中的烤箱頂部。我向上帝禱告,希望此生不要再看見這般場景。幾萬棟房屋現在竟深陷一片火海!燃燒的噪音、房屋的崩塌聲、烈火延燒的轟隆聲、女人小孩的尖叫聲,群眾急忙奔走的模樣,高塔、房舍、教堂崩塌的景象,這真是一場令人驚駭的災難。
若你加入佩皮斯或伊弗林的行列,也會看見河面上飄著許多貴重物品。民眾把珍貴的財物丟入水中,大家都擠在船上,懷裡抱著傢俱、樂器、毛毯、現金以及銀器。整座城市的高塔及數十棟教區教堂,全都在烈焰火光的映襯下,成為一幢幢剪影。空中飄著漆黑的灰燼,火焰延燒的路徑中,地面上的一切被燒得一乾二凈。在某些區域,溫度甚至直逼攝氏一千七百度。
延燒範圍的中心點,是倫敦最宏偉的建築:聖保羅大教堂。這座教堂挺過了所有降臨在倫敦的災難,屹立不搖將近六百年。但是這次,教堂屋頂上的鉛也遇熱融化,沿著牆面向下流淌,濺灑在偉人的墳墓上。巨大石柱也因為高溫而碎裂。這座象徵倫敦悠久歷史的尊榮建築也崩壞為塵土。
有的人說這場火燒了四天才熄滅,也有人堅持是五到六天。不過在大火發生的四個月後,住宅的地下室裡仍有些許物品持續悶燒,只要空氣竄入又會引發火苗。佩皮斯發現,該年冬天,地窖還是時不時飄出濃煙,最後一次則是發生在 1667 年 3 月 16 日,距離倫敦大火已有半年之久。
烈火消退後,民眾開始注意到焚燒後的殘骸。某個十五歲的少年威廉.塔斯威爾(William Taswell),在 9 月 6 日當天來到大教堂,那時火勢仍在延燒。他描述路上的景象:
星期四太陽一升起,我就迫不及待來到聖保羅大教堂。地板好燙,我的鞋子都要燒焦了,而且空氣的溫度之高,我在走到弗利特橋的路上,還得停下來休息幾次,整個人精神委靡,差點都要暈過去。停下來喘口氣之後,我終於來到聖保羅。看到教堂的鐘融化時,我實在不可置信,希望能有人陪我一起承擔如此激動的情緒。
崩塌毀損的牆面,還有教堂周圍的石造結構不斷墜落,掉在我腳邊發出巨響,差點都要把我壓死……我忘了說,那個時候我在教堂東側的牆邊看到一具屍體,在高溫中顯得相當乾癟。那具屍體乾癟蠟黃,身上沒有半吋肌膚完好如初。她應該是個跑到教堂避難的虛弱老太太,以為火絕對不會燒到這裡。她身上的衣服都已燒焦,四肢變成焦炭。

隔天,約翰.伊弗林也像塔斯威爾一樣巡視整座城市。他說:
今天早上,我徒步從白廳走到倫敦橋,沿途經過弗利特街、聖保羅大教堂旁的盧德門山(Ludgate Hill)、齊普賽街、交易所、主教門(Bishopsgate)、艾德門(Aldersgate),還有莫菲爾德(Moorfields),接著來到康希爾等地,一路上困難重重、難以行走,必須攀過冒著煙的碎石堆,還不時會迷失方向。
而且路面溫度過高,鞋底彷彿都要融化……回程路上,我發現宏偉的聖保羅大教堂現在成為一片廢墟,場面實在令人悲痛……教堂中由鉛和鐵鑄成的裝飾,還有鐘跟金屬嵌板全都融化了。裝飾精緻的默瑟小教堂(Mercers’ Chapel)、美輪美奐的交易所、莊嚴的基督堂(Christ Church)、所有公會大廳、華麗堂皇的建築、拱門以及巍峨的大門入口,全都被燒成灰燼。
噴泉都已乾枯傾頹,裡頭殘留的水還在滾沸的狀態。地下室中的裂縫、水井、地牢還有曾經用來堆放貨物的倉庫,仍飄出焦黑的惡臭以及濃煙。就這樣走了五、六英里,路上看不見半塊完好如缺的石頭或木材,全都被燒成煤炭或白如雪的石灰。
走在被火燒盡的倫敦中,每個人看起來要不是像在荒蕪的沙漠遊蕩,要不就像在被敵軍砲火摧殘的死城裡徘徊。動物屍體、床單寢具還有其他易燃物飄出的臭味,令人難以呼吸。
而且我只能挑寬敞的道路走,完全無法走進狹窄的小巷。無論是地面還是空氣中,濃煙跟炙熱的高溫持續籠罩,我的頭髮都要燒了起來,腳步也越發沉重。窄巷跟小路已經堆滿廢棄物。有時走著走著,會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唯一辨識方向的辦法,是靠著那些已成斷垣殘壁的教堂或公會大廳,如果還有塔樓或尖頂結構殘留下來,才能認得出路。
烈火熄滅後,民眾才得以準確估算破壞的規模。他們發現從倫敦塔到聖殿教堂(Temple Church),也就是從泰晤士河到北側市牆之間的區域,全都被大火摧毀。除了聖保羅大教堂,倫敦有八十七座教堂與六間小教堂都成了廢墟,甚至完全倒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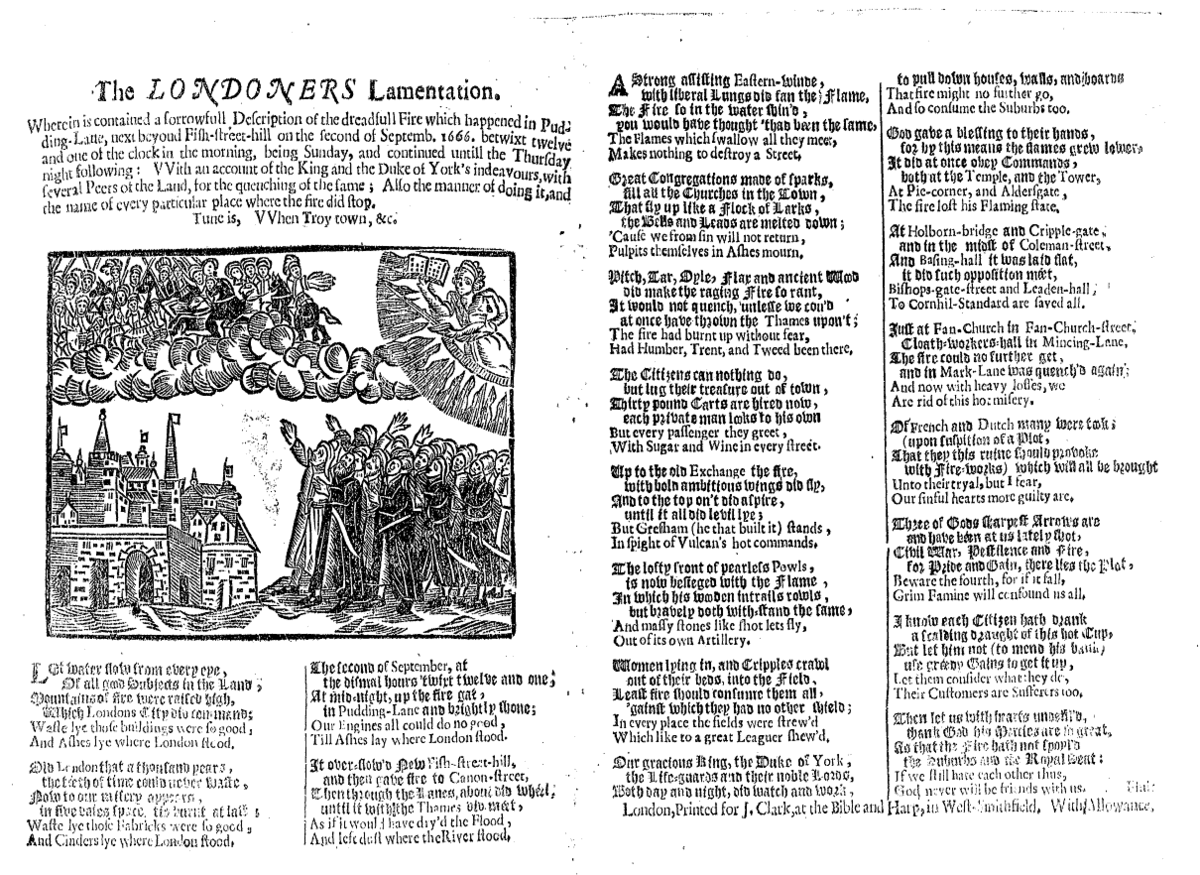
(Source:Wikimedia)
五十二座同業公會的大廳已不復存在,皇家交易所、海關大樓(Customs House)還有四間監獄的命運也是如此(許多囚犯還趁亂逃獄)。倫敦石裂成碎塊,其中體積最大的一塊也只不過長兩英尺。受大火波及的區域面積,總共有四百三十六公頃,總計超過有一萬三千兩百座房屋被燒成灰燼。
雖然這只是整個倫敦的五分之一,但這個區域卻是最讓倫敦人自豪的地方,涵蓋了珍貴的歷史文物與建築、市政管理中心與交易通商場所。經過這場大火,總共有八萬人無家可歸。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大家幾乎都在四天內找到棲身之所。
在 6 日星期四與 7 日星期五這兩天,在通往伊斯林頓(Islington)以及海格(Highgate)兩地的道路邊,都有人紮營野宿。到了隔週星期三,睡在路邊的民眾都已消失,暫時設立的教堂與市場也開始營運。
當然囉,房地產售價與房租直線飆漲,但是人們都願意一起合住。有的人試圖在舊址上搭建簡便的小磚房,不過冬天將至,而且政府無力提供多餘的治安防護,多數人最後仍然搬離。這時要特別警覺,因為生活已相當艱難,民眾也無心恢復舊教區的巡守制度。如果在夜裡遭到襲擊,沒有員警會拿著火把前來協助。佩皮斯在傍晚搭著馬車經過這片廢墟時,手中可是握著出鞘的劍。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