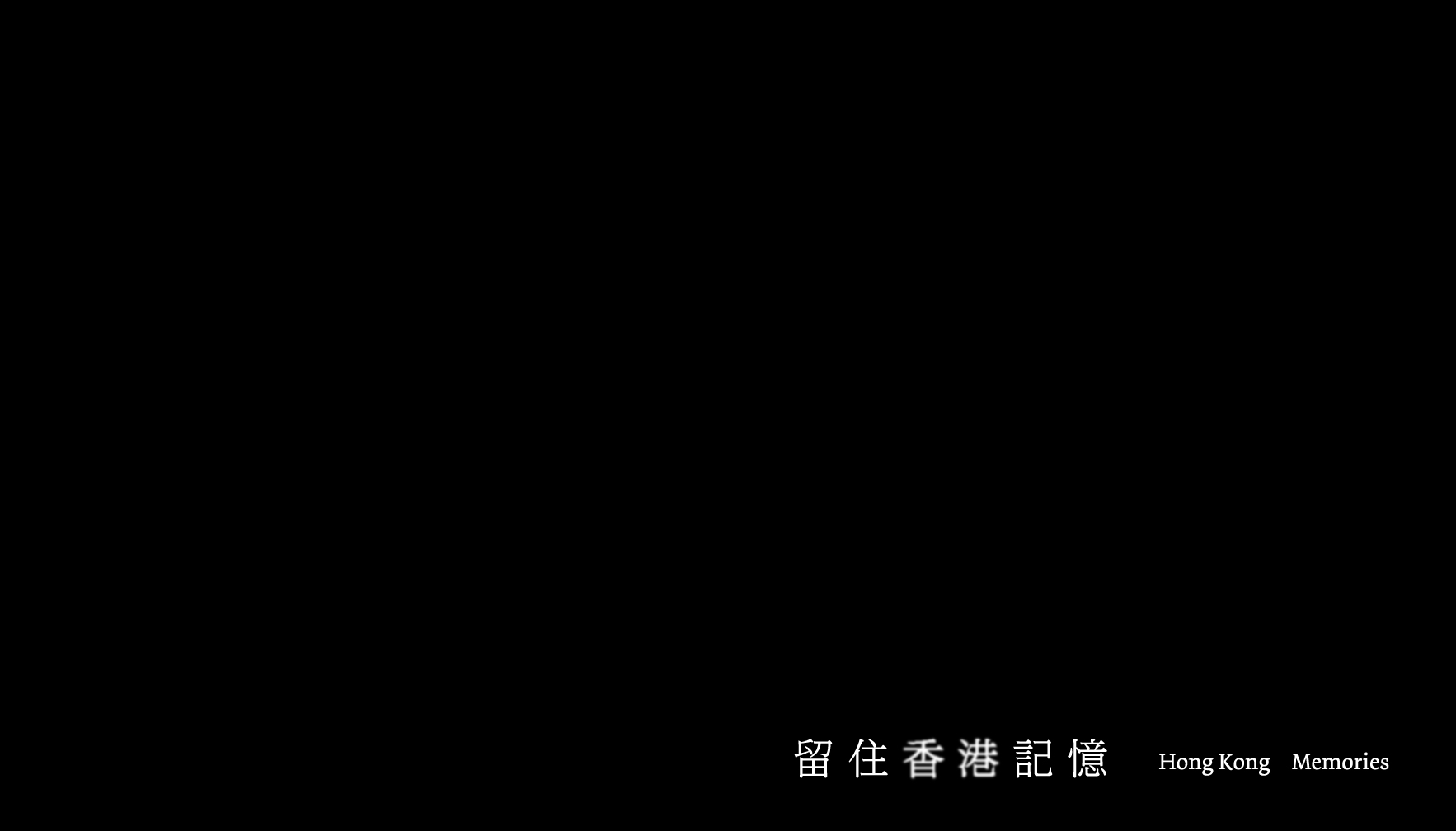總而言之,香港人既有的文化、獨特的歷史,在香港的課堂都不受重視,而且日益受大中華意識排擠。
本人撰寫《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這本以香港本土觀點撰寫的香港通史,旨在抗衡主流教育「去香港化」的大勢。縱然這本書必然會遭既得利益者斥為「偏激」,肯定不會成為歷史課的教科書。但本人希望拙著能成為年青學子的課外讀物,自己國家自己救、自己歷史自讀。
下文為《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的撮要大綱,部份內容曾收錄於《香港民族論》及《香港本土論述2013~2014》。

香港之主權移交予中國已逾十六載。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本土意識,卻有增無已。2006年保衛中環天星碼頭之社會運動,為香港本土社會運動揭開序幕,之後香港出現了一連串包括保衛皇后碼頭、保衛菜園村等以本土及地區認同為出發點的社會運動。民俗學者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陳雲,2011)主張香港為有獨特身份與歷史的城邦,並抗拒中國的政權、旅客及移民的入侵。此論使本土派與大中華派之爭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研究國族主義的台灣學者吳叡人甚至大膽指出,香港國族主義經已形成。
只是目前的討論,往往流於情感上之宣洩。比如城邦論中指斥中國遊客及移民為蝗蟲,已經淪為逞口舌之勇的仇恨語言。吳叡人認為香港國族主義若要進一步發展下去,就必須要省察香港的歷史,那方能為香港本土運動找到出路(袁偉熙、何雪瑩,2013)。
本文旨在探討香港身份認同,自開埠之前到主權移交後的發展史。筆者希望能透過梳理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讓本土派與大中華派之間的論爭,可以由情緒化的人身攻擊,回到理性的辯證之上。
社會科學在探討國族主義時,多視之為近數百年的現代過程。比如葛爾納(Ernest Gellner)認為國族主義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工業革命令近代國家須確保有充足的人力資源,令國家須定劃疆界,並促進界內民眾的向心力(Gellner, 1983)。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則認為近代傳媒的發展、以及殖民主義的制度安排等,令不同社群原先互不相識的社會精英產生作為命運共同體的想像。這些精英之後發起國族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建立國族國家(Anderson, 2006)。
史安東(Anthony Smith)卻指出國族主義雖為現代產物,其誕生卻不是一個由無到有的過程。猶太人的身份認同、以及中國華夷之辨的思想均有逾千年的歷史。縱然兩者嚴格上並稱不上是國族主義(前者乃宗教身份、後者乃文化認同),這些前現代的族群歷史卻對之後國族主義之發展影響深遠(Smith, 1987)。簡要而言,國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國族主義卻會從前現代的族群史中有意無意地汲取養分。

那麼香港前現代的族群史又是甚麼呢?坊間普遍會將新界史視為香港史前史。這些說法大多會輕輕帶過從百越到唐代的歷史,然後提及五大氏族如何於宋元之交遷居新界,客家人如何隨五大氏族遷入,這些族群之後如何開拓新界,然後面對清初遷界、復界的挑戰。但是,香港開埠時有本地(廣府)、客家、福佬及蜑家等四大族群,主流版本的新界史卻大多是本地與客家這兩大陸上族群的歷史,比較少著墨於福佬及蜑家這些海洋族群的歷史。
此外,新界其實要到1898年才成為香港的一部份,那時候香港已開埠五十七年。當時新界社會與香港社會存在着極大差異,令英國決定要以間接管治的方式,將新界與市區分開管治。要到六、七十年代,隨着香港政府開拓新市鎮,新界才逐漸融合為香港的一部份(Hayes, 2006)。香港開埠時,新界大氏族並沒有擔當太重要的角色,早期香港華人精英亦多為海洋族群的成員。
那麼說,香港史前史就必然是福佬及蜑家等海洋族群的歷史。這些族群並非如陸上族群那樣忠實遵從儒家價值,他們在由陸上族群主導的中華帝國體系中被邊緣化,多為陸上族群所歧視,甚至被視為未開化的化外之民。
在華南沿岸的海洋族群又是從那裡來的呢?我們知道嶺南本非中華帝國的一部份,其原住民被中原人士稱為百越。到秦代,中華帝國才首次對嶺南實行管治,而且管得不久。秦末天下大亂,龍川縣令趙佗據嶺南自立,成立南越國。雖然南越國為漢人稱王的外來政權,其屬民卻主要是原住民,是以朝廷亦以百越風俗管治,執政階層的舉止文化亦漸百越化。

要到漢武帝年間,漢帝國才能夠開始長期佔領嶺南地區。但當中的人口始終以原住民為主,他們直到宋朝仍然拒絕漢化,而直到唐初嶺南每十數年就會有一次叛亂(黎明釗、林淑娟,2013)。而駐防嶺南的將領,偶然會煽動原住民叛亂,令形勢更為複雜。東晉末年,盧循興兵叛亂,號召華南的原住民起事。叛軍攻佔廣州後,欲北伐首都建康,卻被劉裕率軍擊潰。部份原住民事後被押往大嶼山,淪為替朝廷產鹽的奴隸。有研究指這場叛亂,很可能是華南地區盧亭傳說之起源(孔誥烽,1997)。南朝陳開國君主陳霸先亦為駐嶺南將領,他得到粵西原住民首領冼夫人襄助,得以北伐登基。
直到唐代,嶺南一帶仍然未大規模漢化,漢人之活動範圍,亦只限於廣州和粵北(曾華滿,1973)。到了宋代,因北方受遼、金、西夏等國威脅,中國的發展重心南移。珠江口一帶開始修築河堤發展農地,並在近岸地區引沙填海造地。今日的南海、番禺、順德、中山等地,有很大部份是宋、明、清三代填出來的。修堤、填海均需要大量投資,亦有一定風險,而爭奪新填地亦會帶來紛爭。最初只有南遷漢人,靠考取功名的族人取得官方庇蔭,方能參與填海造地的工程。
但填海造地的潛在回報實在豐厚,令嶺南原住民禁不住誘惑,不惜放棄逾千年的堅持,要令自己成為漢人。畢竟只有漢人,才能考取功名、買賣土地。原住民的漢化在明代中業尢其普遍,他們的做法通常是修撰族譜,聲稱自已是宋代南遷漢人之後人。為了證明家族的土地擁有權,這些族譜大都會畫蛇添足地指出祖先當年是取得官方批文,獲准遷居嶺南:儘管這其實是明代才有的制度。
而族譜亦會攀附鄰近已考取功名的同姓人,聲稱他們與己族同根。他們根據《朱子家禮》的規定,修建宗祠,以定期祭祠儀式凝聚族人。這樣,新興的宗族於明清的嶺南展開了圈地競賽。較遲漢化的原住民,以及圈地運動的失敗者,便只有兩條出路。一是遷居荒山,成為瑤人。另一個選擇是逃到江河大海,以舟為居。這群水上人便成為了蜑家族群(Faure, 2007)。

閩南族群亦是在香港附近生活的海上族群。他們源自福建南部,故被稱為福佬人。閩南族群在香港為少數族群,分佈卻是眾族群之中最廣的。他們原聚居於福建泉州、漳州及廣東潮汕,後隨貿易航線遷居至廣東沿岸、雷州半島及海南島。不少閩南人遷出中華帝國的勢力範圍,植根於台灣及南洋諸國,成為這些國家的重要組成族群。
閩南族群的祖先,為漢族遺民及福建原住民的後代。戰國初年,越為楚所滅,部份越國遺民遷居當時尚未漢化的福建中部,並與原住民融合為閩越族。閩越一度自立為國,到漢武帝時才被納入中華帝國體系。即或如此,福建一帶處於帝國邊陲,仍遺有閩越遺風。到西晉末年永嘉之亂,衣冠南渡,漢人世家開始遷入福建。閩越人終採納漢文化,並以漢人世家自居,形成了閩南族群。
由於福建缺乏農地,閩南族群遂遷往泉州、漳州,打算出海謀生。初時海上絲路的貿易均為廣州所壟斷,到唐末黃巢之亂,叛軍攻入廣州,屠殺港口內的回教商人,以泉州為基地的閩南人隨即成為叱吒南海的海洋族群(湯錦台,2013)。
與陸上族群相比,海洋族群比較不看重儒家的倫常規範。能透過科舉作上向社會流動,是陸上族群忠於儒家倫常的動機,亦為陸上族群融入中華帝國體系的國本,但蜑家一直被視為化外之民,到清代雍正期間才獲平權。縱使有權考科舉,其子弟卻無法與陸上大宗族所辦的書院教育出來的子弟競爭。
閩南族群以航海貿易為生,亦不擅於科舉。是以在人倫的問題上,海洋族群遠比陸上族群開放:同性戀是海洋族群的成人禮,船上男女關係少繁文褥節,女性亦能憑實力得到認同。儒家倫理少求鬼神,多堅持克己復禮。祭神卻是海洋族群生活的核心,他們多生活禁忌,宗教活動極其華麗,凡事問卜神明,只求神明協助他們出海冒險,少祈求神明保守倫理社會秩序。簡而言之,海洋族群及價值觀與中華帝國體系格格不入(Anthony, 2003)。
縱然海洋族群在中華帝國體系中被邊緣化,但海上絲綢之路頻繁的貿易,令海洋族群有機會謀生甚至致富。宋代西域貿易路線斷絕,令當時中國倚靠海上絲路作對外貿易。到南宋失去華北大片土地,令朝廷須從海外貿易徵收稅項,令南宋中國具有海洋性格。蒙古滅宋後,元代亦承襲了宋代的貿易網絡,海洋貿易仍然興盛(Lo, 2012)。
元末民變,中華帝國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張士誠及方國珍都曾從海外貿易獲得經費。朱元璋擺平其競爭對手後,決意要將所有海外貿易納入朝貢體系,以免貿易滋長競爭勢力。
明代立國不久,仍效忠於方國珍的舟山群島居民叛亂,最終朝廷下令舟山居民內徙並頒佈海禁令。海洋族群倚靠海洋貿易為生,朝廷的禁令意味着他們無法合法營生。他們有的遷居南洋諸國,以外國使臣的身份參與朝貢貿易。但為數更多的海洋族群被迫從事非法活動,比如是從事走私貿易,有些甚至還當上海盜(曹永和,2000)。他們包括了明代中葉由江浙、閩南海商與日本浪人所組成的倭寇,鄭芝龍、鄭成功等明末清初的閩南海上武裝勢力,以及於乾隆、嘉慶年間活躍於華南的蜑家及閩南籍海盜(Anthony, 2003)。
海上族群的文化與陸上族群格格不入,反倒令他們易與外國人合作。葡萄牙人在立足澳門之前,一度於浙江外海的雙嶼島與倭寇從事走私貿易(Chin, 2010)。鄭芝龍興起前,曾任荷蘭人的通譯,借荷人之勢力嶄露頭角。其孫的東寧王國,則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業務以至軍事上的合作(曹永和,2000)。
清代中葉的蜑家籍海盜一度成為越南西山朝的水師,透過劫掠閩粵水域支援越南財政,張保仔則倚靠西人俘虜替海盜練習使用火器(Murray, 1987)。到後期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辦學,修習西學的大多是沿海海洋族群,或是南洋華僑(Smith, 2005)。

這些海上非法活動,卻製造了一條涵蓋沿岸各地的產業鏈。轉售賊贓、提供糧水、供海盜消遣的酒館、賭館及妓院,以及探路獲取情報等產業,令沿海貧民亦能從海上貿易中獲益(Anthony, 2003)。雖然清代中葉華南海盜因郭婆帶及張保仔相繼接受招安而瓦解,但華南沿海的地下經濟依然健在。沿海居民曾參與英國人的走私貿易,如怡和等英商將鴉片置於公海上的躉船,讓沿海居民接應(Greenberg, 1969)。
英清戰爭期間,不少沿岸海洋族群都為英軍服務,提供糧水,清廷多次上奏斥之為奸民,可見海洋族群與英人合作是為常態(蔡榮芳2001)。英法聯軍戰爭期間,新安縣士紳發起反英運動,荃灣有一條村卻堅持與香港交易,反過來綁架他們(Munn, 2008)。香港開埠後,與英國人合作的海洋族群,獲香港政府批出土地,獲利後成為了香港首批華人精英。他們包括了新加坡歸僑譚亞才,蜑族的郭亞祥及盧亞貴。郭亞祥後來成為了鐵行船務(P&O)的買辦。盧亞貴為現今蘇杭街一代下市場的大業主,曾一度是香港首富。只是後來下市場大火,令盧最終破產(Carroll 2007, Munn 2008)。
英國開始管治香港後,最終決定在香港行英式普通法。香港成為一個在中國之旁,卻在中國以外的城邦。中國那套靠科舉作上向社會流動的做法並不適用於香港。原先被排拒於科舉以外的海洋族群,卻能靠營商而得到社會地位,有些則接受西方教育,畢業後擔當洋行的買辦。他們取得香港的名利,又會到中國捐官,回港後再以華民代表自居,從而得到政治上的影響力(Carroll, 2007)。於是海洋族群便巧妙地利用中國與英國之間的角力,將香港建設成東亞海洋族群的第一座城邦。
可是海洋族群的連繫多靠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ism)中的利益交換。這些建基於對恩庇者忠心的連繫,卻令海洋族群有人亡政息之虞。他們亦缺乏社會組織的傳統。明鄭建立東寧王國後,連年政爭。華南海盜之間常有跳船之事,海盜聯盟又會因個人恩怨而土崩瓦解。海洋族群缺乏結社能力,令早期政府難尋合作伙伴。講求人際裙帶關係的海洋族群,往往帶來貪污腐敗。海洋族群結社文化之不足,使香港開埠初期陷入難以管治且吏治敗壞之局面(Munn,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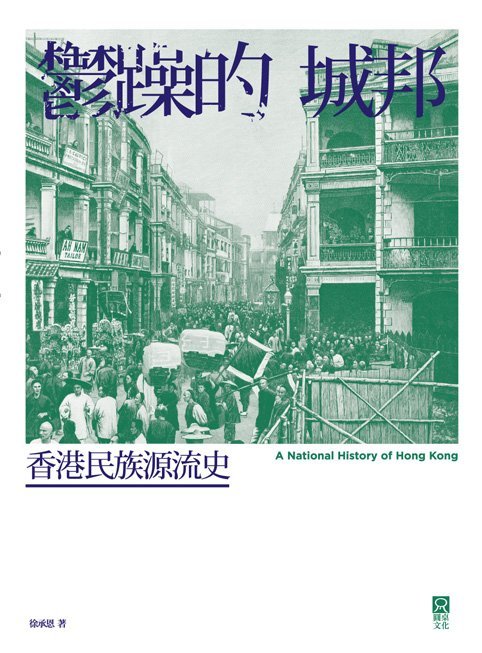
在雨傘革打底下,市面出版了不少著述該段時間本土歷史的書籍,固之然可喜,算是以本土角度記述本土歷史之潮,與以往以大中華角度看香港歷史有所不同。
英國以武力打開中國大門,正式將西方文化、政權植根於這彈丸之地,香港以及香港人所面對的命運,就與中國開始截然不同,香港人的命運共同體,就只有香港人而已。
香港的發展總是充滿矛盾、掙扎、千絲萬縷的,但總是受制於英國與中共的掌控,香港人對於香港的前途甚至沒有話語權。作者於書的最後,只想大家誠實面對自己而已。誠就是真,上天必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