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然中國很早就有華夷之辨的傳統,但嚴格而言並不是現代意義的中國國族主義。韓愈《原道》有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華帝國歷史上的漢族族群意識,歸根究底乃建基於對儒家文明的認同,而不是基於共同經歷而有的命運共同體想像。是以這種漢族族群意識,只見於熟讀儒家經典以備戰科舉的士大夫階層,一般百姓只以宗族及村莊為效忠對象,並無中華民族的概念。嶺南並非儒家文明的核心地區,當中的海洋族群更是與科舉無緣,是以當年嶺南沿海居民支援英國人攻打清軍時,並沒有很沉重的心理負擔(蔡榮芳2001)。
英清戰爭後,嶺南及南洋的華人比以往更能接觸到西方政治思想。他們看到民族主義如何能夠團結各列強之民,凝聚力量走向富強。他們對西方殖民主義亦有更貼身的經歷,在南洋諸國生活的華人亦目睹殖民主義如何令這些國家淪為落後地區。這些經歷使他們覺得中國要有自己的國族主義,方能避免淪為列強的殖民地(Karl 2002)。
中國第一批國族主義者,多為嶺南歸僑或者是曾經留學外國,也有些是香港居民。比如說孫文是曾經留學香港的檀香山歸僑、謝纘泰是澳洲四邑歸僑、楊衢雲自小即在香港生活、黃興是日本留學生、而宋教仁則長期旅居日本。他們都是身處中國之外時產生中國國族主義的觀念。海洋族群、華僑及南方人乃催生中國民族主義的主力,有論者甚至指當時國族主義風潮乃海洋中國的北伐(梁文道2011)。
十九世紀末,美國、澳洲等地均爆發排華風潮,不少四邑籍華僑決定到香港發展。他們接觸過西方文化,有部份已成為基督徒,因而比較能理解西方的自由主義及國族主義思潮,同情革命黨的國族主義,來到香港後積極推動共和革命(Chung 1998)。
1905年,清帝國因美國立法禁止華工移民入境而爆發杯葛美國貨運動。同情革命黨的四邑派商人迅速響應,並將焦點放在清廷軟弱的反應上,藉此騎劫反美運動為反清運動。1908年,日本商船二辰丸因偷運軍火而遭扣押,日本卻反過來要求清廷賠償道歉。事件激起反日情緒,革命黨卻因是該批軍火的潛在買家而陷入矛盾的境地。保守華商亦乘機於香港推動杯葛日貨的運動,為保皇黨增添聲勢。反日運動持續至1909年初,因釀成流血衝突而遭香港政府鎮壓,無疾而終(Tsai 1993)。
香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演變成各種中國國族主義運動的角力場。香港的華人菁英亦參與了中國的政治角力,並慫恿香港政府參與其中。早至1900年,何啟及韋玉聯同港督卜力趁義和團之亂的權力真空,意圖拉攏李鴻章及孫文,推動兩廣獨立,最終此計劃因地緣政治的急速轉變而未能成事。
辛亥革命後,四邑派商人於廣東得勢,獲得廣州革命黨政府的利益輸送。粵幣因廣州政府理財不善而貶值,香港政府禁止粵幣流通,卻令遵從法令拒收粵幣的電車公司遭港人罷搭抗議。香港政府擔心中國共和國族主義損害英國在華利益,亦不願見到四邑派商人坐大。與革命黨關係友好的何啟自此不再獲得信任。香港政府決定在1914年不再延續其立法局議員任期,並建議英國政府封他為爵士,讓他體面地下台。
香港政府亦扶植像何東、劉鑄伯等保守華商與四邑派抗衡。不少華商見四邑派與廣州革命黨政府官商勾結,深感不滿而加入此反革命黨的行列。這派人士當中有好幾位中西混血兒,遂以香港開埠前所屬的新安(寶安)縣為名,自稱為寶安派,另組華人總商會,並支援袁世凱的北京政府與廣州革命黨政府對抗。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人多流亡海外,廣州政府則落入親袁的龍濟光之手。寶安派商人趁機發展廣東如供水、水泥等的基建項目。
但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而鬱鬱而終後,中國四分五裂。孫文得滇桂軍閥支持重返廣州任大元帥,卻無力獨攬大權。1918年,陳炯明組織粵軍反攻廣州助孫文一臂之力,並於11月出任廣東省長。不過,自此廣東政治呈現孫陳相爭之局。

陳炯明主張親商政策,提出要將發展廣東列為優先事項,以「粵人治粵、聯省自治」為政策方針,贏得寶安派的支持。但孫文及其國民黨黨羽卻執意北伐,並得到四邑派的支持。國民黨左派的廖仲愷,則推出一連串不受華商歡迎的政策。
最終兩派於1921年6月決裂,陳炯明向總統府鳴炮示警,孫文先乘軍艦敗走上海,再靠滇桂軍閥之力反攻。翌年1月陳敗走惠州,孫文在廣州站穩陣腳,四邑派亦獲得暫時勝利,藉官方關係參與房地產炒賣,獲利頗豐。
但一連串事件令孫文失去對歐美國家的信心,逐漸倒向蘇聯。香港政府拉攏孫文的嘗試,則因陰差陽錯而失諸交臂。1923年10月,廣州政府已由第三國際鮑羅廷、國民黨左派廖仲愷及蔣中正共同把持,政策全面左傾,組織農民及工人,批判包括寶安派及四邑派在內的華商。華商則成立商團,武裝自衛。
商團代表曾與匯豐銀行及香港政府接觸,計劃走私軍火予商團以抗衡孫文,但事情在1924年8月敗露。商團在廣州發起罷市,武力抗爭,一度令孫文考慮避走韶關。但黃埔軍校得到蘇聯軍援,其師生10月進攻廣州,向商團根據地西關放火。商團事敗後,大批廣東華商逃亡香港,留在廣東的華商亦遭政治迫害。寶安派與四邑派兩敗俱傷,港督司徒拔亦因處理不當,最終遭倫敦撤換(Chung 1998,蔡榮芳 2001)。
1925年5月30日,上海一群工人發起罷工抗議日資僱主虐待員工,卻在公共租界與英國巡捕爆發衝突,多名工人被捕。其餘工人遊行至老閘捕房要求放人,英籍捕頭下令開火鎮壓,釀成十三死四十傷。事件震動全中國,香港工人亦發起罷工聲援。他們的動機既是出於中國國族主義情緒,亦是寄望能透過反殖抗爭促進勞工權益。罷工工人陸續離開香港前往廣州,並獲得左傾的廣州政府資助接濟。
香港的華人菁英以及旅港廣東華商在前一年才被廣州政府鬥得焦頭爛額,好不容易才能於香港休養生息。如今廣州政府又支援省港大罷工,彷彿要這群精英再無立足之地。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精英,則認定事件為廣州政府對香港的侵略。是以,當香港政府徵召他們與罷工工人抗衡時,他們並不只是消極的配合,而是盡心盡力積極參與。香港華人精英在同仇敵慨抵抗外侮的過程中,建立起效忠本土的身份認同,並向香港政府證明了他們對殖民地體系的忠誠(Chan Lau 1990, Carroll 2007)。

省港大罷工初期,香港流失大批勞動力,令百業蕭條,社會人心浮動、治安不靖。何啟生前的友人及合伙人曹善允臨危受命,義務擔任臨時工務處長,善用華商階層的結社網絡,透過各大商會及街坊組織動員未參與罷工的市民。這些組織成立多支自衛團,維持社會秩序,防止罷工搞手搗亂、或以恐嚇手段威逼他人罷工。
除此以外,這些社會組織亦四出尋找義工及希望復工的工人,填補因罷工而出缺的崗位。部份勇敢的華人精英與陳炯明舊部梁永燊將軍合作,成立特務組織工業維持會,一方面暗中調查罷工領袖,另一方面則用武力對付罷工工人。部份未有參與罷工的基層華人,則自告奮勇加入輔助警察及皇家香港軍團,同時自行組織義務消防隊。經各方努力,香港大部份經濟活動到7月逐漸恢復。雖市況未如昔日繁華,至少香港經濟能持續運作下去。華人菁英的本土保衛戰,至此先勝一仗。
香港華人菁英亦發起輿論戰,爭取普羅大眾支持,以抗衡罷工領袖們的論述。他們運用其社會組織動員香港中學生派發傳單、張貼街招,宣傳反對罷工的訊息。學海書樓等前清御史則獲得大筆資助,讓他們制定學校教材,以傳統文化抗衡自五四起的新思潮,強調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華人菁英亦在罷工期間創辦《工商日報》,成為反對罷工的輿論平台。罷工結束後,該報繼續擔當公共領域的角色,讓華人精英討論政治及社會事務。
1925年11月,漢學家出身的金文泰接任港督,決定與廣州政府談判,周壽臣和羅旭龢擔任香港代表,負責北上與廣州政府及工人代表談判。工人代表質疑周羅兩人之代表性,令談判破裂。華人精英鍥而不捨地繼續聯絡蔣介石和汪精衛,雖未能達成協議,但談判氣氛比之前有所改善。
1926年3月,廣州發生企圖劫持蔣中正的中山艦事件。蔣中正及其國民黨右派乘勢發動政變,汪兆銘等國民黨左派以及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失勢。省港大罷工亦因此失去其幕後支持者。到6月蔣中正主導的廣州政府決定北伐,遂決定修補與香港的關係,9月18日單方面宣佈於雙十節結束罷工。香港罷工工人的民族主義熱情遭廣州政府出賣,亦未能爭取到任何本土勞工權益,下場十分悲慘(蔡榮芳 2001)。
省港大罷工發生前,香港政府並不完全信任華人菁英,行政吸納政治的體系中最高的行政局內一直都沒有華人代表。華人精英在省港大罷工期間積極抵抗廣州政府的干預,令香港政府意識到他們對殖民地體系的忠誠。罷工期間負責與廣州方面談判的周壽臣在1926年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勞苦功高的曹善允亦於1929年成為立法局議員。自此香港本土華人精英成為了香港政府主要管治伙伴。
與此同時,華人菁英合作對抗廣州政府的經歷,使他們產生命運共同體的想像。在中國國族主義代表着政治正確的年代,華人精英會辯稱他們是要以更務實的方式愛國,但他們心目中已經視香港為自己的家鄉、為自己首要的效忠對象。他們為了香港,可以與原為母國的中國對着幹,與香港政府的殖民地體系合作無間。精英本土意識自此成形(Carroll 2007)。

這種菁英本土意識,看似是一小撮人的獨特思維,其實際影響卻可以極為深遠。安德森指出作為國族主義先鋒的南美獨立運動,參與者多來自佔人口少數的奴隸主階層。比如說創立大哥倫比亞的玻利維(Simon Bolivar),本身乃委內瑞拉的貴族,家族擁有多座由奴隸開採的礦場。
東南亞諸國的獨立運動領袖,則多為曾加入殖民地體系的文化精英:他們在同一晉升階梯中共同升遷的過程中,產生了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當這些意識透過文化傳播或是制度安排滲透到普羅大眾那邊,便可能催生新一輪的國族主義運動(Anderson 2006)。
香港華人精英的本土意識成形後,亦會透過各種可見的制度及隱藏的習慣,潛移默化香港社會。當社會條件成熟,這種原屬於精英的小眾意識將演化為普及的族群本土意識。中國赤化後,香港與中國的邊界比以往遠為封閉,為本土意識的開花結果提供理想的土壤。
作者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national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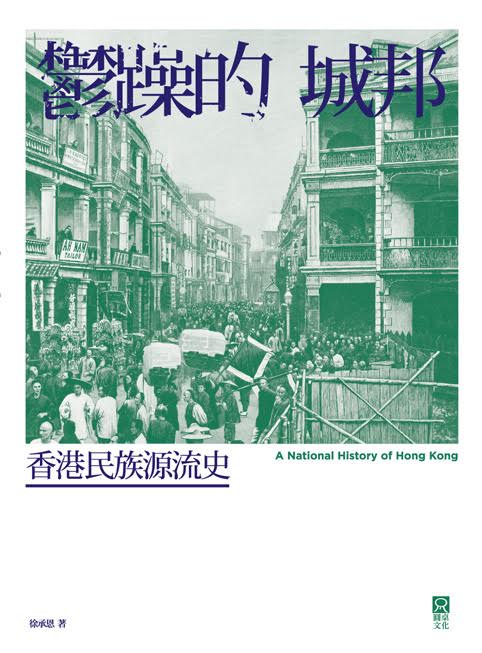
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國際書號:9789881438867
出版社:紅出版 (圓桌文化)
出版社專頁:http://www.red-publish.com/big5/book/2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