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英的故鄉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島嶼,也是唯一同時並存三國領土的島嶼。除了馬來西亞和汶萊,占有島嶼四分之三面積的印尼將它命名為加里曼丹。
加里曼丹島上有被統稱為達雅克族(Dayak)的原住民部落,有早期從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遷來的馬來族,有大航海時代來的華人,有近代因政府移民計畫和礦產資源而來的爪哇人、馬杜拉人(Madura)……有人說,每五位加里曼丹居民,就有一位不是本地人。
但什麼是「本地人」呢?
蘇英描述的加里曼丹,是一座文化地景豐富又帶著濃厚人情味的島嶼。除了以伊斯蘭教信仰為主的馬來人,經過荷蘭殖民的原住民和華人大多信奉天主教,只是多少都融合了過去的習俗。

比如她的母親就是天主教徒,每星期都會帶女孩們去教堂做禮拜,小蘇英在那有著尖塔和彩色壁畫的大屋子裡聽了無數耶穌、使徒和聖人的故事。
雖然如此,但華人過年時家裡一點也都不馬虎。
蘇英記得過年前一個星期開始,就要忙著做各式各樣的餅乾和蛋糕;到了年三十夜,大掃除完,布置就緒,五彩繽紛的糕點山一樣堆滿客廳桌子。因為沒有打蛋器,蘇英光是處理蛋白就要花好幾個小時,「到現在想起來都好累,一點也不喜歡過年。」
除了點心,過年最重要的便是團圓時吃的炒麵。將長長的麵汆燙後,炒得金黃香酥,加入海鮮、蝦子、豬肉、韭菜、豆芽,聞起來就是過年時豐盛的味道。
餅乾、鳳梨酥、千層糕是為了訪客準備,就像齋戒月後華人會參加穆斯林的聚會並收到餽贈一樣,過年時華人的朋友、鄰居也會來家中拜年。
「老師啊、同學啊都會來拜年,然後耶誕節或什麼就換我們去拜年,拿糖果。大家真的都相處得很好……」蘇英看著前方的桌子,好像那些糖果餅乾和色澤誘人的千層糕,還滿滿堆在上頭一樣:「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但國小後很多東西就變了。」

蘇英印象中的轉捩點,是一位重要明星和華人發生衝突不幸身亡。
因為新聞由政府掌控,沒有人能知道明確發生什麼事,激動的群眾開始爆出「中國人滾回中國」之類情緒性言語。騷動不安持續延燒,政府開始禁用中文字,日常生活也不再能說客家話和福建話,連過年都必須偷偷摸摸。張燈結綵舞龍舞獅的盛況固然難以再現,拜訪的客人與笑語也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低沉。
而隨著衝突逐漸激化,對「印尼人」懶散、不懂理財、胸無大志等負面形象的刻劃,與「華人」優越性的塑造,一點一滴在蘇英的生活圈擴散,鋪天蓋地的偏見和誤解使得人與人之間單純的交往益發困難。
「我國中畢業前,印尼文老師還偷偷給我們出功課,讓我們編一本客家話的字典。」蘇英笑著說:「他很好奇,因為他太太是客家人,但是不會說客語。」
蘇英的師母不會說客語,自然不是幾年前衝突的結果。
故事要從四百年前說起。
1619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占下了今天的雅加達,以高牆圍起一座名為巴達維亞的城。從那時起,本來在中國沿海與南洋島嶼間往來經商的華人,就不再只是商人和移民。
沒有政治利害關係,又有悠久商業傳統的華人,成為荷蘭統治者的承包商,負責從中國引進勞工、匠人和荷蘭人需要的貨品,並管理當地村莊的稅收與經濟作物生產。而其中最有權勢的商人,就被任命為「華人甲必丹」(Kapitan Cina)。

十九世紀中葉,荷蘭在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積極將勢力範圍由爪哇往外拓展,新開發的錫礦、菸葉、橡膠園,都需要大量廉價勞工,華人的「大移民」時代就此拉開序幕。
定居印尼數代的「土生」華人以公司形式招來(有時甚至強行拐騙)大量的「新客」華人,而新客華人藉著語言、地域文化的優勢和奮鬥精神,又成為新企業的擁有者。從全國最大的公司到荒廢礦村的小店,印尼華人始終在市場經濟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並且以一種既深根又游離的狀態作為印尼的「他者」存在。
因此,當好不容易走出二戰並爭取到獨立的印尼人民知道原本荷蘭掌控的經濟領域將被華人接管時,長久被殖民的複雜情感與眼下的困頓便引起了一發不可收拾的排華聲浪。
1956 年,印尼商人阿沙阿特(Assaat)帶頭發起一系列攻擊行動,在演說聲明中,他大聲疾呼:「華人是一個排外的族群,無論在文化上、社會上,尤其是在經濟上,他們一概拒絕和他人分享。在經濟領域,他們是如此專權,事實上,他們壟斷了我們的經濟!」
1959 年,針對西爪哇地區頒布的歧視性法令,造成約十萬名華人被迫離開印尼。
1965 年 9 月 30 日,蘇哈托平定了一場流產政變,蘇卡諾(Sukarno)被架空,他親近的印尼共產黨則遭指控參與政變。軍方隨即展開嚴酷掃蕩,造成數十萬人死亡。由於共產黨中有不少華人,因此本已帶著「非我族類」標籤的華人,此後陷入更不友善的處境。
1966 年,所有華校都被關閉,華人只能進入以印尼語授課的學校。1967 年,政府以「妨礙同化」為名,禁止公開慶祝華人的宗教和文化節慶,比如新年和舞龍舞獅。那是蘇英出生前十年。

相對剝削感向來被認為是造成排華的重要因素,但並非所有華人都過得比其他人好,這點蘇英最了解。
「我高中時曾經很看不起爸爸……」
蘇英的父親年輕時被父母逼婚,因此到處流浪不願回家。第一任妻子離開後,他和第二任妻子生下二男一女。但因為生意常常出遠門,結果妻子又離開,留給他一個兒子。為了讓兒子有人照顧,蘇英的母親才被介紹給這個年紀比自己大了兩倍的男人。
「因為公務員會刁難華人,他們始終沒有登記。生意失敗後他就回家待著,也不工作,都是媽媽一個人養我們。」
最早,蘇英的母親開了一家小雜貨店。那時家裡境況還好,全村只有他們家有電視機和電燈。母親向農民收購香蕉,換給他們稻米和油。每次收成後,家中都會煮滿滿一鍋的食物給遠道交貨的農民。橙紅的鮭魚、鮮黃的圓茄和墨綠色的樹薯葉,總是搭著農人亮白亮白的笑容。
然而動盪的大環境也使小生意越來越難維持,母親最後收了店面,不斷隨著商機在鄉村間遷移,而蘇英和姊妹則由外婆一手帶大。外婆愛吃檳榔也愛抽菸,因此小蘇英常常幫著剝檳榔、捲菸葉。
差不多要上國中時,蘇英的母親做了重大決定:她賣掉所有財產,辭退所有幫傭,堅持搬到加里曼丹最大的都市──坤甸(Pontianak),讓小孩受更好的教育。
「但她沒有想到都市的房子和土地竟然這麼貴,錢很快就花光……」
因為心疼母親,本來調皮好動的蘇英便收起性子,天天在家裡幫著做家事,照顧妹妹。對她而言,這些改變唯一的「好處」,就是過去忙碌的母親終於有空在過年親自下廚。
「那個過年,媽媽煮了豬頭花生湯,是用真的豬頭剖半去熬。媽媽一開始不想讓小孩看到,所以只盛湯出來。但我覺得好好喝,好甜,就自己再去廚房裝。結果一打開鍋蓋,看到豬頭在裡面嚇了好大一跳。不過媽媽和我解釋用豬頭比豬腳什麼都甜,我也覺得很好喝,過一下就繼續喝了。」
對蘇英而言,那樣的甜意味著某種和兒時糕點迥然不同的年味:「唯一不變的只有炒麵。爸爸說,吃長長的麵才會長壽,所以每年一定要吃炒麵。」

高中畢業時,蘇英想試試自己的能力,結果考上大學,但沒錢念。她想要工作賺錢,但因為媽媽也在外面工作,她必須留在家裡照顧妹妹。
「那時候心裡真的很埋怨爸爸。媽媽在別的島工作,一個月才回來一次,爸爸根本不知道在哪裡、做什麼。所以我一定要在家。那時候大妹讀國中,小妹讀國小,我每天一大早起來幫她們做早餐,準備點心、衣服,幫小妹綁頭髮,送她上學。回家以後就做家事。
媽媽去工作前,什麼都來不及教我,我必須自己花很多時間努力嘗試,努力學,朋友約我出去我都不敢,更沒有機會交新朋友,覺得非常悶,也很寂寞……」
更糟的是,1997 年由泰國開始延燒的亞洲金融風暴重挫印尼經濟,無數公司與工廠倒閉,外資撤出。半年內,印尼盾貶值 72%,一年後失業人口更高達兩千萬人。
在末日般的低迷和恐慌中,有人開始將矛頭轉向華人,最終釀成 1998 年駭人聽聞的「黑色五月暴動」。官方最保守的統計是「 1250 人在這次動亂中喪生」,而遭到強暴的華裔婦女則不計其數。

暴動最嚴重之處在爪哇的雅加達和蘇門答臘的棉蘭,但蘇英仍能感受到整個社會擾動不安的氛圍。
「我自己其實很害怕,我覺得我沒辦法擔負妹妹的安全,壓力非常大。但為了要兩個妹妹安心又不能表現出來……」第一次,她無比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不屬於這裡,留在這裡沒有希望。
「媽媽老闆的朋友是媒人,她一直很喜歡我,覺得我單純又會顧家。」
1998 年,那位媒人突然出現在蘇英前面,問她願不願意嫁給臺灣人。幾天內,媒人三番兩次地問,最後她實在受不了,便假意答應後躲起來。
「那時候我好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結果隔天就在上班半路被她抓到了。她說都答應人家了,一定要去看看。其實我有很多學姊都嫁來臺灣,也聽了很多故事,可是我很擔心語言不通,所以連臺灣究竟在哪裡也沒想過。沒想到一看發現『咦!他竟然會講客家話!』,而且長得還不差,就覺得好像也可以接受。」
蘇英笑著說:「媒人看我鬆了,就馬上問媽媽在哪裡。我說媽媽在別的島。沒想到她馬上去租快艇。我在快艇上一邊顛一邊想:『糟糕,快艇這麼貴,這樣就不能不答應了……』」
正在工廠的母親被蘇英突如其來地造訪嚇了一跳,但那震驚完全比不上後面得知的消息──她決定嫁到臺灣。於是,蘇英的母親搭上快艇一起回去,籌備幾天,舉行了婚禮。七個月後,蘇英踏上她原先根本不知在何處的島嶼。
美濃的客家庄有阡陌相連的農田、魚塭,休耕的花圃和菸樓,氣候比赤道貫穿的昆甸溫和得多,但又不至於讓在熱帶長大的蘇英感到寒冷。即使不會中文,低矮的磚房和柔軟的家鄉話,還是讓蘇英覺得一切不真的那樣陌生,甚至有些親切。

「我先生的外公那邊是養鱉世家,他來印尼以前也是賣鱉料理。回來後他幫表哥做過水泥,也幫親戚烘過菸葉。媒人說什麼他有兩棟房子,月薪七萬,根本就太誇張……他工作雖然不穩定,可是只要有機會就都肯做。所以我就放心了。」
最終,蘇英和丈夫一起承繼了外祖父的事業。一個鱉池,一間沙屋,一座放冷凍飼料和鱉蛋的小小倉庫。我們站在鱉池邊,看蘇英活靈活現地比畫一隻小鱉的生命歷程:
一顆蛋大概要等四十天才會孵化,小鱉出來後,要先放在旁邊的小水池,不然會被其他大鱉吃掉。等幾個月過去,小鱉稍微長大一些,再放進大池,每天餵牠們各種海魚混成的飼料,維持水質。當一隻鱉養到差不多兩、三歲時,就會在夏夜悄悄爬上沙灘,產下一顆顆珍珠般晶瑩的蛋。這時,她就會教著小孩怎麼撿、怎麼排,才不會把脆弱的蛋碰壞。
「我先生有時忙了一整天,晚上還會特別出去,蹲在那邊和鱉說話。特別溫柔……」蘇英說。
笑容裡,有一種安穩、恬靜,真正在家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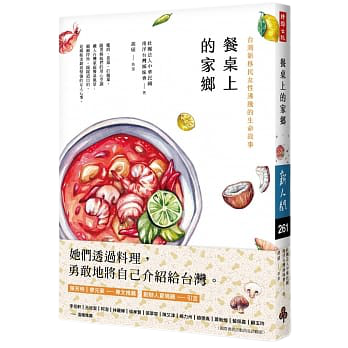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餐桌上的家鄉》
「餐桌上的家鄉」不僅是南洋臺灣姊妹會分享料理的粉絲專頁
透過這本書,陪她們做菜、說話,發現新移民女性的柔軟與堅韌; 她們通過料理,勇敢把自己介紹給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