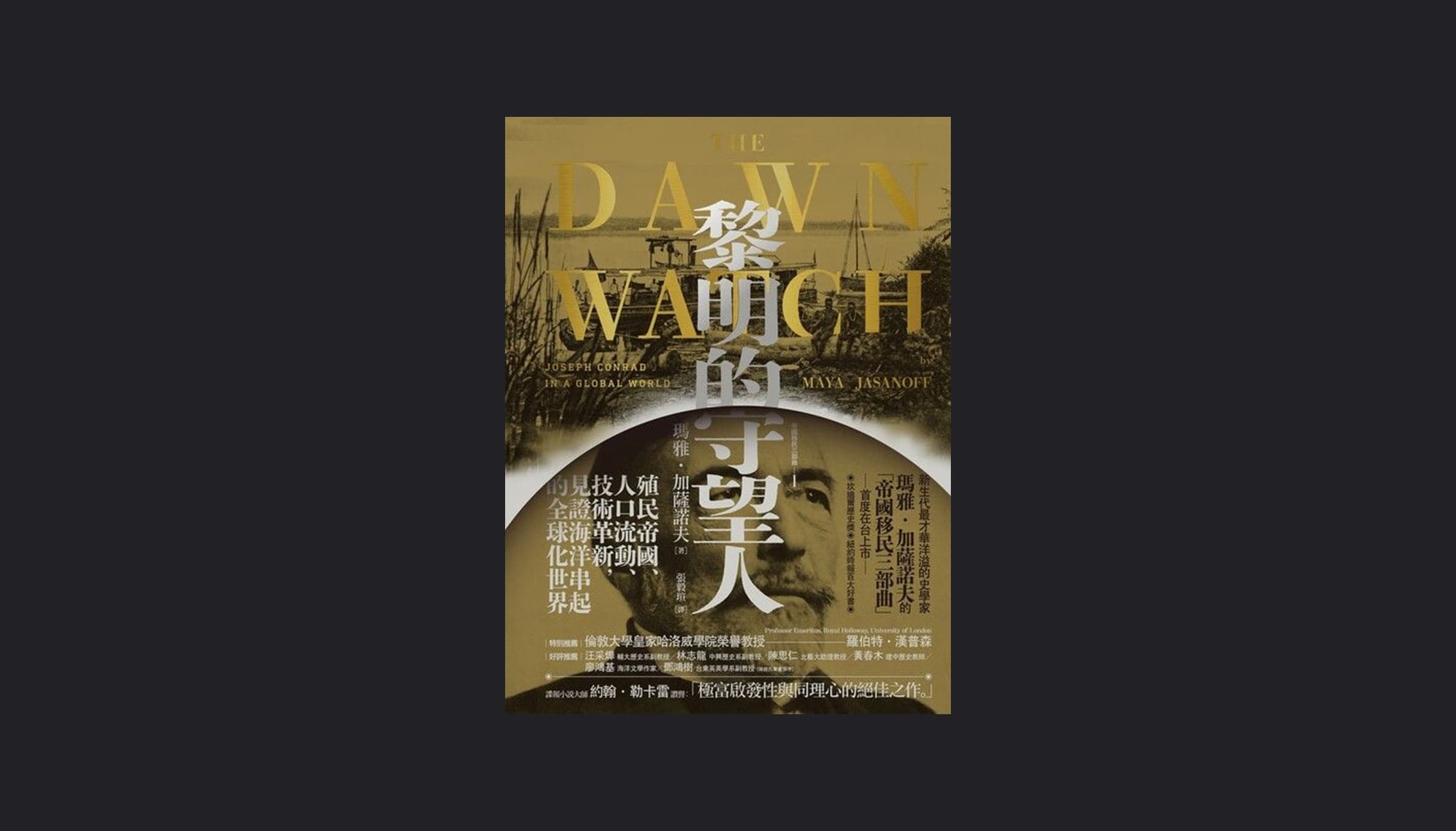今天,我們對約瑟夫.康拉德的認識大概最主要就是《黑暗之心》作者;他以自身的剛果經驗寫出兩部故事,這是其中之一。
1890 年 5 月 6 日,他在布魯塞爾簽下三年合同,預備成為河輪「佛羅里達號」的船長(且有機會參與探索內陸的探險活動)。他在 6 月 12 日抵達剛果波馬港,踏上溯河前往金夏沙的旅途,此時離他從「奧塔哥號」辭去人生第一個船長職已有一年多。他兒時熱中閱讀探險故事,還會在老舊地圖書的空白處仔細追蹤歐洲人在東非大湖區繪製地圖的進度,他這時想必是圓了童年夢想。
馬羅在《黑暗之心》裡講述自己非洲之旅開端的情節,康拉德一共利用他在布魯塞爾與利奧波德國王公司代表會面情況、他沿西非海岸往下航行的經歷,以及他去金夏沙走的陸路(共走了 370 公里路,在 8 月 2 日抵達目的地)等親身經驗來寫成。康拉德不可能預料在剛果會遭遇什麼,但這些遭遇改變了他的一生。後來,他感到自己在此之前只是個「畜生」:在親眼見到利奧波德手下各個公司對當地人的奴役與屠殺之後,他本身與其政治觀點都因此覺醒。

康拉德十六歲離開波蘭,之後以馬賽為家待了四年。期間他為了進入商船水手這一行而以見習身分出海去了三次西印度群島,同時愜意享受法國港口的生活。1878 年他二十一歲,法國船不再讓他上船工作(因為未在俄國服完兵役),於是他開始在英國商船上討生活。
接下來幾十年,他數次出航澳大利亞、印度與東南亞,還以「維達號」大副身分四度往返於新加坡與婆羅洲、蘇拉維西等地無數荷屬東印度小港之間。最後這四趟行船在他後來的作家生涯裡非常重要,提供他頭兩本小說《奧邁耶的癡夢》與《海隅逐客》以及數部短篇故事的寫作材料。在回憶錄《私記》中,他寫到在倫敦租屋居住時,那些他在婆羅洲遇到的人物如何重返他的記憶:奧邁耶、奧邁耶的妻女,「然後是帕塔尼族(Patani)其他的人」。
對康拉德來說,這些吵吵嚷嚷吸引他注意的阿拉伯人、馬來人與海峽殖民地華人,都證明「神秘的同胞之情將世上所有生靈結合在一個希望與恐懼的群體裡」。正是這樣的信念,對「凡人眾生,不管他們生活在何地,住的是房屋或帳棚、是在霧氣籠罩的街道、還是被陰鬱紅樹林黑影遮擋的叢林」顯露的共情,這是康拉德在他第一本書序言裡提出的主張,也是他寫作生涯依循的指引。
瑪雅.加薩諾夫勇敢追循康拉德在剛果走過的路,親身體驗這個比利時殖民所留下的千瘡百孔國家。她正確強調出《黑暗之心》能讓當代讀者一窺權力如何在不同大陸、不同人群間運作,也詳細說明康拉德在非洲的經驗,以及利奧波德的殖民活動實際上如何進行。
《黑暗之心》初版時,向英國讀者揭露那些以「文明教化」為名在剛果實施的暴行,告誡他們不要相信這類霸權干涉背後有任何可取「思想」。利奧波德將一片土地命名為「剛果自由邦」(這命名帶著些許玩世不恭),而比利時卻在此戕害人權;人們常忘記,在 E.D.莫瑞爾開始在報章雜誌對此展開抨擊之前,早幾個月《黑暗之心》就已在《布萊克伍德雜誌》連載。
和康拉德另一部非洲故事〈進步的前哨站〉一樣,《黑暗之心》也寫出帝國主義怎樣在基層運作──以及帝王、政客和記者等人言論所描繪的畫面距離真相是多麼遙遠。
不過,瑪雅.加薩諾夫是透過另一趟全然不同的旅程,從香港越過印度洋航向英國,以洞察康拉德與二十一世紀當代世界的關聯性並加以解釋。這趟旅程同時也賦予本書勾勒的脈動:也就是康拉德在成為職業作家之前,身為水手的他從甲板或艦橋上看見「一個全球各地互相關聯的世界」,亦即我們現在所居的這個世界,「逐漸顯現」。
成為作家後,在他所寫的小說裡,康拉德重訪航海歲月曾去的地方,非洲、印度、模里西斯、東南亞、澳大利亞,還有那些他大概只匆匆一瞥的地方(例如《諾斯楚摩》的南美洲)。此外,他從海上歸來時以倫敦暫時為家,在其他的旅程裡到過日內瓦和法國某些地區,這些也都呈現於他的小說裡。他從未前往《西方眼底》的俄國,但藉由俄國文學來認識俄國,也認得俄國是宰制兒時波蘭的帝國占領勢力。簡言之,如加薩諾夫所言,他是「全球化世界裡的公民」。

然而,康拉德身為波蘭人的部分也實在不可忽視。他雙親對波蘭獨立運動自發的犧牲奉獻是他人生無法磨滅的經驗,這也浮現在他晚年為波蘭請命的政治熱情裡。加薩諾夫巧妙援引柯爾澤尼奧夫斯基家族背景,以及康拉德幼年成長環境中的文學運動、政治奮鬥、警力監控與流刑等歷史脈絡。
康拉德在英國商船工作的歲月裡以倫敦為居所,這又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世界。倫敦就像巴黎,這座城市經歷過大規模改建,拆除市區貧民窟、鋪設新的寬闊幹道。同時,倫敦也像加薩諾夫所形容,是「全世界的『某處』組成的蛛網」中心。更重要的是,她觀察到當時英國以收容政治難民而自豪:沒有限制、不須護照與簽證。
康拉德唯一一本以倫敦為背景的小說《密探》裡大部分角色都是外國人,這點頗值得注意。康拉德寫這部小說的背景是因為寫作不久之前,右派政治人物與報章雜誌進行宣傳活動,反對逃離俄國反猶屠殺的東歐人抵達英國,導致 1905 年的《外國人法》,自此英國移民政策從維護難民轉為維護邊界。
康拉德在英國商船上任職時,是眾多不同國籍船員中的一員,加薩諾夫很有眼光地強調出這件事。當康拉德開始在海上討生活,英國造船業正處於高峰,英國船東控制 70% 世界貿易。但這一切都隨著帆船被輪船淘汰而改變。
正如加薩諾夫所示,水手這一行地位低、薪水又少,而且充滿危險。海岸運煤船「海撈者號」是康拉德在 1878 年學英語的地方,它在 1881 年十月帶著全體船員葬身海底。1883 年,「巴勒斯坦號」甲板發生爆炸,在蘇門答臘外海毀於火災,康拉德用這次經驗來寫短篇小說〈青春〉。
文學界一開始將康拉德定位為異國風情小說作家。當時書評家還陶醉在吉卜林筆下的印度生活故事裡,直接就把康拉德視為同一種帝國主義風格的寫作者,為《奧邁耶的癡夢》裡兼併婆羅洲的行動喝采,完全誤解書中對歐洲殖民者的反英雄式處理。不出所料,在〈青春〉、〈颱風〉(背景在南中國海)和《水仙號上的黑鬼》(內容詳述從孟買到倫敦的航程,途中「水仙號」差點在好望角因暴風雨翻覆)出版後,康拉德的早期聲名又多出一部分:航海小說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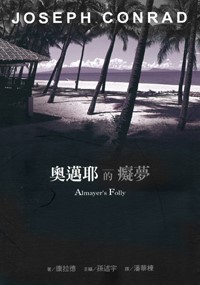
康拉德以南美洲為背景的小說《諾斯楚摩》是他筆下的全球化世界集大成,也是英語小說中討論全球化的傑作。這部小說靈感來自他與羅伯特.康寧安.格雷厄姆的友誼,呈現一個複合式的南美洲國家,該國過去曾長期受西班牙統治,而獨立運動領導人物卻是西班牙殖民者後裔,近年又遭英美兩國以挹注資本於公共建設計畫的方式進行新殖民主義式的侵略。
加薩諾夫引述格雷厄姆在巴拉圭與阿根廷的一些經歷,為這本小說提供一些背景脈絡;她又詳述當時刺激康拉德動筆寫作的大新聞,也就是巴拿馬從哥倫比亞分離出來(以及美國干涉支持新國家成立)的經過。她呈現出一本起初欲探索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如德義統一建國與南美洲爭取獨立的動亂所印證)的小說,最後如何成為一部預言書,預示著我們現在以後見之明所看到的「美國世紀」之降臨。
(本文作者為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榮譽教授、倫敦大學英語研究中心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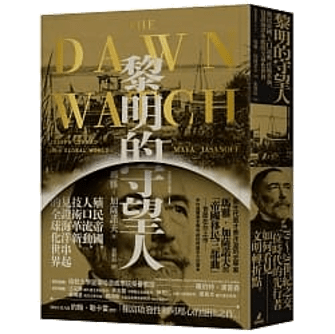
本書作者以歷史學家的獨到見解,帶領讀者見證康拉德的筆下世界,認識全球化如何生成,並形塑我們今日的世界。在作者眼中,康拉德是見證新時代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