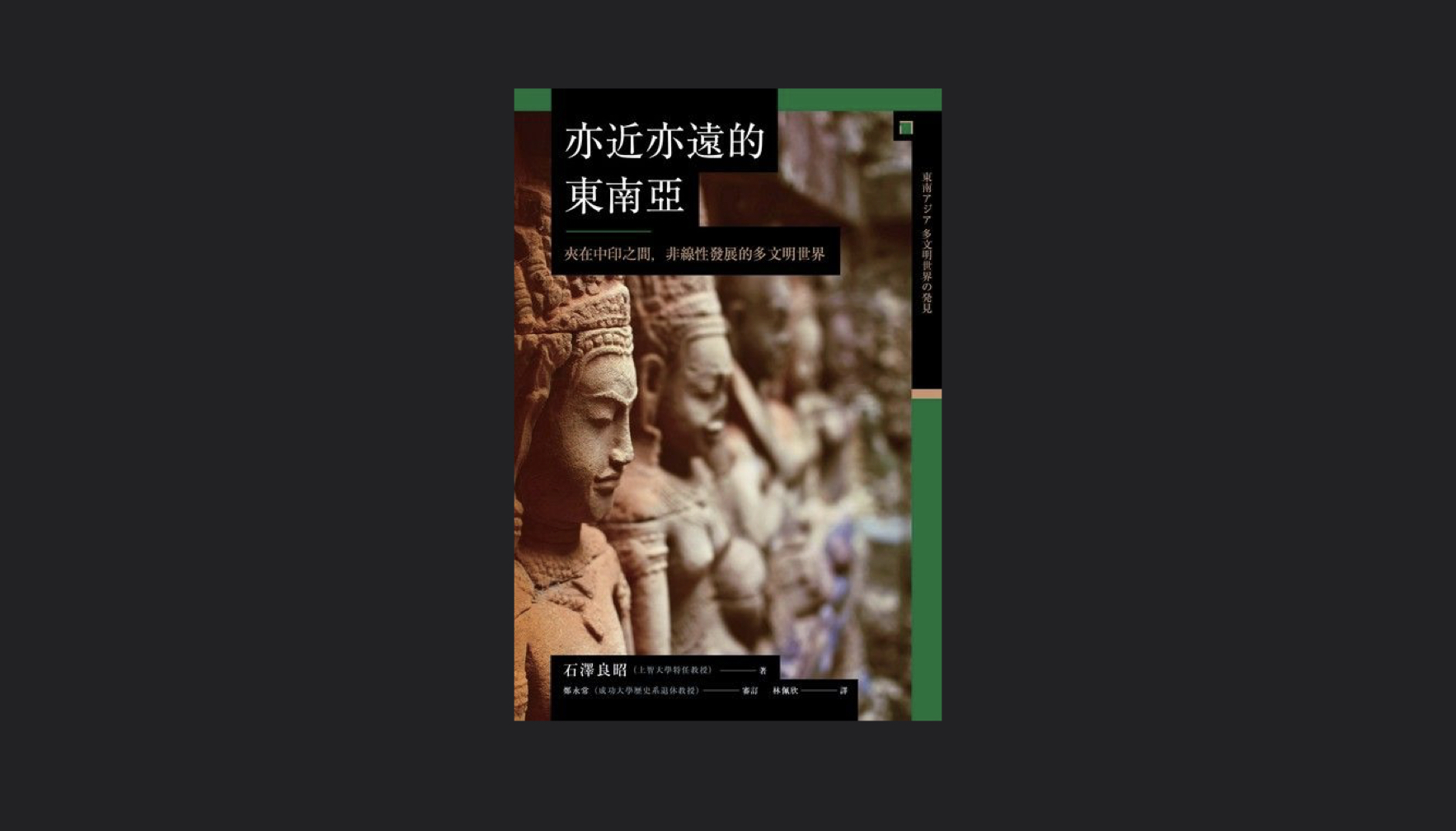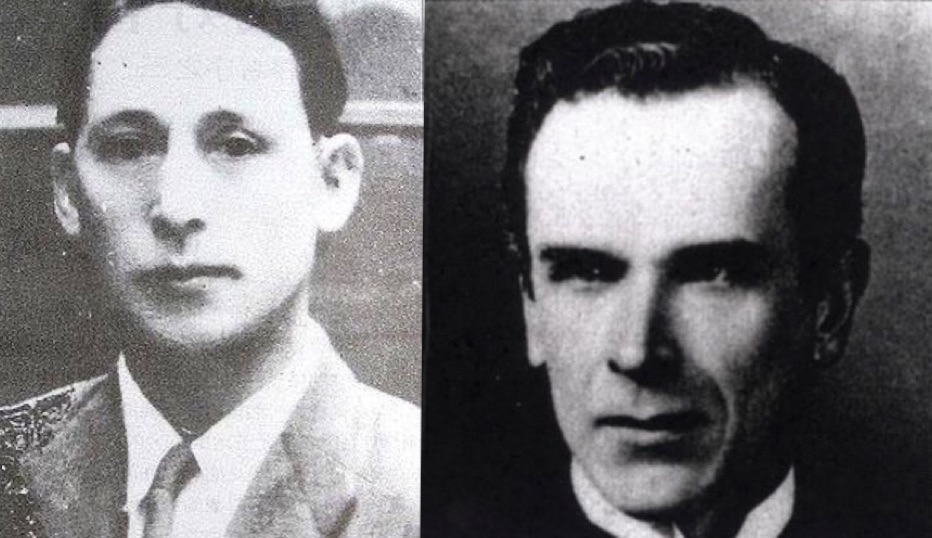「白鰻祭是邵族的傳統祭典,以糯米做成白鰻形狀祭祖,祈求來年好漁獲。」
騎了半個小時的山路,停在一戶人家前。門前的柏油路用幾根木棍圍起來,旁邊一塊板子寫著「祭典舉行中,請勿進入」。
什麼?哪裡?這裡嗎?
我偷偷環顧一下四周。阿嬤、中年婦女屋內屋外來回走動,用我聽不懂的語言協調椅子跟手杖的擺放。屋簷下掛著「日月潭形象商圈伊達邵商店街」的木牌。我的朋友們稀鬆平常的靠著機車滑手機,並沒有要再移動去哪裡的意思。
祖靈籃
過一會兒,有人騎機車把「祖靈籃」載來了。「祖靈籃」是一個有把手的竹籃,裡面的衣服疊到快掉出來。去年來觀禮的 Kaisanan 說,祖靈籃裡面裝的衣服和首飾都是歷代流傳下來的,最下面一層的衣服可能兩百歲不只,比博物館收藏的還要有歷史。

八點多的時候,二十多戶人家的祖靈籃已經差不多到齊,沿著雙黃線排成一列。先生媽(shinshii)也已經穿戴好傳統服飾,頭戴花環,背著手在門口清點祖靈籃,看哪家缺席。大愛電視台攝影機就緒了,只等開始。
三位先生媽把塑膠凳子拉到門口排好,撐著頭就開始唱歌。曲調是重複的,歌詞每句稍有不同。歌詞依序唱出每一家所有祖靈的名字。邵族語言沒有文字,他們怎麼記得?「這就是先生媽的訓練啊,他們遴選祭司的條件可是很嚴格的。」
先生媽不但要通過嚴格訓練,還需要祖靈認可。例如現場三個先生媽裡面最年輕的郭素秋(51歲),就是近兩年多次先生媽入夢,今年登上 lalu 島獲得祖靈認可後,才正式入行。
在現代化的衝擊下,族人漸漸外流,要不是素秋剛好是考古學博士,致力於保存傳統文化,先生媽這個終身義務又責任重大的職位並非人人都願意接手。
以前邵族的照片裡,都是同時有七八個先生媽坐成一排念祖靈的名字,現在只有三個人。一半的人力等於兩倍的辛苦,等到祖靈名字終於唱完,太陽都出來了,口也乾了。
我們一行 8 個年輕人還沒等袁家先生媽舉行完儀式,又轉移陣地到邵族另一邊的石家觀禮。
「在氏族分工下,不同的姓氏有不同的職責,唱歌、領袖等。過去擔任領袖職位的,現在只剩下石家跟袁家兩個。Lhnawanan 被政府音譯成袁家,Lhkatafatu 被譯成石家。」
「日本人要蓋水庫,邵族被強制遷到現在的伊達邵。然後國民政府又土地重劃,邵族的土地又變得更少,甚至演變成兩個頭目住在同一個部落(部落範圍以土地位置為準)的情形。頭目住得越來越近,有時連族人都會搞混不知道要把籃子送到哪裏,祖靈納悶『你是誰!』這樣。」
切白鰻
石家旁邊圍觀的人比較少,但是進度比較快,已經把白鰻堆成的小山端出來。石家頭目現場在門口樹上拔幾朵花,放在白鰻堆上做裝飾。先生媽拿著菜刀砧板,緩步走向白鰻堆。她挑了一條白鰻舉起來,對天大聲唱歌。
唱畢,開始挑選白鰻要切。挑選的時候菜刀還差點滑下桌子,還好及時攔住,令人捏把冷汗。切好後,先生媽用竹盤子端著請在旁邊觀禮的我們吃:「吃平安啦!」味道是單純的糯米,吃不出額外的糖或鹽巴。口感稍硬,嚼久了糯米的甜味才會出來。

切完白鰻後,頭目說先生媽要休息一下,我們要拍照的現在可以進去「管制區」拍照,只要注意不要摸到祖靈籃就好。
湊近看,籃子裡面的首飾花花綠綠,有的還有貝殼、山豬牙。有些衣服因為太舊而失去了本來的顏色,但是仔細看仍然能看到人工織布、手工刺繡的紋理。反觀現代的衣服雖然顏色鮮豔,但是一看就知道是電繡,不知道一百年後還能不能像他的前輩一樣保存得這麼好。

先生媽差不多休息完了,拍照的大夥趕緊竄到木棍管制區外,讓她繼續下一階段的祭祀。頭目跟夫人一起把族人的祖靈籃、手杖、酒粕收到騎樓下,然後再把頭目家族的祖靈籃拿出來,單獨跟一碗小米酒一起祭拜。
因為天氣太熱,大家席地坐在頭目家旁邊的停車場納涼。穿著黑色吊嘎的頭目問:「你們要不要喝水?」大夥開著玩笑:「頭目家的水耶!聖水嗎?」一邊接過頭目給的礦泉水。
祭拜頭目祖靈的歌唱完了,先生媽端一碗酒出來,以指沾酒向天灑,口裡喃喃自語祈福。到這邊為止,祭祀差不多要告一段落。我們好奇另一邊的進度如何,又再騎機車回去。
袁家進度較慢,大約再重複了一次跟石家差不多的流程。站沒一下子,就看到剛剛石家的先生媽騎著電動車駕到。原來是因為袁家的先生媽歲數高了,體力稍微不堪負荷,石家的先生媽名牌都還沒拿下,自己的祭祀一結束就趕來支援。
等到灑酒儀式也結束,邵族族人一一把祖靈籃移動到騎樓,木棍就拿掉了。袁家的頭目把白鰻端進房子裡整理,切下白鰻的尾巴,也是收下族人的敬意,剩餘的部分則連著祖靈籃一起還給族人。
宴客
傳統上,頭目都會在白鰻祭結束的時候宴客,但是袁家前幾天已經請過了,所以我們回頭到石家吃午飯。抵達石家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吃了。看到客人來,吃飯的人熱情的招呼,拿碗筷、介紹桌上的菜。茭白筍、鮭魚、燻雞、刺蔥芋頭梗。
大人小孩都在客廳門廊或坐或站,生面孔們開始互相介紹。這個是西拉雅族、他是道卡斯族,他們都沒有身份。為什麼會沒有身份?
Kaisanan 慢慢的說:「當初政府開放登記原住民身份的時候,只在南投縣政府公告,資訊沒有傳達給居民。沒去登記的人政府沒有紀錄,就不承認他們的後代有身份。」
「最近平埔族群在爭取的正名運動,也是類似的處境。根據政大林修澈教授的估計,真正日本人註記『熟番』的人的後代,2001 年也差不多 15-20 萬人而已,並非 2300 萬人全民皆是平埔混血。漢人創造出『平埔族群都已經漢化到消失』的謊言,是為了掩蓋他們侵佔土地的事實。」
「現在情況也很難改善:既有法定原住民擔心政府承認平埔族群身份之後,資源會分不到、選票被搶走,屢屢跑出來混淆視聽,反而進一步加深族群之間的誤解。」
嚴肅的話題旁,頭目兩歲半的小兒子眼睛很大、睫毛很長,拿著玩具爬來走去。至寶阿嬤傳統服飾還穿著,手牽她心愛的馬爾濟斯靜靜的坐在門口。
傳統上,族人獻白鰻尾巴給頭目時也要附兩瓶酒,現在與時俱進變成罐裝啤酒,Bar Beer 跟海尼根。放在旁邊,想喝酒的人自己拿。我朋友被認識的人問到要不要喝,都以騎機車為由推辭掉了。我沒有被問。一直到吃完飯,也沒有看到誰喝醉。
Aitu 轉頭問我:「跟你一起來的女生呢?」我說:「剛剛她跟頭目的兒子說話,說著說著就被帶進裡面聊天了。我剛剛跟去看了一下,在介紹玩具呢。」我自己敘述起來也覺得蠻神奇的 — — 照原住民的歷史,我跟 Daphne 都是曾經迫害原住民的漢人呢。結果小孩子喜歡她,聊得投緣也就沒有什麼漢人不漢人的了。
飯後雨下得太久,我們就待在門廊聊天,一不注意她進去玩也已經一個小時多。我有點擔心又去看,只見她跟小孩子和樂融融的被玩具堆包圍,坐在軟墊上一起看卡通。
等到雨勢轉小,我們就暫別石家頭目,往下一站去了。
後記
因為我皮膚黑,朋友一直鼓勵我去查自己有沒有原住民血統。出於好奇,我還當真跑去戶政事務所查。承辦員很年輕,對這個業務似乎很不熟,在電腦前點來點去幾十分鐘都沒結果。他旁邊的男同事關心他,小聲的問:「她要辦什麼?」「她要查自己有沒有『原住民身份』(強調)。」男同事脖子伸長了,像是在說「怎麼會有人要查這個?」女承辦員笑了笑,像是回答「我也不知道,我也覺得很傻眼。」
那個無聲的肢體動作,坐在櫃台前的我看在眼裡。我並不責備他們怎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卻引發我省思是什麼樣的觀念會讓他們有這樣的反應。
然後我想起了主流文化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未開化的、貧窮的、教育程度低落的......。然後我想起我的原住民朋友,他們說起族群問題頭頭是道,就連我自己想要重述,都沒辦法同等清楚;他們有的國際論壇跑透透,有的勤上節目、做直播,有的創立組織、帶領文史工作坊。
比起庸庸碌碌生活的人,我更崇拜他們。
在那個櫃檯前,我感到淡淡的哀傷。
出戶政事務所的時候,剛好在下大雨。那天我們離開石家,雨一直沒有停,最後只好冒雨騎車,到家的時候褲子都濕了。朋友媽媽出來迎接,笑著說「我們小時候都是在這種雨跑回家的啦!」然後拿衣服借我換。
我撐開傘在雨中行走,褲腳仍然一點一點的被浸濕了。
延伸閱讀:
- 〈跳舞唱歌小米酒喝到飽?快拋開你對「豐年祭」的誤會!關於部落年祭你看不到的那一面〉
- 〈不要財團式的觀光!還邵族土地!〉
- 為什麼會有原住民「沒有身份」?〈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不是結束,而是另一波平埔族群復振運動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