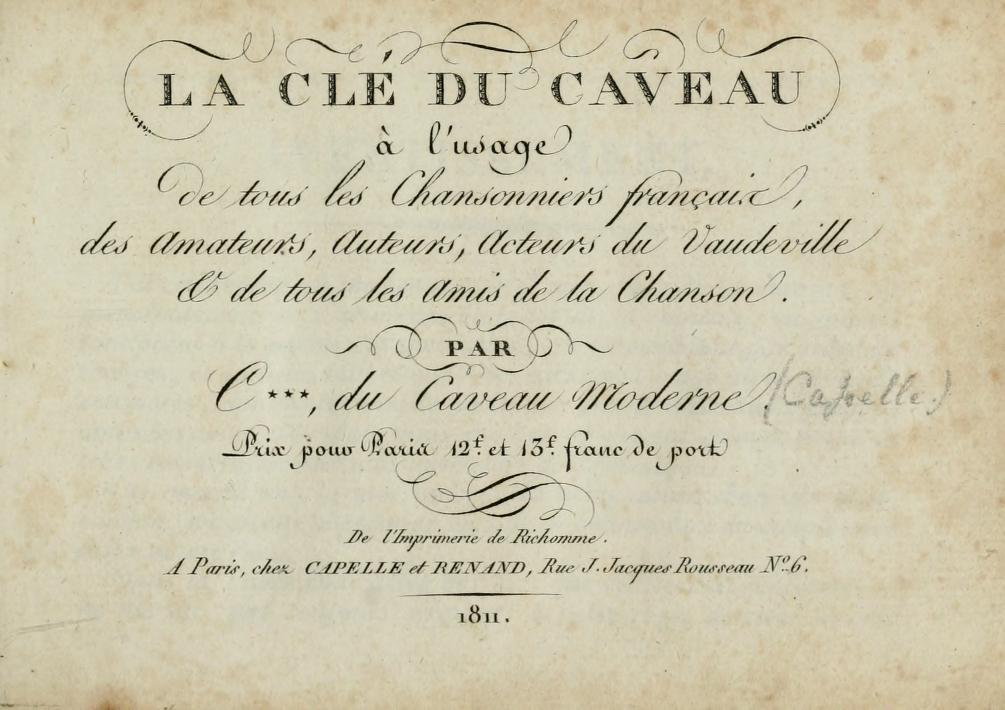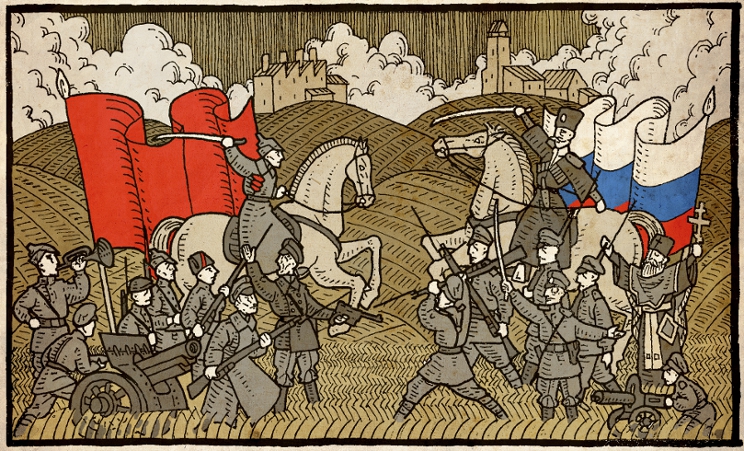巴黎人經常把時事寫成歌詞,搭配最受歡迎的曲調,如「馬伯克從軍去」(Malbrouck s'en a-t-en guerre)(這首歌在美國變成了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在英國則是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歌曲是幫助記憶的工具,在文盲占多數的社會裡,歌曲是傳遞訊息最有效的方式。比起今天美國的廣告歌曲,十八世紀巴黎的歌曲傳遞訊息的效果可能更好。巴黎各式各樣的人物,從見多識廣的沙龍名人,到最普通的學徒,都共享同一種曲調。只要有點小聰明的人,都能即興創作一兩個對句,或是填詞進法國民謠那種八個音節的曲調,還使用互韻的小技巧等,這些旋律都傳進眾人的腦袋裡。如同馬西爾(Louis-Sébastien Mercier)所說的「沒有一個聚會不是充斥著被無禮民眾改編過的『雜耍曲(vaudeville)』」[28]
有一些歌曲源自宮廷,但他們會傳入平常人家,再由平民傳唱回宮廷裡。工藝家們在工作的時候高唱自創的歌詞,時機來的時候,甚至會在舊曲調上面加入新的小節。
伐瓦(Charles Simon Favart)是該世紀最偉大的歌詞作者,在他還是小男孩的時候,就會使用最流行的旋律,一邊唱著他新填好的歌詞,一邊跟著節奏,在父親的麵包店裡揉麵團。他和他的朋友(包括Charles Collé, Pierre Gallet, Alexis Piron, Charles-François Panard, Jean-Josephh Vadé, Toussaint-Gaspard Taconnet, Nicolas Fromaget, Christophe-Barthélemy Fagan, Gabriel Charles Lattaignant, François-Augustin Paradis de Moncrif)一個比一個更會即興創作粗俗的民謠、和飲酒歌,先是在佳列(Gallet)雜貨店,後來又唱到沙弗(Caveau)咖啡館。
他們的歌曲迴盪在小酒館和街頭巷尾,又當時最流行的戲院找到了出路──從聖傑曼博覽會(Foire Saint-Germain)開始,沿著大道上的各種歌舞雜耍表演,最後進到了法國的喜劇劇院(Opéra Comique)。至於庶民階層,則有衣衫襤褸的街頭歌手,拉著提琴和手風琴,在巴黎的新橋和奧古斯丁碼頭,或其他有獨特意義的地方演唱著。
歌聲充滿了整個巴黎。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整個法國可以被形容是「被歌曲給調過音的專制君主國。」(an absolute monarchy tempered by songs)[29]
在這樣的環境裡,一首朗朗上口的歌可以如野火燎原般散播,而且在傳唱的同時不斷滋長。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口語傳遞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加入新的段落,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加入在這個新詞舊曲、移花接木的遊戲裡。新的歌詞被抄寫在小紙片上,在咖啡館中交換,就像是詩和故事透過小報(nouvellistes)散布開來一樣。
當警察巴士底監獄對囚犯搜身的時候,他們沒收了相當龐大的資料──這一箱一箱的資料至今仍然可以在阿森納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找到。小小的紙片上,佈滿手抄內容,以勝利之姿在人們手中傳來傳去,直到某個關鍵時刻,警察拿著搜索票,發出命令「掏空你的口袋」。[30]
這裡有個典型的例子,在一張紙片上頭,抄寫著一首歌的最後一節歌詞:「那個大混蛋臭婊子」(Qu'une bâtarde de catin)──這是所有攻擊龐巴度夫人、國王和皇室的流行歌裡最紅的一首。當梅爾伯特(Pidansat de Mairobert)在巴士底監獄被審問時,警方就從他背心的左邊口袋裡,搜出來這樣的紙片。[31]
梅爾伯特以替人寫作維生,根據警方的資料,他「住在科德利埃街上,洗衣婦那棟房子的三樓」。他「沒什麼錢,只能依賴文采勉強度日。」[32]不過,他時常出入杜博蕾夫人沙龍的優雅聚會,也常與一些屬於皇家成員的歌曲收藏家為伍。
他的同伴中最了不起的是莫赫帕(Maurepas)伯爵,他是海軍大臣,也管理王宮內廷事務,可說是凡爾賽宮裡最有權力的男人之一。在路易十五時代,莫赫帕可說是皇室政權的化身。他機智風趣、狡猾謹慎又不擇手段,他老謀深算,但卻表現的開朗樂觀,讓國王很喜歡和他親近。他也經常討好路易十五,找來最新的歌曲取悅國王,甚至一些嘲諷莫赫帕他自己的歌也在其中。當然,在這些歌曲中也不乏揶揄他政治對手的曲子。[33]

不過,這可是個危險的遊戲,弄巧成拙可就糟了。1749年4月29日,國王把莫赫帕伯爵解職,因為一張搜索票,就把他流放。當時的人認為,莫赫帕的垮台是凡爾賽宮中權力遊戲的精采變局。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大家都在問。
從信件與日記的證據來看,答案無庸置疑:既不是政治衝突、也不是理念上的對立,更不是關於某個政策、原則或是金援的問題……問題在於歌曲。特別由於一首歌,它是以「當危險變得親切」( Quand le péril est agréable)的曲調編成的,歌詞如下[34]:
Par vos façons nobles et franches,
Iris, vous enchantez nos coeurs;
Sur nos pas vous semez des fleurs.
Mais ce sont des fleurs blanches.
對現代的讀者來說,全篇歌詞都相當晦澀難明,若僅按字面翻譯,整首歌聽起來像是一個天真的少年想對女人獻殷勤:
因你高貴而隨意的姿態,
鴛尾花啊,你迷惑了我們的心。
在我們的路上,你灑滿鮮花,
只不過是白花點點。
然而,對於凡爾賽宮的內部人士來說,這首歌的意義再明顯不過了。就算是皇宮內最愛開低俗玩笑的人也會同意,這首歌顯示當時的流行歌曲潮流,已經遠遠跨越了可接受的範圍。
這首歌將龐巴度夫人比為鴛尾花(有些版本用龐巴度夫人還是女婢時的名字,稱呼她為「小魚」),內容則是暗示一場在國王私人寢宮內的親暱晚宴。在這裡路易所發生的事應該是最高機密,沒有任何八卦可以洩漏出去。
這個餐會由四人組成,包括國王、龐巴度夫人、莫赫帕,還有龐巴度夫人的堂姊亞斯達夫人(Mme. d'Estrades)。龐巴度夫人抱著一束白色風信子花前來參加,然後將花朵一一分送給三個賓客:也就是歌詞裡提到的白花。
不過,「白花點點」(fleurs blanches)同時也意味著性病,是某種月經體液的模樣。[35]與會的三人當中,只有莫赫帕能夠這個事件寫成歌詞,並從皇宮偷偷洩漏出去。不管他是否真的創作了這首歌,私人寢宮內的熊熊怒火已被點燃,他也因此被奪走權力,驅逐出凡爾賽宮。
當然,事實並非人們說的這麼簡單。莫赫帕有不少敵人,特別是他在政壇上的對手阿任森(Argenson)伯爵,他是國防大臣,也是龐巴度夫人的盟友。龐巴度夫人的身分是國王首席情婦(maîtresse en titre),這個頭銜就皇室的正式規格來說,只是個半官方的位子,更不能保證她不被八卦流言給擊倒。

這場由莫赫帕所策劃,並利用歌曲形式發動的攻擊,也許會讓國王決定與龐巴度夫人斷絕關係,以贏回民眾的心。至少有某些巴黎人是這麼想的,他們說,白花之歌只是滔滔傳言中的一部分。在1749年的前半年,敵視皇室的各種詞曲早已在巴黎街頭奔流不息。[36]
這一波音樂潮水並未因莫赫帕的倒台而靜止。有些觀察家認為,這也許是因為莫赫帕的黨羽,為了證明莫赫帕不該為這件事情負責,而在他被流放之後,刻意加強歌曲的聲勢。
不過,無論皇宮內的鬥爭走向何方,巴黎市的歌聲都讓政府非常頭疼。在國王支持下,阿任森組織了一個查禁歌曲的計畫。就在他發現巴黎人又在編寫新歌時,他立刻開始採取行動。這首歌的第一句歌詞是「怪獸和他的黑色憤怒」(Monstre dont la noire furie),怪獸指的就是路易十五。而一項新的任務指令,從凡爾賽宮的行政廳傳到巴黎市的警察總部:「找出寫了這句歌詞的作者」。
這個命令隨著指揮鏈,從警察總長、巡邏警官到間諜,層層傳遞下去。沒過多久,警官何梅理(Joseph d'Hémery)就收到一位便衣探員傳來的紙條,上頭寫著:「我知道有一個人的書房裡有那句詆毀國王的歌詞,幾天前那人才說了認同歌詞的話。你要的話,我可以告訴你他的名字。」[37]
就這麼幾句話,沒有署名,一張破破爛爛的紙條,就讓這個間諜賺進12金,這筆錢大約是一個低技術勞工一整年的薪資。這張紙條也挑起了一連串驚人的搜捕行動,對象包括了詩作與詩人,進而累積成我所見過最豐富的一系列文學偵查檔案。跟著警方搜查詩作的腳步,我試著重建了一個網絡圖,來展示訊息如何穿梭在十八世紀巴黎市的口語傳播系統中。[38]
在一連串祕密行動之後,警方逮捕了一名持有一份手寫稿的人,稿子上面寫著那句歌詞。他是位醫學院的學生,名叫做柏尼(François Bonis)。根據他在巴士底監獄的審訊,他說他從一名神父愛德華(Jean Edouard)那裏聽來的;愛德華也被逮捕,他在自白中表示,他是從另外一位神父蒙田(Inguimber de Montange)那裏來的;蒙田被逮捕之後,供出了第三位神父杜嘉(Alexis Dujast);然後杜嘉也被逮捕,說他從一名法學院學生哈勒(Jacques Marie Hallaire)那裡得來的;這人又被逮捕,並說他是從公證單位的職員盧耶(Denis Louis Jouet)那裡得來的,而他接著被捕……
這條線索追查下去,源源不絕,線索的範圍越擴越大,在警察決定放棄追查源頭時,已經逮捕了14個人。每一次的追捕,就產生一宗檔案,每一宗檔案又挾帶了關於通訊模式的新證據。完整的模式可以參見這個程序圖。
乍看之下,案情是直線發展的,產生的環境看來也頗為單一。這句歌詞(圖片的一號詩作)一開始是在學生、神父、律師、公務員、職員當中流傳,他們都與彼此為友,而且都很年輕──大約是16到31歲左右,大部分是20歲出頭。歌詞本身也釋放出相應的氣息,至少對阿任森伯爵來說是如此。他曾把一份歌詞抄本退回去給總長,並在其上附註說明,他形容歌詞「實在臭名昭彰,對我、對你來講,簡直像是聞到巴黎拉丁區裡那些賣弄學問的爛臭味。」[39]

不過這個程序圖,隨著審訊的開展而越顯複雜,碰到哈勒,也就是從圖片上面數來的第五個人的時候,詩作來源的路線分岔了。哈勒從修道院院長居亞爾(Guyard)那裡獲得三份詩作,居亞爾的三首詩是從三個不同的來源獲得的,而他們又是各有各的來源管道,以此類推。最後警方發現,他們在追緝的,總共有六首詩與歌,一首比一首更有煽動性(至少對當局來說是如此),而每一首的散播模式也不盡相同。
結果,有14位歌曲的散播者被丟進巴士底監獄中,這次行動的檔案也因此被稱為「十四人案件」。但是警方怎麼樣也找不到歌詞的原作者。事實上,也許根本就沒有這麼「一位作者」的存在,當然不是因為羅蘭巴特或傅柯告訴我們「作者已死」,而是因為人們隨心所欲的增減詩節,代換詞彙。
這是一項共同創作;第一首詩詞,早就被許許多多其他的創作覆蓋、穿插,最後綜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詩詞電流(poetic impulses)的場域,從一個傳輸地點跳躍到下一個,讓空氣中充滿了各種流言蜚語(mauvais propos),充滿煽動叛亂的雜音,其中卻仍壓著韻。
巴士底嫌犯的訊審記錄,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圖像,讓我們看見詩歌得以散播的背景,和他們散播的模式。每傳到一個地方,詩句的內容都再被討論一次。柏尼表示他在濟貧醫院(Hôtel-Dieu)抄了第一首詩,當時他的一位朋友正和神父熱烈地高談闊論。「他們談話的內容轉向小報裡的新聞;那名神父說,『能寫出這麼毒舌的詩句罵國王,這人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然後他拿出一首攻擊國王的詩來。」[40]
哈勒聲稱在父親家裡和幾個朋友晚餐的時候,抄下了這首詩。他的父親是聖德尼(Saint-Denis)街上的一名絲布商人。蒙田在大學的餐廳裡,聽到有人在閒聊的時候大聲的念詩,他就把詩句抄了下來。
希貢聶(Pierre Sigorgne)是杜波利(Du Plessis)學院的教授,他讀了兩首詩給學生,讓他們抄下:這可是在巴黎的大學發生的政治聽寫(political dictée)啊!
希貢聶背下這些詩,其中一首長達84句歌詞。十八世紀的巴黎,記憶的藝術依然蓬勃發展著。而在許多例子中,人們透過最厲害的增強記憶工具來幫助記憶,也就是音樂。有些詩詞的創作,是為了符合最流行的曲調的韻律。這些詩詞透過歌唱的方式,到處流傳,伴隨著從皇宮傳出來的幾首歌,以及前述那引發了一連串調查的歌曲,
不管是歌唱或是背誦,詩文通常被抄寫在一些零碎的紙片上,在人們的口袋裡帶來帶去,並且可以拿來和其他的詩文交換。歌詞的內容很快地進入小報的世界,而且被印刷發行。在《路易十五的私人生活》(Vie privée de Louis XV)這本暢銷書裡,收錄了兩首最長的詩「法國不幸的命運」(Quel est le triste sort des malheureux Français)、以及「人民啊,曾經如此驕傲,如今竟卑躬屈膝」(Peuple, jadis si fier, aujourd'hui si servile)。
《路易十五的私人生活》是攻擊當政者的歷史書寫,也成了1780年代的暢銷書。書中觀察1749年盛行的歌曲、詩詞,它這樣寫著:
「在這個讓人羞恥的時代,一般大眾對為政者和情婦的嘲弄毫不保留,而人們的不齒將持續到任期的結束......這些輕蔑的言論一開始出現在諷刺詩中,是因為人們對愛德華王子遭受的待遇感到憤怒。(愛德華王子[Charles Edward Stuart],又稱為Bonnie Prince Charlie,這位有意於競逐大位的年輕人在1748年12月10日在巴黎被捕,並根據英國與法國簽訂的第二亞琛合約[Aix-la-Chapelle],被流放在外。)
下面這段文字,比較了路易十五和愛德華王子光榮的流亡:
Il est roi dans les fers; gu'êtes-vous sur le trône?
他是深陷囹圄的國王;為何你還能安坐在寶座之上?
接著,是一段對全國的呼籲:
Peuple, jadis si fier, aujourd'hui si servile
Des princes malheureux vous n'êtes plus l'asile!
法國人啊,你曾經如此驕傲,如今卻卑躬屈膝
不要再為那些不快樂的權貴提供庇護了!
民眾如此渴望取得這些資訊、牢牢在心、並交換訊息,在在證明了讀者對於詩人所抒發的情感,確實有所共鳴。不過龐巴度夫人夫人也不是好惹的......她採取了一個驚人的舉訂,下令逮捕所有的作者、街邊兜售的小販、和所有散播小本子的人。沒多久,這些人就塞滿了巴士底監獄。」[41]

簡言之,消息傳播的過程在各種場景裡,透過不同的形式展開。它總是經過討論與社群的再創造,而不只是單線式的擴散,受聽者也不是被動的。這是在不同的團體之間吸納與重塑資訊的過程,也就是說,這是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或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的共同創作。
如果你忍受我賣弄一下術語,這其實是一個「多媒體反饋系統」(multi-media feedback system)。這聽起來蠻流行的。但我只是想要提醒你,在這種研究當中,理論問題還是至關重要的;而我援引的是Eliu Katz 和 Gabriel Tarde發展出的傳播社會學理論,而不是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時髦理論。[42]
講回到唱歌的媒介,在「十四人案」當中最熱烈流傳的一首歌,就是「那個大混蛋臭婊子」,這首歌是巴黎當時最受歡迎歌謠的典型。整首曲很簡單,只要是八個音節的句子就能搭配進曲調裡,例如這句:「當情人和我做愛時」(Quand mon amant me fait la cour)。有些資料會用這句替換「我該不該念悔罪經?」( Dirai-je mon Confiteor),第一句裡的「臭婊子」(catin)指的正是龐巴度夫人。
而朗朗上口的副歌是這樣的「啊是他!啊是他!一無是處的大蠢蛋」 (Ah! le voilà, ah! le voici/ Celui qui n'en a nul souci),指著法王路易的鼻子,罵他的無憂無慮,罵他的愚蠢。第一節歌詞是這樣的[43]:
Qu'une bâtarde de catin
A la cour se voie avancée,
Que dans l'amour et dans le vin,
Louis cherche une gloire aisée,
Ah! le voilà, ah! le voici
Celui qui n'en a nul souci.
那個大混蛋臭婊子,
法國皇宮佔盡風頭,
情慾、愛戀和紅酒,
路易只求安逸享受,
啊是他!啊是他!
啥也不管的大蠢蛋。
每一節歌詞都諷刺一個公眾人物,在龐巴度夫人之後諷刺國王,一路往下唱,大臣、將軍、主教、朝臣……。每一個人不是無能,就是腐敗,而每一節之後都會重新強調歌曲的主題:那個本該對人民福祉負責的國王,現在卻耽溺於飲酒與性愛。整個國家正走向窮途末路,路易卻「啥也不管」。
雖然我不能證明,但是我覺得這種歌曲就像是童謠一樣──那種一個人站在圓圈的中間,其他孩子牽手圍著他,一邊跳,一邊數數兒地唱「農夫在山谷裡」(the farmer in the dell)或是「孤零零的起司」(the cheese stands alond)──不過這裡完全是為了嘲弄,嘲笑國王那個超級大笨蛋。
整首歌囊括1748年到1750年之間的重大事件或政治議題,詩韻非常簡單,因此,當新的事件發生,新的嘲諷對象可以輕易地被加入整首歌裡。這就是當時的壯抗。若是你把所有現存的歌曲版本擺在一塊兒比較,很容易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現象。
我從各種零散的手稿裡,找出了九種版本的歌曲。歌詞從6行詩到23行詩都有,較為晚期的歌詞,提及比較後來發生的事件,例如,1750年春天,黎塞留公爵勾引稅款包辦人波普里尼(A.-J.-J. Le Riche de La Popelinière) 的妻子,搞的眾所週知、惡名在外。
除此之外,如果你比較同一歌詞的不同的版本,還會發現字句上的差異。當歌曲從一位歌手傳到另一位歌手時,內容就產生了些許變動,這可視為是口傳過程中留下的痕跡。
巴黎人或許不是古老史詩的吟唱者(不像是洛德教授[Albert Lord]研究的那些賽爾維亞人[Serbs]),不過他們肯定是新聞的傳唱者。[44]「那個大混蛋臭婊子」的內容承載了許多的新聞和評論,簡直就是一份「被唱出來的新聞報紙」。
但這首歌不該被獨立討論,因為他只是無數詩歌中的一首,這些歌曲遍佈巴黎各個角落,內容涵蓋了巴黎人感興趣的各種話題。要得知歌曲的總數是不可能的任務,不過,如果仔細檢驗現存所有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理解。
從這張圖,可以看到紙片上面寫著包括了好幾節「那個大混蛋臭婊子」的詩歌歌詞,這是從居亞爾(Christophe Guyard)的口袋裡拿出來的。他是「十四人案」當中的其中一人,而這張紙片是他在巴士底監獄被搜查時,搜出來的資料。
前面提過,還有另一張類似的紙片,上頭也寫著「那個大混蛋臭婊子」的歌詞,但它是警察從梅爾伯特的口袋裡沒收的。梅爾伯特並非「十四人案」中的一人,所以他非常有可能是從另一群社交網路中獲得這首歌的。
還有另外七份抄本,藏在其他圖書館中,他們可能也來自其他的網絡。簡言之,這些歌曲從不同的管道散佈開來,而這十四人的社交網只不過是龐大網絡當中的一個小角落而已。

到底有多龐大呢?讓我們試著想想看另一種證據:摘錄集(collections)。
不少巴黎人從咖啡廳或花園等公共場合取得寫著歌詞的紙片,然後保留在自己的公寓裡。當警方搜索梅爾伯特的房間時,他們就查獲68份類似這樣的摘錄集──從歌曲、詩集、隨手抄寫的各種文本。更富有的蒐集者,則可以派他們的秘書,將資料抄寫成井井有條的條目,或被稱為「歌本」(chansonniers)。最有名的一本叫做「莫赫帕歌本」(Chansonniers Maurepas),其中搜羅了莫赫帕收集的資料,數量高達35冊。[45]
透過研究這個歌本,還有其他七本同樣來自十八世紀中期的歌本,我大概可以猜到當時大約有多少首歌存在過,又有哪些歌是當時最流行的。巴黎市立歷史圖書館(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一本十二冊的摘錄集,涵蓋的資料可說最為豐富。它名為《歷史上的邪惡作品》(Oeuvres diaboliqu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temps),其中收錄有641首歌曲和詩詞,是來自1745年到1751年之間;還有264首詞曲,則是認為是來自從1748年底到1751年年初。[46]
顯然,「十四人案」當中交換的六首歌曲,不過是龐大曲目當中的一小部分。不過,他們在這些歌本中處處可見,伴隨著同一個主題的許多其他歌曲。「那個大混蛋臭婊子」在不同歌本中出現高達8次之多,可以說是十八世紀中期,最能代表巴黎人的主題曲。
最後一種檔案,則給我們一種機會,能夠重新聽見巴黎人所聽見的聲音。當然,這些聲音早在250年前,就消失在隨著空氣之中,不可能在今天原音重現。但是,有一系列的音樂「解碼書」(keys)仍然保留了「歌本」當中的音樂曲調。例如,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沙弗之鑰》(La clef du Caveau)就是這樣一個例子。[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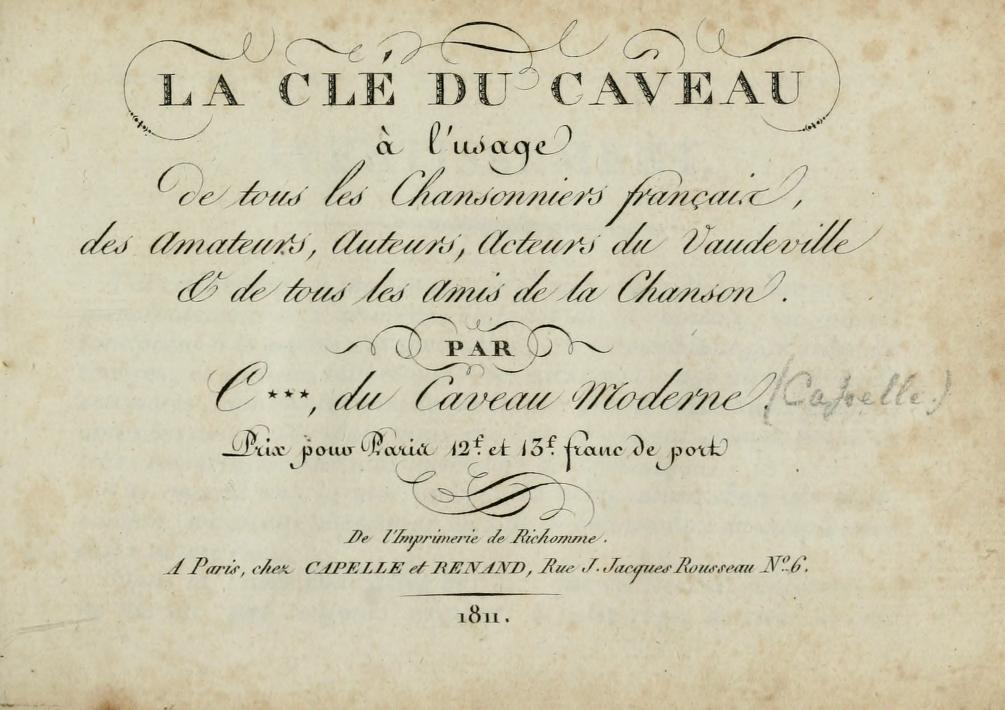
我沒有辦法將這個文本轉化聲音,但是有位才華洋溢的歌劇演員,同時也是巴黎夜總會的歌手達拉芙(Hélène Delavault),會在本場演講後用法式夜總會的音樂會形式,為各位演唱好幾首曲子,內容全都是關於1749年發生的事件,包括其中有兩首與我們剛剛提到「十四人案」直接有關,也就是「鴛尾花的姿態」(Par vos façons nobles et franches)和「那個大混蛋臭婊子」。
若你是在美國歷史學會的網站上讀到這篇演講,你可以點選其中的超連結,聆聽達拉芙親自錄製的歌曲。簡單來說,二十一世紀的資訊科技為我們開了一扇1750年的窗戶,讓我們聽見歷史歌唱。
*那個大混蛋臭婊子
全文歌詞與更多的錄音請上:http://www.hup.harvard.edu/features/poetry-and-the-police/
下集預告:八卦流言如何拖垮一個政權──18世紀巴黎的新聞與媒體(四)
本文作者為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暨講座教授
本文譯者為密西根大學社工所畢業,現專職翻譯寫作
註釋:
[28]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new edn. (Neuchâtel, 1788), 1: 282. Mercier also remarked (6: 40): "Ainsi à Paris tout est matière à chanson; et quiconque, maréchal de France ou pendu, n'a pas été chansonné a beau faire, il demeurera inconnu au peuple." Among the many historical studies of French songs, see especially Emile Raunié, Chansonnier historique du XVIIIe siècle, 10 vols. (Paris, 1879–84); Patrice Coirault, Formation de nos chansons folkloriques, 4 vols. (Paris, 1953); Rolf Reichardt and Herbert Schneider, "Chanson et musique populaire devant l'histoir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Dix-huitième siècle 18 (1986): 117–44; and Giles Barber, "'Malbrouck s'en va-t-en guerre' or, How History Reaches the Nursery," in Gillian Avery and Julia Briggs, eds., Children and Their Book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to Celebrate the Work of Iona and Peter Opie (Oxford, 1989), 135–63.
[29] This bon mot may have been coined by Sébastien-Roch Nicolas Chamfort: see Raunié, Chansonnier historique, 1: i.
[30] One box in the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ms. 10319, contains dozens of these snippets, thrown together helter-skelter, which comment in rhyme on all sorts of current events: the amorous adventures of the regent, Law's fiscal system, the battles of the Jansenists and Jesuits, the tax reforms of the abbé Terray, the judicial reforms of the chancellor Maupeou—set to all kinds of popular tunes: "La béquille du Père Barnabas," "Réveillez-vous belle endormie," "Allons cher coeur, point de rigueur," "J'avais pris femme laide." The repertory of melodies was inexhaustible, the occasions for drawing on it endless, thanks to the inventiveness of the Parisians and the rumor mill at work in the court.
[31] BA, ms. 11683, fol. 59, report on the arrest of Mairobert by Joseph d'Hémery, July 2, 1749. The verse on the scrap of paper comes from a separate dossier labeled "68 pièces paraphées." In a report to the police on July 1, 1749, a spy noted (fol. 55): "Le sieur Mairobert a sur lui des vers contre le roi et contre Mme. de Pompadour. En raisonnant avec lui sur le risque que court l'auteur de pareils écrits, il répondit qu'il n'en courait aucun, qu'il ne s'agissait que d'en glisser dans la poche de quelqu'un dans un café ou au spectacle pour les répandre sans risque ou d'en laisser tomber des copies aux promenades . . . J'ai lieu de penser qu'il en a distribué bon nombre."
[32] BA, ms. 11683, fol. 45.
[33] Maurepas' love of songs and poems about current events is mentioned in many contemporary sources. See, for example, Rathery, 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is d'Argenson, 5: 446; and Edmond-Jean-François Barbier, Chronique de la régence et du règne de Louis XV (1718–1763), ou Journal de Barbier, avocat au Parlement de Paris (Paris, 1858), 4: 362–66.
[34] Rathery, Journal et mémoires de marquis d'Argenson, 5: 448, 452, 456. The following version is taken from d'Argenson's account of this episode, 456. See also Barbier, Chronique, 4: 361–67; Charles Collé, Journal et mémoires de Charles Collé (Paris, 1868), 1: 71; and François Joachim de Pierre, Cardinal de Bernis, Mémoires et lettres de François-Joachim de Pierre, cardinal de Bernis (1715–1758)(Paris, 1878), 120. A full and well-informed account of Maurepas' fall, which includes a version of the song that has "Pompadour" in place of "Iris," appears in a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songs in the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ms. 649, 121–27.
[35]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Nîmes, 1778), 1: 526: "FLEURS, au pluriel, se dit pour flueurset signifie les règles, les purgations des femmes . . . On appelle fleurs blanches une certaine maladie des femmes." Rather than 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like gonorrhea, this maladie might have been clorosis, or green-sickness.
[36] In addition to the references given above, note 30, see Bernard Cottret and Monique Cottret, "Les chansons du mal-aimé: Raison d'Etat et rumeur publique (1748–1750)," in Histoire sociale, sensibilités collectives et mentalités: Mélanges Robert Mandrou (Paris, 1985), 303–15.
[37] BA, ms. 11690, fol. 66.
[38]I have discussed this affair at length in an essay, "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to be published sometime in 2001 by 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Its text, which contains references to a great deal of source material, can be consulted in the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is essay, on the AHR web site, www.indiana.edu/~ahr. Most of the documentation comes from the dossiers grouped together in BA, ms. 11690.
[39] Marc Pierre de Voyer de Paulmy, Comte d'Argenson, to Nicolas René Berryer, June 26, 1749, BA, ms. 11690, fol. 42.
[40] "Interrogatoire du sieur Bonis," July 4, 1749, BA, ms. 11690, fols. 46–47.
[41] Vie privée de Louis XV, ou principaux événements, particularités et anecdotes de son règne(London, 1781), 2: 301–02. See also Les fastes de Louis XV, de ses ministres, maîtresses, généraux et autres notables personnages de son règne (Villefranche, 1782), 1: 333–40.
[42] My own understanding of this field owes a great deal to conversations with Robert Merton and Elihu Katz. On Gabriel Tarde, see his dated but still stimulating work, L'opinion et la foule (Paris, 1901); and Terry N. Clark, ed.,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Chicago, 1969). For my part, I find Habermas's no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valid enough as a conceptual tool; but I think that some of his followers make the mistake of reifying it, so that it becomes an active agent in history, an actual force that produces actual effects—including, in some cas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For some stimulating and sympathetic discussion of the Habermas thesis, see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 Mass., 1992).
[43] I have located and compared the texts of nine manuscript versions of this song. The first verse, quoted below and reproduced in Figure 10, comes from the scrap of paper taken from the pockets of Christophe Guyard during his interrogation in the Bastille: BA, ms. 11690, fols. 67–68. The other texts come from: BA, ms. 11683, fol. 134; ms. 11683, fol. 132; BNF, ms. fr. 12717, pp. 1–3; ms. 12718, p. 53; ms. 12719, p. 83;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ms. 648, pp. 393–96; ms. 649, pp. 70–74; and ms. 580, pp. 248–49.
[44] Albert B. 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ss., 1960), shows how the rhythms of poetry and music contribute to the extraordinary feats of memorizing epic poems.
[45] Unfortunately, the chansonnier Maurepas stops in 1747, but the even richer chansonnierClairambault extends through the mid-century years: BNF, mss. fr. 12717–20.
[46]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mss. 648–50.
[47] P. Capelle, La clef du Caveau, à l'usage de tous les chansonniers français (Paris, 1816); and J.-B. Christophe Ballard, La clef des chansonniers (Paris, 1717). Most of the other "keys" are anonymous manuscripts available in the Fonds Weckerlin of the BNF. The most important for this research project are Recueil d'anciens vaudevilles, romances, chansons galantes et grivoises, brunettes, airs tendres(1729) and Recueil de timbres de vaudevilles nottés de La Coquette sans le savoir et autres pièces à vaudeville (n.d.). For help in locating this music, I would like to thank Hélène Delavault, Gérard Carreau, and Andrew Clark. Hélène Delavault has recorded fourteen of the songs that circulated in Paris during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749–1750, and the songs and lyrics are available on the AHR web site.
[48]Louis Petit de Bachaumont, the doyen of Mme. Doublet's salon, had a lackey known as "France": see Funck-Brentano, Figaro et ses devanciers, 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