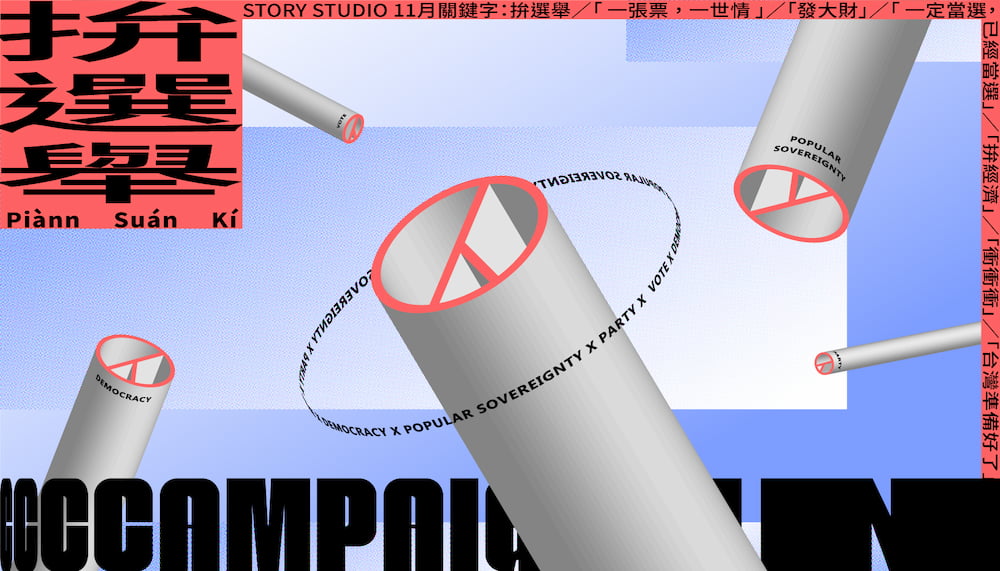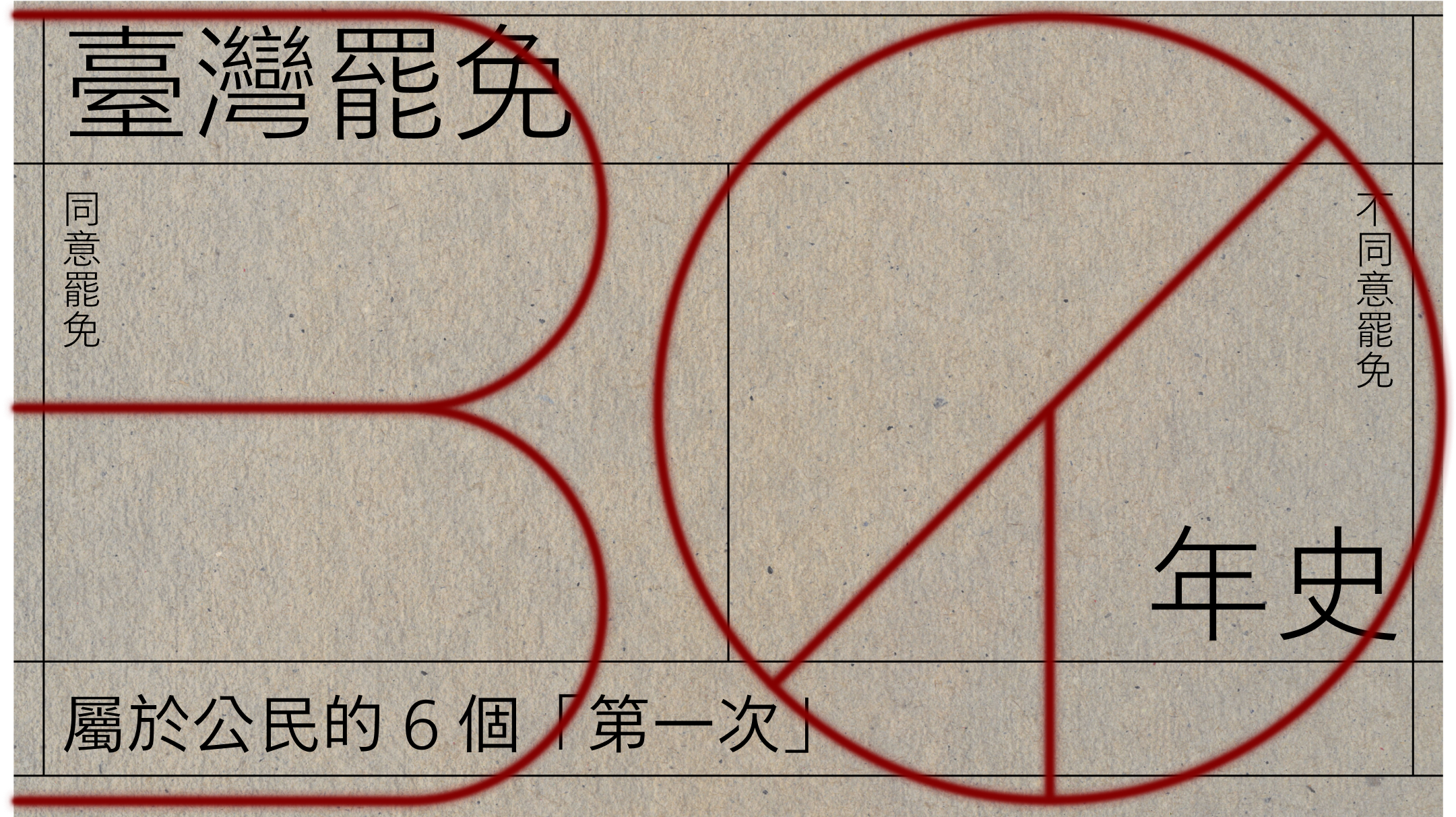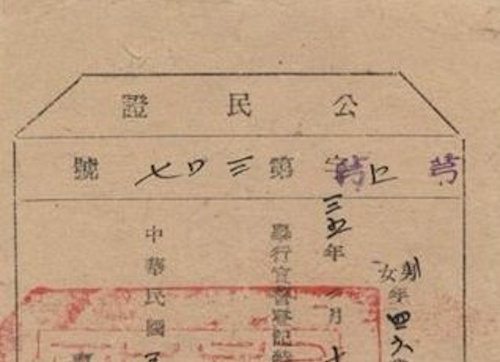著名的哲學教授、也是活躍的公共知識份子薩巴特(Fernando Savater),三十年前寫了一本書,叫「給阿瑪多的政治學( Politica Para Amador )」(中譯本《哲學大師寫給每個人的政治思考課》於 2015 年出版 )。在這本書裡,薩巴特用對話的方式,和幻想中的小兒子讀者「阿瑪多」解釋,為什麼我們要關心政治、要勇於認識政治,而又為什麼「政治參與」對當代人如此重要。
根據本書譯者魏然,給阿瑪多的話裡最常出現的字之一,是「悖論」。
是的,政治充滿矛盾,民主社會裡,充滿看似顛倒的悖論。
例如,生活在一個充滿選擇的民主社會,看似是一件好事,但有的時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複雜的事。薩巴特直接而誠懇地告訴阿瑪多,今日的民主社會並未比過去的專制政府解決更多問題,也恐怕並沒有凝聚更團結的社會、打造出更健全的制度,或者給人民更有錢的生活。相反的,在眾聲喧嘩、眾生平等的前提之中,「民主唯一能保證的事情是,將會有很多的衝突。」
又例如,鄂蘭認為,一個人只有在民主政治裡才是真正「自由」的,既不統治,也不生活在統治之下。這句話並沒有錯,但薩巴特進一步睿智地指出,「自由」其實會令人恐慌,恐慌到想逃。
因為,作為一個獨立自由的人,就意味著將面臨各式各樣的犯錯的可能、失誤的可能、被誘惑的可能,而我們必須承擔起過失的全部責任。
因為,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沒有人生來就是神一般的統治者,沒有人生來就享有比別人多的權利,也沒有人可以將自己的成功或失敗,完全歸責給國家。這個國家的每次進步,每場災難,上面都寫著你的名字,無論有多渺小。
自由確實會令人恐慌,現代社會中的自由個人,就像獨立漂浮在一片無際無邊的汪洋裡,沒有任何其它依靠,所有方向和價值都必須由自己判斷決定。沒有神、沒有領導、沒有既定俗成。
「(阿瑪多,)你不要以為永遠是執政者想要取締自由或者盡可能消減自由──在很多情況下,是公民們對自由感到厭倦或恐懼,於是主動呼籲當權者進行鎮壓。」
薩巴特說,民主的敵人經常不在外頭,而在於內部人民害怕他們擁有的「過多」自由,也害怕別人擁有的自由,所以,他們情願當一個被約束的信徒,一個受指導的狂熱者,一個依附家長的巨嬰。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放心把自己的選擇權交給別人。政府的禁令與限制越多,自由越少,他們反而越安心越滿足。
「每當民眾要求國家『為了我們好』而限制自由時,國家決計不會放過這個天賜良機。」
此所以,民主政治最大的悖論就在於,自由的公民可以利用這個社會所賦予他們的自由,來終結自己(和其他人)的自由。別忘了,有些極權領導者,如希特勒,就是通過選舉程序上台的。
國家的最終目標不是統治眾人,不是讓他們感到恐懼而保持沈默,或是屈從別人的權力,正相反,它的目標是把每個人從恐懼中解放出來,在最大限度上安全地生活。—史賓諾沙
薩巴特的祖國西班牙,在 1936 -1939 年間陷入嚴酷的內戰。以「反右派極權」為精神的共和軍和人民陣線,吸引了數以萬計來自歐美各地的理想青年(如文豪海明威),拋棄舒適的家園,加入遙遠的國度為自由、民主的抗爭行列。
在抗爭期間,曾有人問共和派領袖、西班牙第二共和總統阿薩尼亞(Manuel Azaña),真的相信自由可以讓人民更加幸福快樂嗎?
總統回答,「老實說,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能肯定,自由可以讓人們活得更像一個人。」
專題上線前幾個晚上,香港學子在校園遍地的煙霧和烈火中,揮舞著自由的黑色旗幟,年輕的手寫好了遺書,放在溫熱的口袋裡。三十年前哲學家那一番給小朋友的叮嚀,以及明年臺灣即將要「拚」的民主選舉,在這個時候看來,格外地抽鞭腦神經。民主選舉難道是當今抵抗極權的,所僅存少數、被動而脆弱的武器?
臺灣解嚴後拚了三十多年的選舉,作為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我們貌似還在摸索學習。有時我們的競選像場舞台大秀,有時政治讓人覺得宛如荒謬派戲劇,但這個自由的國家在過去一場一場選舉中,展現了每一個時代的精神和文化特性,在民主的路上慢慢前進。而自由的臺灣人,將在未來的選舉中,作一個獨立而勇敢的公民,帶著國家繼續拚下去。
(本文作者為故事StoryStudio 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