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的墨西哥室藏有一把刀,長約 30 公分,雪松木做的刀柄,石髓石打造的刀身,刀尖十分銳利,刀刃還細心雕成鋸齒狀。刀柄的製作尤其精美華麗:柄身是一塊散發著香味的深色木頭──那是墨西哥最珍貴的木頭,因為這種木頭特別能防白蟻。整塊木頭鑲著精美的圖案,由淺色的松綠石與深綠色的孔雀石交錯排列而成,中間還點綴著三種貝殼:珠母貝、白色海螺貝,以及深紅色的多刺牡蠣貝。

當你仔細欣賞鑲嵌的圖案及其對比的顏色時,可能得花一點時間才能看出,那個圖案其實是一個蹲伏著的阿茲特克人。這個阿茲特克人的臉隱藏在一個鷹喙頭套裡──這種鷹嘴張開的頭套是個身分標記,表示他是一個高階的「老鷹武士」;他的下巴靠在可怕的刀刃起始處附近。他袒露著牙齒,目光炯炯,專注地看著刀尖。
這件展品的做工精緻,手藝高超,加上博物館展場那清冷、安靜的氣氛,讓人一點都猜不到這把刀來自何處、有何用途。要了解這把刀的用途,你得移動目光,望向刀柄,望向刀身本身──那位製刀者的手藝是如此精巧,以至於武士的每一顆牙齒都刻得清清楚楚。這時,那個蹲伏著的男子之所以顯得如此急切,如此專注,其原因終於變得清楚了:原來他正在等待血──人類的血。
大約在公元 1500 年左右,這樣的刀──或許就是這一把──是用來切入人類腹部,從胸腔下方切到橫隔膜,先製造一個開口。此時神殿上的祭司會立刻伸手探入那個開口,迅速摸向上方的心臟,把心臟扯出來。接著他會把還在跳動的心臟放入一個特製的淺碗裡─這個專為放置心臟而製作的淺碗是由玄武岩刻成,碗的下方有個很高的底座,座身刻著太陽圖案,淺碗邊緣則塑成人類心臟的樣子。剛剛被摘下心臟的受害者,他的身體則被推下神殿的台階。
神殿的台階下面聚了數千名觀眾,圍觀剛剛那一幕充滿血腥與痛苦的場面。心臟取出,儀式完成,他們全都歡呼慶賀,周遭有各種打擊樂器和絃樂器的演奏,還有歌舞隊載歌載舞的表演。阿茲特克人舉行活人獻祭通常都是因為國家打了勝仗。這是一場國家勝利的展演。透過殺死敵人,肯定阿茲特克人的權力──在太陽神與戰神維齊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的保護之下,他們開疆拓土,擴展帝國的權力。

英文單字「sacrice」(祭祀)源自拉丁文,本意指做一件神聖的事。這個字涉及許多古代地中海的宗教傳統,以及這些傳統如何影響我們的思考習慣至今;而所謂「神聖的事」,也不只是指奉獻祭品或禮物這個概念而已。祭祀這個字所隱含的意義不只是把珍貴的物品放在我們永遠拿不到的地方,一如穆伊斯卡人的黃金,實際上指的是摧毀那個物品,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讓一個更高的力量息怒,我們才能完成某個更崇高的目的。
把酒倒入地裡作為獻禮、燃燒珍貴的香作為獻祭,這兩者都是很明顯的例子,因為酒與香經過祭祀之後就永遠不能再使用了。但是祭祀的活動可以重複舉行,而且通常不僅止於獻酒或燒香,這裡所謂的「摧毀」可能是指灑血,也可能是奪取他者的生命。
如果說「sacrice」這個英文單字衍生自羅馬的傳統和習俗,那麼這個概念本身則幾乎是普遍共有的。近數十年來,祭祀是讓宗教歷史學家最擔心的主題,尤其是那種公開的、儀式性的動物獻祭或活人獻祭。
有些學者認為這類祭祀行為呈現了人類天生內在暴力的一面,而舉行祭祀就是承認這種暴力、限制這種暴力,同時緩解或驅除因這種暴力而造成的集體罪惡感。有些學者則把目光聚焦於祭祀在建立社群、團結社群成員所扮演的角色。幾乎沒有學者觸及身為人類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即種種更為深沉的情感這個主題。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個主題讓人覺得不安。
傑戈.庫柏是大英博物館美洲部門的主管,根據他的看法,如果你要進入阿茲特克石頭刀背後隱藏的思想世界,了解跟這把刀有關的儀式性殺人事件,你首先必須了解阿茲特克人對戰爭的看法:
阿茲特克是個相對短暫的帝國,大概只維持了一百年左右;這個帝國在公元1428 年左右崛起,此後就一直處於戰鬥的狀態之中。這個帝國興起之後就極力發展並擴張國土,勢力幾乎涵蓋了現代墨西哥大部分地區和美國南方的部分區域。直到1521 年,西班牙征服者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入侵,這個帝國才迅速瓦解並徹底走向滅亡。在這個極度軍事化的帝國,「老鷹戰士」是政府部門最高級的職位。要爬到這個階級,你得在戰爭中捕獲一名受害者,將之帶回部落囚禁或下放為奴──或公開獻祭給神。

阿茲特克帝國擴張國土之際,英國也正在打玫瑰戰爭。在這段時期,歐洲人的戰爭通常涉及大量傷亡:殺傷力極強的箭到處亂飛,數以千計的士兵手持銳利的金屬武器互相砍殺,一心一意想把對方砍死。不管結果如何,交戰的雙方都會留下好幾百名受了傷或斷手斷腳的士兵,讓他們痛苦地留在戰場上等死。阿茲特克人的戰事跟歐洲人不一樣──非常不一樣。歐洲人在戰場上的殘酷行徑,還有歐洲人在戰場上屠殺大量士兵,看在阿茲特克人眼裡是極其可怕的。阿茲特克人上戰場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打敗敵人,俘虜敵人。通常他們的戰士會在戰場上俘虜一個受害者,將之帶回首都。把敵人全部殺死對阿茲特克人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依賴投降的部族奉獻貢金,而貢金來自那些從戰場上回來的人。他們會從敵方的軍隊裡捉幾個人作樣本,而不是把整支軍隊殲滅。那個被刀挖出心臟的人有可能是個戰犯;獻祭戰犯是阿茲特克人最常見的獻祭形式。
我們不難想像,這樣的死亡祭祀如果被阿茲特克人的潛在對手看到,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威懾效果。再者,他們這種蓄意的嗜血儀式有可能是特地設計的活動,目的是遏止戰爭帶來的殺害與痛苦──雖然這是一個耐人尋味、但有點違反直覺的想法。不過我們可以確定,這個嗜血儀式對西班牙人很有利,他們得以據此極力強調阿茲特克人的殘酷,同時大肆屠殺阿茲特克人和劫掠他們的帝國。
就祭儀和實際兩個層面而言,這把石刀既象徵且體現了阿茲特克戰爭的兩個重要面向:一是把精挑細選的敵人殺了獻給神,二是對他們征服的人民索取貢金。裝飾這把石刀的不同零件,例如松綠石、孔雀石、帶刺的牡蠣貝和珠母貝等,全都是極為珍貴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貢禮,來自帝國不同的區域──有些區域彼此竟相隔數百英里之遠,我們也常在現存的貢禮清單上看到這些材料。由此可知,這些在各個地方收集到的材料,最後會全數運回帝國的首都,然後再打造成最華麗的祭儀用品。
不論在心理上或是在經濟上,阿茲特克人發動的戰爭看來都很合理。據傑戈.庫柏所述,阿茲特克人的活人祭祀還另有其他重大的宗教意義:
阿茲特克人的神──維齊洛波奇特利──不僅是個戰神,同時也與燃燒的太陽有關。阿茲特克人相信諸神曾經犧牲自己,流血以創造人類的生命。人類的心臟被視為太陽力量在地球上的一滴精華。因此,阿茲特克祭司從人體取出一顆心臟,將之奉獻給神,這有一部分是為了償還所有人類欠下的巨大債務。同時也希望這份奉獻足以幫助太陽繼續在既定的軌道上運行──這就是為什麼那個盛放人類心臟的淺盤底座會刻上太陽的圖案。在阿茲特克這個重視死亡方式的社會裡,作為祭品而死是一種良善的、有益眾生的死法。
誠如我們在前一章看到的,人類獻給諸神禮物通常是為了從諸神那裡獲得各種益處。阿茲特克人也是如此,他們希望透過活人鮮血的溢流,來維持帝國與宇宙秩序的穩定。

涅內伊德碑像(the Nereid Monument)是一座巨墓,位於克桑托斯古城(Xanthos),亦即現代的土耳其西部;由於巨墓的許多鑲板都刻著跳舞的水神涅內伊德(Nereids),因而如此命名。這座巨墓建於公元前4世紀初,墓主是當地的國君厄爾賓納(Erbinna)。建築風格模仿希臘愛奧尼亞柱式神殿,嵌著大量雕刻鑲板;這些鑲板本來是有顏色的,不過現在已經褪成淺灰色。鑲板上刻著厄爾賓納王在政治與軍事兩個領域所扮演的多種角色:接見大使、舉辦晚宴等。但是其中有兩片描繪人民公共生活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動物獻祭。
看過阿茲特克人壯麗血腥的活人祭祀之後,我們可能以為希臘式的涅內伊德碑像會帶給我們一個平靜的、令人寬慰的畫面:古典的長袍、托加袍,還有清晰刻畫的美麗圖景。其實不然,我們發現涅內伊德碑像也充滿了殘忍的暴力。在其中一面鑲板上,我們看到有個人抓住羊角,努力把羊往前拉,而那隻羊抵死不肯,只見牠用盡全身力量抗拒,蹄子深深埋入地裡,身體極力往後退。羊的後面有人牽著一頭牛跟著。
在第二片鑲板裡,我們終於看到等著兩隻動物的是什麼了:祭台。有一個看來像是祭司的人站在祭台一側,另一側的男子已經脫下了上衣,以免弄髒。我們幾乎就快看到儀式即將開始,聽到動物尖叫,看到牛羊的屍體被肢解,血濺得到處都是,蒼蠅一大群一大群飛來,動物內臟的惡臭飄散在空氣裡。希臘神殿的教區通常也是神聖的公開屠宰場。
在古代地中海地區,像這種定期殺死家畜的祭祀儀式相當常見──除了希臘人,羅馬人、腓尼基人,在耶路撒冷神殿的猶太人也會舉行這樣的獻祭儀式。很明顯地,這是一件可怕的工作,你難免會聞到動物排泄物的臭味。但這也是一個重要和嚴肅的宗教活動,不論私人或公共領域皆是如此。艾絲特.埃迪諾(Esther Eidinow)是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 University)的古代史教授,根據她的解釋:
動物祭祀是個重要的儀式,透過這個儀式,你可以跟你看不見的諸神溝通:你透過動物獻祭來敬拜諸神,感謝諸神。透過觀察動物的內臟,你可以得知諸神是否站在你這一邊。你向諸神請求的事物,也是透過觀察動物內臟顯示諸神是否應許。

換句話說,古典世界舉行的動物祭祀,其功用在某些方面與基督宗教傳統中的祈禱是一樣的:這是一種儀式性的語言,透過這種語言,你可以跟神明說話,也聆聽神明對你說話。舉行祭祀的方式很多,可以在自己的家裡,也可以跟一小群人共同舉辦。不過,規模龐大的市民慶典當然是在神殿裡舉行。
如果神殿裡正在舉辦祭祀活動,你一定會知道的,因為你會聞到祭祀的氣味。祭祀之前通常會有一個遊行隊伍,引領一頭戴著花圈的動物走向祭壇。那頭動物是經過千挑萬選才選出來的,因為用來祭祀的動物必須品種優良,長相漂亮,身價高貴,這樣神明看了才會歡喜。祭壇早已從神殿裡搬出來,放在神殿前面──祭壇必須放在神殿外面,這樣諸神才看得到祭祀,並且聞得到祭祀的味道。祭司通常會面向東方站著,面向正在升起的太陽。在整體效果上,祭祀活動是色彩斑斕的,用意是吸引大量民眾前往參與
諸神是預期中的部分觀眾。人們總是假設神明會來參加祭祀活動──神明一定會前來聽取人們的禱告、回應人們的禱告、享用香爐裡燃燒的香味和動物遺骸燃燒的氣味,還有來聽現場伴隨的音樂。在理論上,動物必須同意被獻祭(就像第五章提到的海豹):如果是大型動物,人們會在祭祀前對牠潑水,使牠點頭。艾絲特.埃迪諾解釋道:
如果用來祭祀的是大型動物,例如公牛,他們會先把牠震昏,然後再割開牠的喉嚨。如果是小型動物,就直接以一把長刀快速割喉了事。在動物被殺的那一刻,現場的婦女觀眾會大聲哀嚎,這是一種儀式性的嚎叫,為祭祀典禮帶來另一層感官上的經驗。
有學者認為這類程序繁複的儀式可能是承認殺生這件事本身那種令人震驚的性質。如果濺血是必要的,那麼這件事就必須公開地、嚴肅地,在整個社群面前、在諸神的面前做。被犧牲的動物必須公開地接受榮耀,因為牠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在儀式的架構之下放棄生命。神聖的殺生儀式接收了每個人在殺生過程中應該感受到與必須感受到的罪;但它也會找到方法來贖罪,或至少遏止這種罪。就像阿茲特克人的活祭儀式,在我們看來這個殺生儀式似乎很殘酷,但是它有可能帶著某種深沉的、合乎道德的職責。

在希臘神殿中,一旦動物已經在祭典裡完成任務,另一個刺激感官的新元素隨即加入:烤肉的聲音與氣味。一般而言,獻神的祭祀過後,接下來就是一場每個人都可參與的盛宴,諸神當然也在被邀請之列。在《伊里亞德》(Iliad)第一章,荷馬給了我們一份難忘的敘述──那是奧德修斯和他的士兵共同舉辦的、獻給阿波羅的祭祀宴會。用艾絲特.埃迪諾的話來說:
他們把受害者的頭往後拉,切開喉嚨,然後再剝皮。接著他們從腿部切下長條肉片,用一層層油脂將肉片包裹起來,在這上面放上生肉,接著整個放在火上烤。負責烤肉的是一個老人,他偶爾會給那些烤肉灑一點紅酒。其他年輕男子就站在旁邊等待,手裡拿著五叉的叉子。
涅內伊德碑像中的祭祀鑲板和隨著祭祀而來的宴會場景傳達了一個希望,即希望碑像的創造者可以永遠參與這種盛大的祭典──在這種祭典中,統治者本人通常扮演著祭司的角色。如果用這樣的角度看,祭祀並不僅只是犧牲一頭家畜來換取大家的好運。相反地,祭祀凝聚了社群中的每一個人,使之產生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團結感;祭祀讓大家有機會一起分享食物,也跟諸神分享食物。對許多希臘人而言,這很有可能是他們唯一吃肉的機會。當然,這樣的祭祀也有一些嚴格的規定必須遵守。根據艾絲特.埃迪諾的說法:
動物的屍體會按部位切開來分給大家──有些分給諸神,有些分給人。大腿骨、薦骨和尾巴首先被取出來焚燒給諸神,因為諸神只食用煙霧。內臟得送去給專家檢驗,觀察諸神是否同意這次祭祀,接著才用烤叉串起來放在火上烤。屍體被整個切開,可能就在現場烤了吃,也可能之後再烤來吃。有時候在神殿附近不遠的地方會有食堂,人們可以到那裡烤肉來吃,或把肉帶回家裡煮食。肉的分配很公平,祭祀儀式提供的肉品在這裡成為食物,成為餵養社會的一部分。
希臘動物獻祭的「宗教儀式」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與諸神以及其他人之間的關係同時得到強化。人們帶著強烈的情感和滿滿的感官經驗聚在一起參加儀式。接著他們聚在一起用餐,他們就在諸神面前分享食物,但是因為諸神只食用煙霧,這提醒了人們神人有別,兩者各自住在不同的宇宙空間裡。世界、人類、動物和諸神的關係既分離又相互關聯,既獨立又彼此依賴──在儀式中,這個秩序再一次得到肯定。
希臘人這個偉大的市民與宗教儀式後來被羅馬人接收,並且在整個羅馬帝國裡實行,這個儀式因此深具影響力,而這一點我們不用再多加強調。這是一個由祭司執行、人民希望可以得到認可與接受的犧牲祭儀。祭祀的煙往上飄升。犧牲者的血被人喝下,犧牲者的身體被社群的所有人瓜分共享──在這個過程中,社群因之而更團結,因之而更強大。從這個古典世界發展起來的基督教,他們把新信仰的中心儀式描繪成犧牲祭儀和「羔羊」的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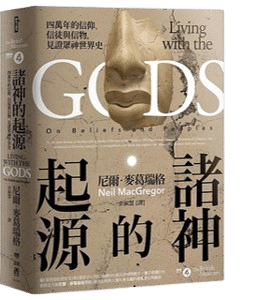
每個社會都會有一套建立認同的信念和假設,它界定人存在的意義、區分社群,在許多地區甚至是政治的動力;這套信念和假設通常被稱為信仰、意識形態或宗教,但它絕對不只是「信仰」或「宗教」。
《諸神的起源》綜觀歷史、環視全球,審視器物、地景和儀式活動,書中不討論宗教史,不探討信仰,更不會替任何信仰體系辯護;本書探究的是這套共有的信念對社群或國家的意義、它如何形塑個體與國家的關係,以及人們在這套信念底下究竟相信些什麼、依何而行動,透過怎樣的方式定義「誰能夠成為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