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太平天國之秋》的譯本在臺暢銷,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以後稱:裴士鋒)的第一本著作也在今年出版,即由其博士論文而改寫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此書接續 1995 年至 2010 年間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之高漲,藉由討論湖南人在十九後半葉、二十世紀初巨變百出的中國史上之角色,試圖從一個以北京及通商口岸為核心的主流敘述,轉向承認刻板印象中保守落後的湖南省之重要性,甚至點明湖南己身的民族主義及其根生低故的傳統,來脫離中國民族主義對歷史詮釋的壟斷和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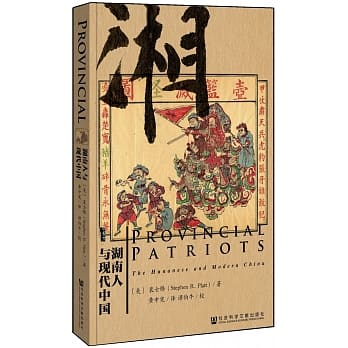
裴士鋒如其老師史景遷一樣文筆非常好,其研究因此具有故事性,相當好讀。這本書以明代湘省遺老的王夫之為主旨,以之聯繫了歷史舞台上的主角,如曾國藩、郭松濤、或毛澤東,以及較少人知曉的配角,如歐陽兆熊、楊毓麟、或劉人熙,不只介紹一個以湘人為主軸的近代史,也析論湖南菁英對己省的認同觀如何形成,來顯著其省籍認同在歷史上的關鍵性。
裴士鋒認為,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湖南菁英奠基了以王夫之崇拜為中心的自我認同,以之克服了湘省於中原文化圈中的邊緣性,然經歷湘軍大敗太平天國勢力所帶來的苦難及光榮,其發展出以湖南(或楚)為核心且頗有普遍性的愛國主義(所謂的 regional pride),並且宣揚湖南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大使命。
到了晚清的時候,湖南從改革運動的前鋒轉向革命思想的蜂窩,而裴士鋒認為,仍未脫離以天下為框的愛國主義,恰好在此因為譚嗣同、唐才常、陳天華等湘人所受的壓迫,以及楊毓麟的《新湖南》等著作之流行,已經發展出以湖南為宗旨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湖南主義,在裴士鋒的論述之下,不僅是中國民族主義之一,而是以湖南為最高價值、甚至作為反對中國或漢人此類大符號的一個思潮,就在晚清至民國初期的亂世中繼續主導湖南知識份子的思維,到 1920 年代仍支配了毛澤東等人所鼓舞的湖南自治運動。
裴士鋒以「草根民族主義」(grassroots nationalism)指稱這樣的認同觀,即具有強烈的地方性、奠基於區域文化的特殊象徵、透過人際網絡及私人媒體推廣的一種愛國主義,而與之對立的,乃是「以國家為導向的民族主義」(state-led nationalism),也就是透過國家教育體制、政治宣傳、官方媒體傳播的一種意識形態。本書所討論的湖南人屬於前者,也因此經常與官方及保守份子所代表的中央主義(centralism)處於矛盾的立場,導致兩者在晚清至民國初年的二十幾年內,往往發生衝突,致湖南的民族主義最後也敗於中央政府為了鞏固新國家而渲染的國族主義。
然而,對治史者來講,裴士鋒的著作似乎太過於忽略了前人之研究,最明顯的問題大概就是關於中國民族主義及一般民族主義的討論。裴士鋒雖提出上述的「草根」、「以國家為導向」兩種民族主義,但其僅作為一種分類,且本書未提供此基本定義,導致其雖然趣味豐富,卻在其所選定的學術領域中難以發揮多大的影響,最終也不會提供讀者更多關於中國民族主義本身的啟發(畢竟李達嘉、杜贊奇等人早就析論過具有「地方」色彩的民族認同,儘管其何以界定「地方」是一個仍待討論的問題),甚至也難以將中國晚清以來強而有力的民族主義思潮放在一種全球性的討論脈絡,也因此對關於民族主義性質的爭議(此認同是現代形成中才出現的,還是古典時代早就有的?)未有貢獻。
換言之,研究民族主義的關鍵不在地緣,而是回答關於其本質的問題,即為何在近現代許多地方能發展出一個極度普遍的認同觀?以省為認同的價值觀,卻為何始終無法勝過更大且模糊的中國論述?
要回答此問題,除了討論傳統上中央與省間的關係,也必須分析晚清時出現的一些年輕菁英,逐漸超越傳統士紳的認同觀,而裴士鋒所選的湘省其實可以作為很好的例子,但因為作者執著於地理上海岸城市與內地湖南省之虛擬對立,又似乎在情感上對湖南有著一種浪漫的想像,導致其分析在這方面其實有預先立場之嫌,故只不過在地圖上修改民族認同的範圍,卻不大處理這些新知識份子在思想上的演變,也不多討論其與觀眾、地方菁英的關係。
簡而言之,裴士鋒所質疑的非是民族主義本身,而是以中國為對象的民族主義之合理性和代表性,故以湖南人的非凡主義(exceptionalism)取代之,因而自己塑造一個湖南人與中國、其他省截然不同的形象,也往往化小如廣東、浙江等省的省籍主義,以成立湘省獨特的假設。這種前提之下,作者誇張地把湖南如此龐大的省視為「地方」,假定其因此就比較不會面臨對關於其想像及凝聚力的質疑〔如中國曾被費約翰(John Fitzgerald)說成是「無民族的國家」──即「nationless state」〕,因此可以作為較為真實的民族認同對象。

裴士鋒這樣能以湖南的「地方」取代中國──「帝國」,但不會真的逃避安德生《想像共同體》裡對民族國家的基本疑問,因為其所描述的湖南民族主義,最後仍是少數屬於精英階層的人所鼓舞的。雖然可以說湘軍的經驗產生一種跨越階級的認同,不過那只是一時的,而「以天下為己任」的湖南觀以湘紳為核心,也明顯地把湖南與(朝廷為主幹的)天下綁得緊緊的。 到晚清最後十幾年,新知識份子才因與士紳日趣矛盾,又希望可以鼓動支持者,所以把它轉換成較為積極的,且與清廷處於對立的省籍認同,而王先謙等士紳就激烈地反對湖南獨立的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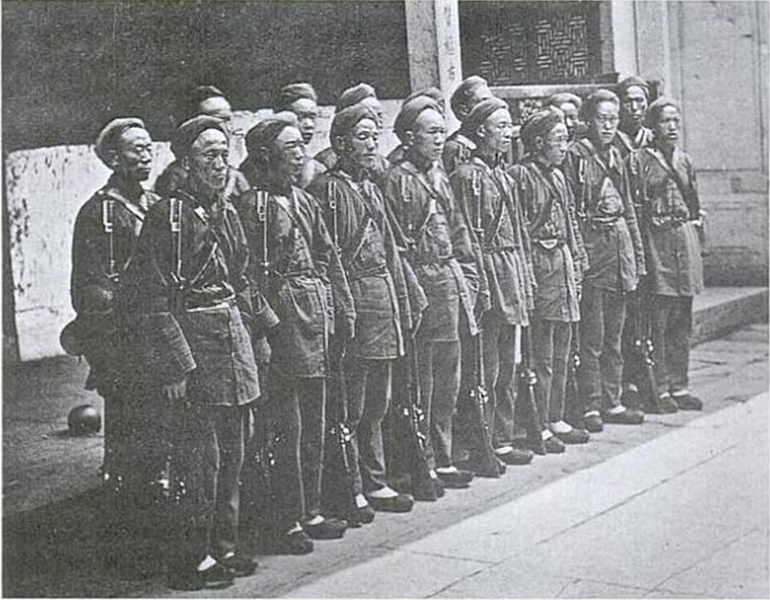
當然,裴士鋒或許沒這個意思,並非企圖加入關於民族主義本質的爭辯,僅希望可以補充關於湖南人對己省的認同;在這方面其書算是成功的,也毫無疑問地有學術價值,畢竟他注意到湖南的獨特性,而避免將之視為十八同質性高的省之一。
不過,裴士鋒的研究恐怕也面臨一個矛盾的情況:本質上似乎還未脫離中國民族主義。因為以看似於較為合理的「湖南認同」,來取代中國民族主義,實際上仍運用了民族主義者的邏輯,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容易遭熟於史料且持有民族情懷的學者以無數的反證「修正」其湖南說;另一方面,作者也經常被自己的分析對象「背叛」了,因為其湖南民族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也都強烈地鼓舞中國的民族主義,導致裴士鋒只好以「有所選擇」地採用特定的史料,也因此自己似乎像民族主義者一般,壓抑湖南及中國認同的複雜性、多聲性。
舉例而言,在書中,楊毓麟是主導湖南民族主義發展的角色,不僅撰寫了被裴士鋒視為具有宣言地位(manifesto)的《新湖南》一書,後來也幫忙出版造成湖南民族主義高峰的《洞庭波》一期刊,至少在作者的論述中相當一致地標榜湘省的民族認同。
但當《新湖南》1903 年在東京出版後,楊毓麟就在同一年於《遊學譯編》上發表了〈滿州問題〉一篇,其中討論清廷、東三省遭受日本、俄國的威脅,以相當激烈的語氣喚醒讀者,指出此事對中國將來的發展之危害。這篇裡楊氏仍提倡「一省獨立則足以號令全國」的道理,但此理念以沒落為文章次等的主張。楊氏呼籲的關鍵不是湘省的自立,而是中國主權的保護:因為「夫中國主權,非滿州政府所私有也,國民之公主權,一家一姓不得私有之」,所以宣傳「吾國民...知死蹈死則可以獨立,可以與滿政府宣戰而保存主權」的道理,顯然地在《新湖南》仍刊印時已轉向以全中國(即清帝國)為範圍的論述,而其於《新湖南》所鼓吹的一種以省為核心的多元主權模式,因東三省的危機而簡化為中國單一的主權。
《新湖南》與〈滿州問題〉的主要共同點反而是對於觀眾的鼓動,也就恰好能反映華興會員周震鱗關於湘人當時於日本的活動,即楊氏等人撰文的主要用意就在於,鼓動年輕學生投入革命陣營,也就「從文化教育事業入手,興學辦報,製造輿論,盡情抨擊清朝政府的腐朽政治,特別著重揭露它喪權辱國的媚外政策,從而喚起全國人民的愛國革命思想。而且通過興學辦報,得以培養革命青年,作為革命運動的前驅。」[1]
然而,楊毓麟當主編的《洞庭波》呢?裴氏風認為其「在形象和措詞上...帶有更頑強的湖南味」,也恰好強而有力地表達在其核心的文章裡,即〈二十世紀之湖南〉。該文不僅以滿人或外國人為湘人之仇敵,甚至訴諸「還有...其他的漢人」威脅湖南,且強調湖南不僅作為省而已,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種族」(race)或「民族」(people),故彰顯「湖南分離主義仍在迅速茁壯」。不過,從內容和現實政局而論,《洞庭波》卻延續了周震鱗上述所描述的敘述策略而已,恰好接續《新湖南》的作風:〈二十世紀之湖南〉內容的前半的確如裴士鋒所說,訴諸他省的抨擊,指出湖南在新政運動為梁啟超等立憲派人物誘陷,但裴士鋒未討論的後半裡,以統一德國(而非是率領普魯士獨立!)之俾斯麦為筆名(即鐵郎)的陳家鼎,卻改口而重新號召湘省對天下的責任,而勸讀者迅速以「起義」、「外交」、「預備革命」等方略悔過湘軍的原罪,甚或主張放棄「省界」且依據「德美聯邦政體」 建國。[2] 總之,以全文來講,裴士鋒並未提出湖南獨立而對抗他省的主張,反而是訴諸一種聯省革命。

從時代背景而論,當時湘籍的激進份子準備參與萍瀏醴起事,而當劉道一等人離開日本參加起事後,陳家鼎等負責宣傳的作者乃致力於喚醒輿論上的支持,盡量抨擊革命派的對手,如清廷、立憲派、官紳等,以拉攏湘省「青年」加入該場革命運動。然而,到 1907 年 1 月,起事的情勢逐漸衰頹,而《洞庭波》似乎立即改名《漢幟》,發揚漢族(而非是省)為核心的宣傳符號,以〈論各省宜速響應湘贛革命軍〉等文勸他省革命派人接續起事。可見,無論是《洞庭波》或著《漢幟》,這兩個姊妹期刊各有其實際的目的,而不是渲染湖南民族主義或「狹隘的地方主義」之媒介而已。
基本上,湘人省籍認同在歷史上的影響力不用否認,也可以說它具有愛國或愛省主義的性質,甚至表面上反對清朝,然而,裴士鋒強調湘人時常與中國而處於對立的處境,又稱此為湘人最主要的認同觀,無論是在宏觀的歷史視野,還是以單獨文本為基礎的分析,實比較難成立。而這原因,並非因為中國民族主義更為真實,畢竟各種各樣的知識份子仍花了十分多的力氣,且透過不同的方式,才把民族認同從精英階層,逐漸推廣至所有居住於全體中國人民,而這種情形,即便在擁有國立教育體制的中共,也其實未變,顯露民族主義本身儘管外貌高昂,其本質乃頗為薄弱。
但也就是因為民族主義初期為參與全國文化(尤其科舉制度在此關鍵)的菁英所建構及喚醒,所以如同上述兩例顯示,像湖南「以天下為己任」的認同觀,始終為中國/天下此符號系統(且以大清帝國為實際存在、平時遭受他國壓迫的政治範圍)在塑造民族主義上匡定,致省籍認同間接也在宣傳中國的符號,也因此對他省之人士發揮影響。
在此不多討論語彙及知識層面,如何約束晚清省籍認同的想像及發展,但另外也可以從時代背景看出一些阻礙以省為對象的民族主義成為主流的因素:前往日本的留學生,其當初的確適合省籍意識的宣傳,畢竟其生活環境至此以己省為核心,故他省學生迅速回應《新湖南》、《新廣東》一類書,自己出版《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等具有省籍色彩的期刊。然而,經過這些新知識份子在陌生地的日本加入方興未艾的留學生社群,即一個勉強可以溝通且共享「清人」、「華人」等身份,再加「取締規則」、「拒俄義勇隊」等活動發生,且革命等思想越來越強力地被宣傳,該批主要由省籍界定的青年已經升為 – 或者被逼迫(參考「取締規則」事件或〈公致江蘇學會書〉一文中所顯露的高壓手段,如封殺、暴力等等)──全國性(national)的新知識分子。
總體而論,裴士鋒以嶄新的視角帶領讀者,解讀湖南在中國近現代史中不為人知的重要地位。以王夫之的思想貫穿全書,不僅介紹了一些較為少人知悉的事情,如介紹幾代湖南菁英間的王夫之信仰,及其對船山思想的各種詮釋,或是晚清湘省內華興會人士利用湖南的省籍意識來煽動支持者。除此之外,書中也對一些主流之外的歷史人物多有著墨,一般讀者熟悉的人物的梁啟超、孫文等人反倒成為配角,也啟發讀者重新思考原先認知的中國近代史的全貌與偏見。
儘管專業的歷史工作者或許會對《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有些惋惜,在某些湖南民族論述時似乎過度地牽強,對史料的解讀也可能有過度簡化的疑慮,但這並不影響作者以地域主義挑戰大一統民族主義的壯舉,這種對大一統民族主義的質疑態度與決心,正好提醒了我們在解讀歷史時應有的警覺與距離。
[1] 周震鱗,〈關於黃興、華興會和辛亥革命後的孫黃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 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1 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 年),頁 331-332。
[2] 鐵郎(陳家鼎),〈二十世紀之湖南〉,《洞庭波》,頁 136-137、147-149、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