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話有「老克勒」這個說法,指講究生活細節、且有一定閱歷和生活品味的老先生。他們戴鴨舌帽、穿牛津鞋、打領結,冬天戴格子圍巾,秋天穿風衣。喜歡悠悠的喝咖啡,喝紅茶要放檸檬,早餐喜食牛奶麥片。每一條皺紋、每一個欣慰的笑、每一步顫抖的行走都是外人難以想像的或不願去模擬的真事隱。
舅公被認為值得上老克勒這一稱號。
舅公家中原是絲綢大亨,少時的經歷像極巴金筆下《家》的故事:愛上表妹,家長卻為他娶了同樣鄉紳家庭出身、但破落在先的姑娘——大概是為了省幾個聘禮錢。二人婚後始終冷淡相對,新婦臉上少見笑容。
以土地為基礎的鄉紳式家庭在迅速的沒落,大少爺隨著兄長來到上海做洋行──大人笑說這就是「地主階級」的「買辦化」。
八一三松滬會戰打響後洋行倒閉,舊宅也被戰火所毀,全家逃到租界作難民。而當租界淪落成孤島,舅公依然沒有工作。
根據老人閒話,每天早晨他依然西裝筆挺的出門。在租界穿過他曾經最愛的沙利文咖啡館,從後門進、前門出,這樣還可以聞得一身咖啡香。隨後在復興公園撿一份西文報紙──已經買不起報紙了──坐在長椅上看一天。傍晚吹著口哨返家。
這份看似清閒和荒誕的少爺情懷背後,其實是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和世界崩塌的無所適從的茫然和恐慌。舅公其實是在報上找招工廣告,無奈當時洋行和外資企業紛紛撤離,西文的優勢不再。偏巧這是他唯一能做的工作。
沙利文咖啡館(Sullivan's Hot Chocolate),當時位於南京路。老闆姓沙利文,英文名則是熱巧克力,以英式紅茶、小壺現煮咖啡和西點出名。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麥德赫斯脫路(Medhurst Road, 今泰興路)交口上的另一家英式建築是它的分店,有電唱機,兩層的英式建築,樓下有火車卡座,樓上多是小圓檯,臨街落地長窗。餐檯上都鋪著綠白方格的桌布,風格清雅。
比較與衆不同的一點是,侍者有一半是白人,主要語言為英語,使得到沙利文咖啡館進餐飲茶成了一種象徵西化的身份標誌。
家中靠的是舅婆與祖母繡花養家。舅婆為了繡花而熬夜,結果染上了煙癮,每工作一小時就要抽煙提神,直到深更半夜。不久後,十多歲的祖母去日佔區的虹口的工廠當了童工;去虹口必須經過一座外白渡橋,在李安的電影《色戒》中有細緻的描繪:當時外白渡橋由日本士兵守衛,中國人若過此橋則必須向日軍鞠躬。為了避免向站在外白渡橋的日本兵鞠躬,年少的祖母堅持每天繞路,多走一個小時上班。
以後回憶起沙利文咖啡館,祖母總是帶幾分埋怨的心酸和幾分無奈;但也是那座咖啡館,給不知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貧困、戰爭和分崩離析的世界的那位年輕人,在每早咖啡館的杯碟輕響和慢聲細語中帶來些許的溫暖和希望吧。
關於舅公後來的故事,父親是這樣寫的:
外公後來在文革的第三年病死,「克勒」舅舅來上海辦喪事,盡管這時他自己也是在五七幹校養豬,不過走在上海街頭,一身打扮:短袖的府綢襯衫,下半截束在白色西裝短褲里,腳登一雙白黑間色的漏空風涼皮鞋,依然是「克勒」。
辦完了喪事,一起聊天,說自己兩個女兒穿得太土了,「以後把我在國外買的連衫裙給她們穿上,一起到南京路上走一走,肯定後要跟上一大批」——我的這兩個表妹在幼兒園時,我媽媽帶她們到照相館拍照想寄給她們的爸爸,後來照相館把兩人的合照放得比真人還大,放在櫥窗里做起了廣告。
外婆去世後,舅舅就很少回上海了。兩個表妹在中學畢業後都去了南方。我結婚的時候到了南方旅游,住在舅舅家,白天看著他西裝筆挺的出去上班,晚上聊天,古今中外,天南海北,興致極高。
奇怪的是,「克勒」舅舅到了晚年卻非常的懷舊,來信裡經常要講些儒家的警句,而原來的洋文味道倒是沒有了。更可惜的是,幾年前得了老年痴呆症,除了我舅媽、我媽媽和他自己的女兒外,其他人一概都不認識了。
那是二十世紀上海灘中無數掙扎的人生裡面的一個小小的註腳。
「過來之人津津樂道,道及自身的風流韻事,別家的鬼蜮伎倆――好一個不義而富且貴的大都會,營營擾擾顛倒晝夜。
豪奢潑辣刁鑽精乖的海派進化論者,以為軟紅十丈適者生存。上海這筆厚黑糊塗賬神鬼難清,詎料星移物換很快收拾殆盡,魂銷骨蝕龍藏虎臥的上海過去了,哪些本是活該的,哪些本不是活該的;誰說得中肯,中什麼肯,說中了肯又有誰聽?
因為,過去了,都過去了。」
上世紀 20 至 40 年代的上海所呈現出的那畸形的繁華,正如木心先生所說看似炫目,實則大夢千秋,只待戰爭與革命將其摧毀。各國租界形成的治外法權與本地大亨黑幫共參都市秩序,外憂內患市民慎諾生活謹守寸光陰。螺獅殼裡做道場,洋場沉淪蝴蝶夢。但上海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願意放棄、挑戰和改變傳統的人,並將他們的文化融匯貫通,成為一座兼具開放性和契約精神的都會。
哪怕命中註定會夭折,也還是值得紀念:那些杯盞中叫人依偎的味道,是二十世紀的苦難中一道美好的靈感乍現。
沙利文咖啡館初名為「沙利文糖果行(Sullivan's Fine Candies)」,沙利文自任經理。美國左翼記者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西行漫記》的作者)就是在那裡邂逅他的第一任妻子、時任美國領館秘書的海倫。南京路舊址於二十世紀 60 年代拆除,建為華東電管局大樓。
1922 年該商行被一美僑雷文(C. H. Ravan)接盤,英文名改稱 Bake-Fine Bakery,中文名照舊。
1925 年,該行吸納社會股份而改稱沙利文麵包餅乾糖果公司,並向美國俄亥俄州註冊,西文名為 Bakeries Co. Federal Inc. U.S.A,並在新閘路開設工廠,其麵包、餅乾、糖果、糕點享譽上海,以至於「沙利文」在老派滬語中常被作為糖果餅乾的代名詞。1949 年以後,該公司與馬寶山糖果餅乾公司等合併為上海益民食品四廠(後上海光明公司),是為上海糖果餅乾的主要生產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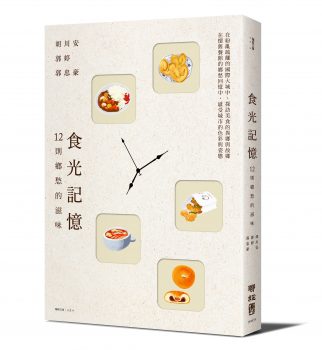
訴說上海、東京、紐約三地鄉愁料理的歷史文化。
從東京的麻婆豆腐、上海的栗子蛋糕,
再到紐約的珍珠奶茶,這是一場以食物為媒介的時空旅行,
戍守他鄉的移民最終透過鄉愁將家鄉美食扎根於異鄉,
用食物串起世代間關於移動、鄉愁和品味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