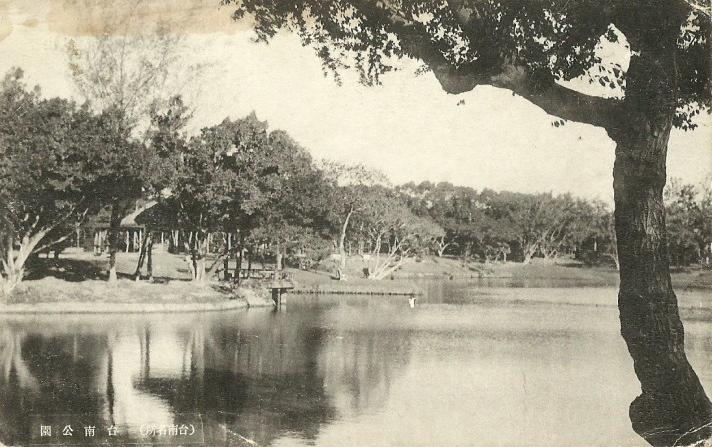2024 年 11 月 24 日,令臺灣人難忘的一天。不管是球員們衝進東京巨蛋球場中央,還是隊長陳傑憲胸口比出的手勢,或是繚繞在電視轉播的應援曲,每個人都可以舉出自己腦海中的經典畫面。奪冠後,圍繞著棒球的各式話題也持續延燒,而這篇文章想要談的,正是和棒球有關,卻又溢出球場的故事——是一場屬於臺灣人的比賽,但卻是比九局的球賽,打得更持久的延長賽。
中職元老球隊與背後的臺南幫
大概所有人都會同意,臺灣能走到 12 強的冠軍,這一步,背後是職棒成立 34 年以來的累積。而把場景拉回 1988 年,「職棒元年」開打的前兩年,熱愛棒球的飯店經營者洪騰勝,走進了臺南統一企業的董事會現場,發表了四十分鐘的短講,力邀辦公桌前的董事長吳修齊、總經理高清愿,組一支職業棒球隊,一起讓職業棒球聯盟成立。當時經營一個球隊一年預算大約是三千萬到四千萬,再扣掉推估的門票收入,每年仍要虧損二千萬左右,因此一開始,統一對於籌組職棒球隊的態度是拒絕的,「本公司對棒球無專長,亦無專人精研」,如此回覆洪騰勝。[1]
至今我們無法知道洪騰勝當年講了什麼,他沒有講稿留下,但遊說過程中,所強調組球隊的社會意義和企業形象提升,肯定起了作用,讓統一願意在教練和球員都沒有著落的零基礎下,以臺南市立棒球場為主要經營場地[2],投下一年數千萬的經費,開啟了後來大家都知道的南霸天、統一獅的故事,甚至成為中職唯一一支元老球隊,一經營就是 37 年。

其實扣掉無法計量的廣告效益,球隊的營運沒有一年能轉虧為盈,職業運動的投入如此,文化教育事業也是。類似統一球隊的故事,見諸於臺南的各角落,背後都有著同一批人的身影。
1950 年代,有感於當時的職業教育還未普及,工商界需要的基層人才不足,過往被認為是窮鄉僻壤的學甲,出現了一間「天仁工商」,是縣內的第一所職業學校;不過才 11 年後,以培育工業電子、機械、紡織、漁產製造等社會所需人才為目的的「南臺工業技藝專科學校」(今南臺科技大學),也接著在永康設立;成大人熟悉的「修齊大樓」,更是企業家首開捐款國立大學校舍之舉⋯⋯而在辦學之外,戒嚴時代,少數能為言論自由留下一小塊空間的報紙《自立晚報》,也出自同一批人的手筆。
起家之路
興學校、辦報紙,這些私部門跳出來適時扮演政府角色之舉,可說是臺南某種商業傳統的延續,而延續這份傳統的人,是一群被稱為「臺南幫」的企業家們。
統一企業、臺南紡織、太子建設、環球水泥⋯⋯今日耳熟能詳的大公司,都是臺南幫等人的事業體。他們的發跡與推動社會公益不是沒有來由,把時光拉回一百年前,1920 年代,當時臺灣還受日本殖民統治,幾位來自北門地區、鹽分地帶出身的囡仔工,陸陸續續遠離家鄉,前往當時繁華的「臺南市」,選擇落腳的地方,是昔日府城商業發展最蓬勃的地帶之一「本町」(今民權路二段)。
清代時叱吒一時的五條港區已淤塞,那時候進步的現代商行,都漸漸集中到本町,根據 1940 年的商業統計,光是三、四丁目(西門—永福路之間的民權路段)短短幾百公尺的距離,就開了 13 家布行,而整個臺南市的總數也才 17 家而已,可想其盛況。這些年僅十多歲的囡仔工,便一個牽一個,來到同鄉長輩開的布行當學徒,從掃地、洗廁所、接電話、倒茶水等基層工作做起,直到紛紛成立了自己的布行。
在艱困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布行生意暫歇,有的人到高雄岡山的日本海軍航空工廠工作,也有人到鄉下的鎮公所、農會擔任公職,以避軍隊徵召,等待和平到來。直到戰爭結束,重啟的布行搭上了政府的八年經建計劃,在美援支持下,臺灣的工業起步,「由商而工」的契機展開,於是,從布行到開紡織工廠,一路跨足其他產業,事業版圖也踏出了臺南,逐漸打出了「臺南幫」的名號。
從本町、民權路起家,臺南幫發跡的根據地,其實巧妙地連接了一段城市史,見證了臺南在有城牆的「府城」時代,同一條路上,商人們向海立生、掙脫外來文武官員勢力,長出自己力量、打造城市的過往。

臺南幫起家的民權路(本町)(Source: 國家文化記憶庫/CC BY3.0)
站起來的民間力量
臺南歷史上的「商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呢?許多歷史學家都注意到,清領初期,臺灣的土地——無論是鄭氏時期留下的「官田」,還是未經登記的土地,都被來臺的文武官員大量地占墾,土地的收益部分作為行政經費,部分則進了官員自己的口袋。尤其是土地生產出、能用來貿易的商品,特別是糖,大半都掌握在官員手中,而這樣的現象,也影響了民間商貿經濟的自由發展。
直到乾隆時期,國勢鼎盛,皇帝不再忌憚有戰功的武將,才開始約束文武官員,過往圈佔土地、在海上恣意對漁民收取規費的陋習,被逐一禁絕,進而使民間的商業活動發展起來,許多海商開始落籍臺灣,在地經營。
這些商人立足的起點,無獨有偶地,便是在今天的民權路一帶,昔日被稱為「五條港」的範圍。
在清廷只開放鹿耳門和廈門單一正口對渡的時期,本島許多貨物都是透過府城沿岸進出——商人們的船隻航行到府城,以中國內地的手工製品或日常用品,與沿岸港口的商行或直接設立的代理行,交換農產品。這些分佈在海岸線的商行,以水仙宮為信仰中心,創造了櫛次鱗比的街市。
從官員手中拿回商貿的主導權、被稱為「郊」的商人群體出現,我們可以看見,財富由官員手中流轉到了民間,成為了城市建設的一部分。商人們在水仙宮旁成立「三益堂」,作為商行間的議事公所,在這裡討論公共議題、立定公約,像是和各郊行捐募、收取出入貨件的規費,並且把這些錢投入地方公益,如:廟宇祭祀和修繕、港道疏浚、造橋鋪路⋯⋯,各角落都有商人的存在。
而在看得見的建設之外,他們也肩負起賑恤濟貧的「企業責任」。像是為單身年老的貧困者、生病無力就醫者,為這些人施醫送藥、資助生活費;在天災病疫發生時,發起募捐救濟;甚至除夕夜時,商請戲班,在水仙宮廟前通宵達旦演出「避債戲」,讓被欠債被催討的人,能在過年前有一處暫避風頭的地方。

眾志成城
走過清領初期文武官員的控制,財富累積到了民間,成為社會秩序維持的力量,雖然那些修建廟宇橋樑、賑恤濟貧的傳統,已經消失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但還有一項留下來的建設,見證了這段過往,那是府城的城門與城牆。
今天所熟悉的「府城」,包含了目前留存的大東門、大南門、小西門、兌悅門,以及臺南女中、成功大學旁的城牆殘跡,而在全盛時期,則是一個擁有 14 座城門、2 座外城、周長 7.5 公里左右內城(相當於 18 圈 400 米操場的長度)的城池,規模是清領時期全臺最大,不僅比周長第二的臺北府城、雲林舊城,多了 2 公里左右的長度,也比多數縣、廳級城市的城周足足多上一倍以上。至於 5.35 公尺的城牆高度,比三個一米八的成人加起來還要高,現在到樹林街的臺南女中旁,就可以體會當年人們仰望城牆的感受。
如此規模的城池,其實不全是官府的建設,背後也隱藏了來自民間的協力,以及一段驚心動魄的「三日築城牆」故事。
早在清中葉的乾隆年間,知府蔣元樞在重修年久磨損的城牆時,便留下了民間紳商的捐獻紀錄。但最多數府城人參與築城的,應還是海賊蔡牽的這一次。
那是嘉慶年間,被稱為「大出海」的蔡牽,已經在海上四處劫掠商船多年,許多從事兩岸貿易的郊商船戶,都曾在海上吃過虧,只能摸摸鼻子付錢贖回貨品。除了活躍在海上,蔡牽也幾度進犯滬尾(淡水)、鹿港、鹿耳門等港口,並且把當時的府治—臺灣府城列為目標。先是在嘉慶 9 年(1804)4 月,進攻鹿耳門的水師營署並焚毀,又燒商船、哨船,火光大到安平港口都看得見,隔年更一路攻到永康洲仔尾,這時候,蔡牽和府城的距離已經只剩六里了。
那一日,府治的官員們眼見事態緊急,城內存兵不足,「念非紳商無可與圖存者」——沒有仕紳商人的參與,大概無法保下城池,於是統領臺灣最高層級的「臺灣道」、地方官的知縣,召集了紳商等人,商討守禦對策。在民間的支持下,郊商不僅「助餉數萬金」,更一口氣募集了近萬人的義民,每個城門都有府縣的差役和義民共同巡守;為了守護住在大西門外、沒有城池保護,第一線面對海岸的居民,義民們更只用了短短三天的時間,以六千銀的費用,築起了一道從小西門到小北門的木城,將商貿重地的大西門一帶包圍起來,這段周長有 1200 丈的臨時性木城,便成為日後的西外城範圍。
蔡牽事件後三十多年,東外城的建造也同樣由民間紳商主動提出,「民捐民辦」地築了起來。這段將大東門屏蔽在內的外城,雖然只是以竹子為材料,但同樣設了三座城門,並且每天晚上都有附近的團練壯丁自主巡守。

殖民下的無形建設
水仙宮一帶的港口起家,因為兩岸貿易而獲得商業利益,而成為地方社會、城市建設主導者的商人們,到了日治時期,因為一統全島的殖民政府到來,而退到了第二線。綜觀日治時期的城市建設,是由總督府和臺南廳主導,但商人們的影響力不曾離開,只是轉換了形式,挹注在宗教活動和文化教育的推廣上。
歷經日治初期的動盪,到了大正年間,「三郊」的商人群體依舊維持著捐修廟宇的傳統:水仙宮、普濟殿、開基天后宮、法華寺、開基武廟、祀典武廟、開基玉皇宮等,都有留下三郊捐獻的碑記。
同時他們也在傳統信仰和殖民建設相遇時,試圖以自身的影響力,撐開傳統信仰的空間,今日所熟悉的「府城迎媽祖」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大正 15 年(1926)大天后宮的鎮南媽祖遶境,原本是固定在農曆三月十五、十六日舉行,但配合剛完工的臺南運河開通式,而將遶境提前到十四、十五日,並且媽祖的隊伍路線,也延伸到了運河的船溜(日文船渠、碼頭之意),作為祝賀運河開通[3],當天也因為媽祖的參與而熱鬧非凡,誕生了「臺南媽祖開運河」的俗諺。
過往這樣的大天后宮媽祖例祭,都是由廟董召集三郊、各保正商團共同協商,才能決定進香的時間,從迎媽祖的改期,可以看到改朝換代後,商人群體試圖在宗教信仰與殖民政策之間取得權衡的努力。
文化教育的推廣同樣也是努力目標。位於西門路的「大舞台」劇場,是全臺第一座臺灣人出資、以本島人為主要觀眾的劇場,由郊商謝群我、王雪農等人創建,不僅引進了當時被認為「不入流」的本土歌仔戲,也是以啟迪民智為宗旨的文化劇團「臺南共勵會」登台演出的地方。
大正15年(1926)大天后宮的鎮南媽祖遶境,特地繞路至臺南運河的開通式(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近代臺灣報刊資料庫)
接力:新臺南幫與新府城
仔細回顧這一路走來,如同一場三百年的延長賽。
先是掙脫了清領初期被來臺官員圈佔的土地,落籍本地的郊商出現,累積的資本成為建設府城的力量;殖民時期,本土的宗教和文化意識,依舊在統治的縫隙中撐出了空間,一面迎媽祖,一面賀運河開通。戰後的臺南幫們,走出了自己的事業版圖,同時延續著府城商人前輩們的傳統,將所得回饋予所在的城,於是我們得以看見,球員們驕傲地把球打擊出去的一瞬間。
「未來一直是現在進行式」詩人林梵寫過。或許人人都可以是新臺南幫,呵護著這座從前人手中接下的古城,並且走出屬於當代的風景。
[1]〈洪騰勝—不服輸的「球痴」〉;天下雜誌 110 期,1990 年 7 月 1 日,網址: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4463;〈職棒成軍點滴 秘書長推銷員最得意的傑作 洪騰勝說服統一公司成立職棒隊的小故事〉,《中國時報》,1989 年 12 月 05 日。
[2] 統一自1999年起認養臺南市立棒球場,是中職首支認養球場的球隊。
[3] 〈期日已近 運河之開通式 式後有神輿巡行旗行列 藝妓歌舞媽祖遶境其他〉,《臺南新報》,大正 15 年 04 月 22 日。
- 林玉茹(2019)。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62 2019.12[民 108.12],1-3+5-51。
- 謝國興,《台南幫:一個台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臺北:遠流,1999。
- 莊素玉,《無私的開創:高清愿傳》,天下文化,1999。
- 陳冠妃,《赤崁如何變為府城?臺南的城市空間與社會》,臺北:南天書局,2023。
- 蔡侑樺,《原臺灣府城城門及城垣殘蹟》,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創科,2017。
- 黃懷賢,〈臺灣傳統商業團體臺南三郊的轉變(1760-1940)〉,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