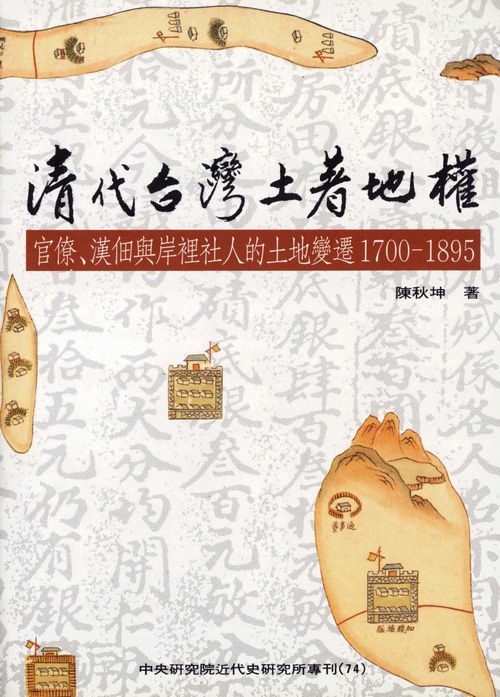2016 年 8 月 1 日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接見原住民代表,其中也包含屬於平埔族群範疇的西拉雅、馬卡道、巴宰等族。蔡總統正式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道歉的全文有段話是這樣陳述:
臺灣這塊土地,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這些人原本過著自己的生活,有著自己的語言、文化、習俗、土地、主權。然後,在未經他們同意之下,這塊土地 上來了另外一群人。歷史的發展是,後來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成為異鄉人,成為非主流,成為邊緣。[1]

這段話傳達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無論是高山族或是平埔族,在歷史上都曾面臨大量漢人移墾競逐,漸而喪失土地,走向弱化。那麼,原住民各族如何流失土地和自我權利,便成為 1980 年代原住民運動以來,研究者競相回答的命題。因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的作者陳秋坤教授,就以中臺灣巴宰族──岸裡社群為例,告訴我們一段岸裡社熟番的土地經驗,究竟他們如何接受土地私有權、商品貨幣經濟如何滲透到部落,以及屬於部落獵場的土地後來如何流入漢人銀主手中?
在開始介紹本書前,我必須先講一個關於岸裡社的故事。
1935 年 4 月 21 日清晨 6 時,「轟、轟」的幾聲巨響,一場發生在中臺灣豐原一帶的地震,讓當時最後一任岸裡社總通事潘永安的宅第,崩塌損壞。在斷垣殘壁中,偶然間發現了一批乾隆年間關於社務的文書。這批文書後來被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學生張耀焜用來撰寫學士論文,並在 1939 年論文完成後捐贈給帝大圖書館,此後便典藏於臺大圖書館。這就是聞名於世「岸裡文書」出土的始末。
那麼,岸裡社的土地經驗是如何展開的?原居於大甲溪北岸后里臺地的岸裡社,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歸化清廷後獲得官府賞賜大甲溪南岸廣闊的土地。雍正十年(1732)大甲西社事件後,岸裡社逐漸將搬遷至南岸,建立起新部落。之後,這些岸裡社人不斷以「官府蒙賞埔地」作為理由,宣稱他們在大甲溪南岸的地權。大甲西社事件後,岸裡通事張達京與土目敦仔等人,共同訂立契約,協議割讓番地換取漢人修圳之水權,又稱為「割地換水」。
在張達京的牽線下,岸裡社人開始引入水利灌溉農田的方式。乾隆初年,岸裡社的田業,開始從原本部落共同管理轉向個人私有。按照部落傳統的習慣,土地名義的領有是來自社主,後來土目敦仔(又稱潘敦)在接受總社主請託後,獲得實際經營社地的權力。
敦仔將社地分為兩類,一為公共社課地,以員寶庄為中心,每年約收取 1200 石公租;另一為社番私口田業,按照男丁婦口平均,除擔任部落公職的番人可分得土地較多外,一般社番平均可分得兩甲以下的土地。至此,岸裡社人從原本狩獵採食,正式走向定居農耕。
如果社人們能夠就此平靜墾耕過日,這片屬於社人漁獵天堂的家園,或能夠有所存續。偏偏有如過江之鯽的漢人們,藉由每年向番社繳納微薄的定額租,開始承耕土地。熟番們在租佃過程中接受漢人既有「一田二主」的觀念,致使土地所有權分化成為業主(收租)權、田主(管理)權。
清代的土地所有人被稱為「業戶或大租戶」,這些人控制許多沒有開墾的荒埔,但通常沒有意願或氣力從事實際開墾活動。所以需招人前來承墾,這些被招來的開墾人(又稱為小租戶),面對的是缺乏水源、土壤貧瘠的荒埔,常需花費較高的成本開墾。這些業戶們為了提高開墾人們的承墾意願,只能收取微薄或較低的固定租金,並保證不隨意更換承墾者。
然而,這些承墾者往往在取得土地後,開始經營類似「二房東」的生意,把土地再轉讓給他人耕作,約定租金為固定比例的收穫量。因此,當後來土地收穫因水利興修日益增加時,小租戶們反而能租金增加,嚐到土地收益增加的甜美果實,但收取固定租額的大租戶,只能乾瞪眼的繼續收取固定租額,也不能隨意提高租額或將土地轉佃他者。
這種「一田二主」的開墾方式,常見於清代台灣移墾社會,很多平埔原住民因給墾埔地於漢佃,而搖身一變成為番頭家(番業戶)。「番產漢佃」的形式,如能持續存在,所繳納的租榖或也能夠提供社人足夠生活所需的糧食。
偏偏事與願違,本書告訴我們,隨著十八世紀以來臺中平原水利設施的日益完備、田地生產力逐步提升。在這種情況下,一田二主的租佃形式,讓番業主只能收取定額的大租,而無法分享田產增加的獲益,同時也讓田底權(佃權)價值上漲,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大租權賤、小租價貴」的地權結構。伴隨著貨幣經濟進入部落,漸次影響社人的生活型態。番業主開始向漢佃借貸、抵押土地借款。少數富有佃人開始轉以「銀主」身分,自行管收租榖。原本番業漢佃的關係,形成番典主、漢銀主的角色置換。
日益貧困的岸裡社人不斷將私有土地抵押典借給漢人,可是在嘉慶初年漢番間的典借關係發生變化。平埔原住民向漢人典借銀兩的年利率從原本 3、4 分降為 2 分,表面上是讓無力償還利息的社人,能夠藉此喘息,但以此的代價卻是土地抵押的期限被延長至 7 到 10 年不等,等於變相成為長期典押土地貸款的情況。熟番的田業長期被漢人管收後,卻往往因無力償還借貸,番地最終流入漢人銀主之手。
不只是一般私有社地因「番人」的典借而流入漢人之手,屬於番社公口糧租(部落公租)方面,也因支應龐大的社務開銷、社職人員薪餉,再加上光緒十一年(1885)劉銘傳的番政改革,原本免交給官方正供賦稅的番大租,卻被迫進行「減四留六」,即大租額減低 4 成,但改由小租戶繳納正供給官方。此舉使得無多的公租,再減 4 成後,已所剩無幾。熟番社只能有向貧困、弱化的道路。

然而,十八世紀以來在番社頻繁發生土地交易買賣、典讓,反映社人對於田園產權貨幣化概念的生成,可是卻也造成社人土地家園的流失,甚至引發許多與漢佃的糾紛。面對此現狀,部落的頭人們並不是片面承受,而是試圖尋求官僚勢力庇護。
可惜此舉對番社而言,無疑是引狼入室。清廷雖然基於治理考量對熟番採取保護政策,可惜未有效執行,形同具文。無論是漢通事或理番同知的成立,都為番社帶來諸多財政、勞役支出的苛擾。也間接引發岸裡社的頭人們,為了提高攤派公費支出,引發部落內部的鬥爭,最終造成嘉慶二年(1797)岸裡部落體制走向官僚化。
來自官方衙役、鄉保、社差,不僅無力調停、解決業佃糾紛,反是再三勒索番社,加重部落公租支應的負擔,甚至包攬番社田業,自己擔任「二地主」。而本書作者指出此類「國家權威對部落滲透」的行為,反而是造成熟番部落弱化的另一要因。
當熟番業主無論是被迫或自願捲入租佃生產體制後,他們的身分就已轉成租佃業主,但因只握有收租權,不僅無法分享田地生產增加的成果,也無法以部落權威的身分要求漢佃履行納租義務。面對此一困境,部落裡的人們只能仰賴官僚力量的介入,可是依然無法有效解決。最終導致十九世紀以來,岸裡社人們番產不斷流失的一惡化局面。大部分番業主成為漢人社會經濟體制下的邊緣階層,甚至以選擇走向遷徙埔里盆地或改宗基督教,來躲避岸裡社貧困化危機。
讀完這本《清代臺灣土著地權》,我們再回頭思索蔡英文總統道歉文中的那段話:「歷史的發展是,後來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面對歷史上原住民的顛沛流離,並不是因為漢人在土地權利取代原住民而已,也與我們一般認知簡單歸究於「漢人狡詐拐騙、熟番純真、質樸」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岸裡社的例子,展現平埔部落命運發展至此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平埔族群融入漢人貨幣經濟體系與官僚體制時的困境所致。
然而,平埔原住民們在面對捲入貨幣經濟苦果之際,並非無助的被迫承受。他們依然具「能動性」選擇不同的策略企圖頑強抵抗,只是面對漢人洪流與官僚體制的箝制,這番努力終究徒勞無功,最終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而族群身分、部落文化也漸漸隱藏在「漢人」主流社會之中。
(作者為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