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九年(1670),來自江西的官宦家庭子弟黃六鴻即將擔任山東郯城知縣,他要經手的地方有許多問題正等待解決。
位於山東的郯城縣已經歷過清初的戰亂和盜匪侵擊,而兩年前的地震使得這個原已窮困的地區生活更加困苦,黃六鴻在其著作《福惠全書》中屢次提到當地居民在生活艱困下出現的社會與道德問題,人們往往為了生存付出沉重代價,暴力、犯罪層出不窮,也處處充滿難以解決的「疑獄」。此外,市鎮與鄉村也存在著緊張關係,「城裡人」的詐騙使得農民畏懼城市。
1672 年 1 月,休庭期間的黃六鴻收到郯城縣歸昌社任某的喊控。任某控告他的鄰居高某與妻子王氏通姦並殺害她。雪地上,身著藍衫白褲與紅色睡鞋的王氏被棄屍林間,直至清晨才被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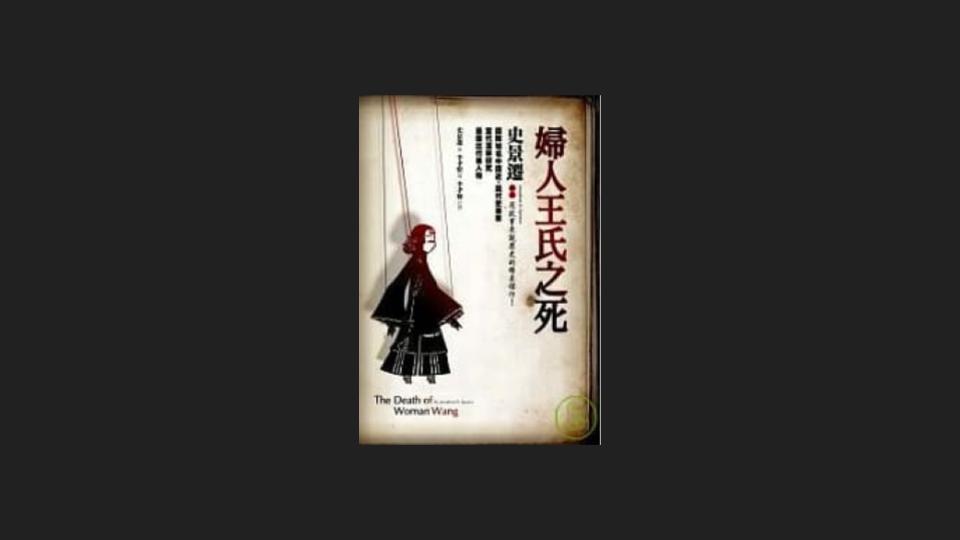
《婦人王氏之死》的作者史景遷在閱讀《郯城縣志》時發現這則史料,並配合黃六鴻在此擔任知縣時的著作《福惠全書》與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將案件與當時郯城縣的情況結合,使一件發生於三百年前的兇案有了敘事性的陳述與新的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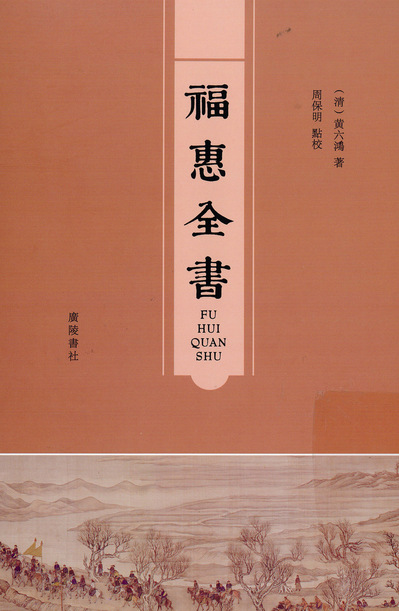
郯城縣的生活環境和價值觀使得人們不得不遵守舊有的、天經地義般的陳規生活著。士紳在此地是不興旺的,而戰亂又使知識人口減少到幾乎消失的地步。
然而,人民的價值觀仍建立在這些士人對道德的認識上,而士人在地方志裡的書寫則透露了「官方視角」對地方政治與理想社會的想像。因為階層、財產、性別而產生的衝突在此地一如其他地區不停上演,郯城縣只是彈丸之地,然其情況亦是中國北方社會的縮影。居民的離散與逃亡、人與人之間的不忠,這些插曲只是更加突顯郯城縣民的困境,選擇王氏案件為題材顯示了作者對結合探討清代地方史、婚姻乃至各種性犯罪的期望。
《婦人王氏之死》中,史景遷援引的另一份史料《聊齋誌異》,其實也是當時山東人民心靈世界的再現,《聊齋》裡的神仙鬼怪不外乎是根基於人性孕育而生。十七世紀末的中國北部社會,其樣貌雖然各有差異,但從《郯城縣志》、《福惠全書》和《聊齋誌異》的記錄裡,我們能窺見清初底層人民不為人知的生活,他們的欲望、困境和對美滿生活的追尋,從這個面向來看,如果僅把《聊齋》當成虛構的神怪小說可能太低估它的價值。
對於真實社會,《聊齋》以寓言甚或傳聞的寫作將當時人的生活記錄下來,不僅止於神仙鬼怪,也充滿人對困境的堅忍、欲望與道德的掙扎、法外正義和各種誓言,這些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其實都來自蒲松齡在家鄉的所見所聞乃至親身經歷。其中,夢境在《聊齋》中佔有一定地位,因為夢可以是荒誕無據的,然而夢境本身常是人對生活經驗的反映,愛恨情仇都可能在夢境中化為真實。
對於夢境的記錄,《聊齋》中即有蒲松齡自己的親身經驗與許多「南柯一夢」形式的故事,反映出生活中的不滿和欲求在夢境中獲得實踐。生活經驗、鄉里傳說或是對於社會現象的諷刺,都可能在《聊齋》中成為奇幻故事的想像泉源,這些故事多少顯示底層人民生活上的艱困,他們的選擇往往也是迫於現況。蒲松齡的故事有時讓主人翁成功逃離地獄般的生活,滿足了人們渴望的生命歷程,有時又藉由人物的背叛(而多數時候也是身不由己)與報應作為對現況的嘲諷。
蒲松齡用看似不可能的生活經驗書寫道德倫理對於人的束縛,而這些束縛往往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劇,至死不渝的誓言有時也會化為背叛。正義在《聊齋》中經常不站在法律的一邊,基於人性立下的誓約或是對傷害的報復才是正義的實踐場域。另外,《聊齋誌異》中有很多運用智慧向命運反抗的女性,或是用魔法向「壞人」(可能是侵略的盜賊或背信忘義的丈夫)報仇的仙姑道女,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沒有神奇魔法的郯城女人在面臨困境時,她們通常付出一切卻以無所回饋,甚至得用死亡實踐其生命意義。
《郯城縣志》中節烈婦女的面貌幾乎和地方志裡的記錄無所差異,也同樣地模糊不清,這些女人都在士人的書寫下成就其生命價值,無論是撫育兒女或是以各種方式殉身的寡婦,她們成就的生命意義在當時社會架構裡是正面美好的。另一方面,既有價值觀也同樣對不符合道德規範的女人作出定義,而《婦人王氏之死》的主角──姓名不得而知的婦人王氏──就是個無法容身社會規範中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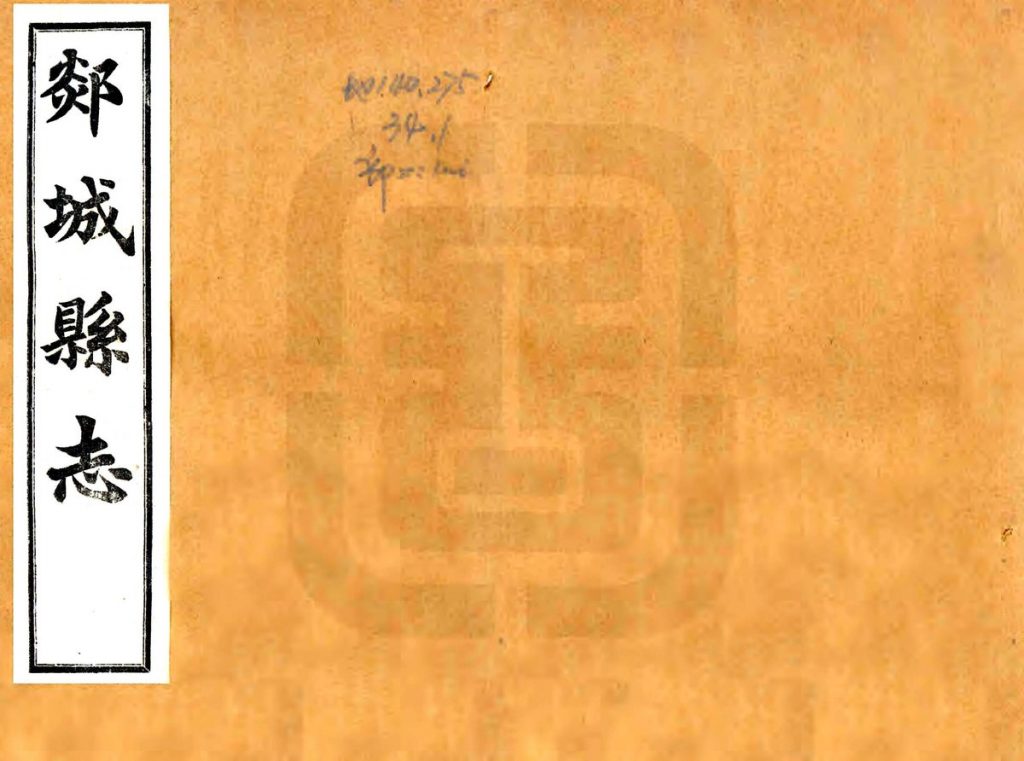
回到 1672 年任氏父子的指控,黃六鴻不得不親自調查這件疑點重重的謀殺案。從任某的房舍、鄰居的供詞,到王氏棄屍的地點,黃六鴻逐漸在重構案情的過程中找到真相。驗屍結果顯示凶手殺死王氏的方法,而兩造對王氏在夜晚「消失」的不一供詞則在黃六鴻敏銳的觀察中得到答案──他發現王氏的鞋底並沒有外出痕跡──任某夜半目擊「高某劫走王氏」的供詞出現了嚴重漏洞。
為了使真兇現身,黃六鴻利用人民對城隍的畏懼來逼使任某認罪,而任某的反應證明他在調查後的推斷是正確的。經過四天左右的審查,黃六鴻在眾人面前陳述凶案始末,這使任某對高某的報復導向致命結果,不過卻因任父年老加上家中沒有其他子嗣而未遭到死刑,然而王氏的死亡仍被黃六鴻視為罪有應得。王氏的喪禮與墓地費用則由高某負擔,藉此懲罰他在廟裡打了任某兩巴掌,但如果沒有發生命案,高某可能會因為動粗而挨上二十大板。
王氏的逃跑揭露了清初山東居民的命運:人們迫於生存而必須違反道德,而這些抉擇往往也釀成自身悲劇,而王氏的死亡則終結了現世的痛苦與生命中的背叛。然而,在常民的心靈世界中,她的靈魂卻可能對郯城縣民造成持續極久的恐懼。王氏之死說明當時人對於報復、殺戮與正義相連的價值觀,王氏之死並沒有洗去其行為造成的「不潔」,人們認為她會在死後騷擾村里即是基於這個原因,「女鬼」的報復超越其現世對道德的破壞。
最後,從《郯城縣志》可知,士人建構的道德世界能在人民身上產生影響,但也因現實環境的困頓造成無數的背叛與暴力,而《福惠全書》中各類刑案的記錄、刑求方式、驗屍規範,正顯示黃六鴻在郯城遭遇的各種難題,他的任官生涯一點也不輕鬆,充滿無法視而不見的疾苦和人類相殘的經驗。黃六鴻的筆調是沉重的,他必須進入人民的心靈才能解決社會問題,但仍然無法結束郯城縣的長久困境。

過去三十多年來,美國學者在中國史研究的領域中,表現最為突出的要算是中國近代社會史了。而這個研究領域的主要課題,包括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民眾叛亂、民間宗教、基層組織及地方社會。
《婦人王氏之死》在類別上可以歸到地方社會這一項,但在風格與取徑上卻與其他的研究大不相同。史景遷一向偏重在文學性的故事,但透過有別於一般歷史論著的敘述技巧,和學術涵養所訓練的敏銳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後,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時空和人物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