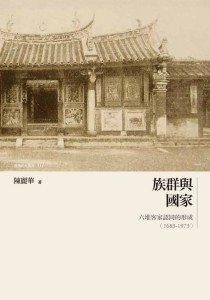什麼是客家?問起這個問題時,大家腦中可能浮現硬頸精神、克勤克儉、客家小炒、客家粄條、擂茶等各種特性或元素,只是,這些乃是歷史演變後的結果,我們只是參與了或正在參與這個歷史形塑的過程。因此,應該要問的是,在甚麼樣的背景下,是甚麼樣的力量引領了這個過程。換言之,客家如何形成,或者在甚麼情境下開始,這個提問,應是更好的問法。
當然,不能以現在對於客家的論述或印象套用於過去,以「客」此詞而言,兩百年前的「客」和今日的「客」涵蓋不同概念,也非指涉相同範圍的人群,更遑論紛雜多元難以捉摸的認同問題。那麼,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林正慧和陳麗華分別用兩種不同的視角提供了一些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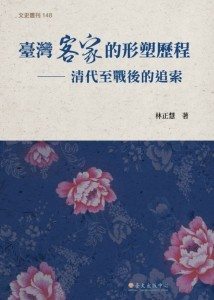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的林正慧博士,甫踏入研究以來,即關注臺灣客家族群之議題,在本書《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出版之前,已出版根據碩士論文改編之《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
這次她跳脫地域,從國家分類族群的角度談論臺灣客家之塑造,旨在說明「方言」是確認族群認同的顯性標誌,然而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混亂了以方言為中心的族群分類,進而影響了族群的自我認識。
這樣的結果,若追溯起源頭,必須回到明清年間的華南一帶。
嘉慶十三年(1808)年,身處「邊緣客域」的文人徐旭曾,在當時廣東土客械鬥的背景下,發表了一篇〈豐湖雜記〉,擬構出一幅以方言為界線的客人分布圖。開港通商後,外國傳教士以 Hakkas 稱述客方言族群的用法也影響客方言族群,促使「客家」變成自稱。與此同時,廣東也於同治年間發生土客大械鬥,其中「客家」也用以指涉客方言族群,這些便成為同治六年(1867)林達泉〈客說〉的論述資源和形成背景。
不同於徐旭曾,處於「中心客區」的林達泉完成橫跨多省的「客家論述」,促使「邊緣客域」論述回流到了「中心客區」。其中基督教巴色會(Basel Mission)對客家的溯源,以及「中心客區」中其他的客人論述,不僅促使林達泉接受了「邊緣客域」論述中的客家稱謂,並豐富了客家論述,進而有利於凝聚客家人的認同,甚而有之,形成客家意識進而其他地方傳播。
到了 1930 年代,客家不僅在進化論下被模塑成優良特性之種族,加以民初以來客家在黨政軍方面漸具實力,已可掌握我族論述的話語權,在一切水到渠成之勢之時,1933 年羅香林出版了《客家研究導論》,將原本備受排擠與鄙視的客家族群請進了學術廟堂。
相對於華南客人論述之發展,清初臺灣文獻雖然已經出現「客」的書寫,但卻有不同發展。以往研究大多從「閩主粵客」之土地承租關係,或者閩粵分別的科學名額分配制等官方劃定的界線,闡述客家認同的形成,但這忽略了方言問題,亦即:雖然「粵人」和「客人」代表的人群意涵可能大部分重疊,不過,由於南部有大量的粵籍福佬,因此「粵」和「客」並不等同於客方言族群。
那麼該如何解決此問題?作者認為,方言是認同的標準。她先透過嘉慶到道光年間分類械鬥之分析,說明粵人有逐漸聚攏之勢,重要的是,粵省福佬潮州人與閩人之結合較為少見,反而閩省汀人附粵之現象頗為顯著。
在這樣的觀察下,她分析各類「客」移民之發展,其中閩籍汀州客,以跨省方言認同出現「汀附粵」之情況,相較於華南以汀州視為客家祖源地,臺灣由於有閩主粵客之行政框架,加以汀、粵都是外來者,其中粵又多於汀,因此汀州人僅能因應時勢選擇依附。位處客話和閩南交界地帶的閩籍漳州客,因語言差異性大,加以「閩主粵客」之框架,故少出現「漳附粵」。
而處於雙語言交界地帶的粵籍潮州客和粵籍海陸豐客,皆因應語言和拓墾環境之差異產生不同的人群結合。相較於語言歧異較大的上述客群,粵籍的潮惠嘉客,由於方言互通,加以開墾環境之惡劣,促使其形成凝聚力強的移民社會。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後,或許受到華南和西人的論述,以方言為標準調查當時的客家,並賦與「哈喀」、「喀家」或「客家」等稱謂,當時紛雜多陳的客家論述,伴隨舊慣調查之展開而定著,其根據清朝閩粵分籍之概念,並以近代人種學給予「廣東人」稱謂。結果,原本以方言分類的客家,遂與省籍界線疊合,影響所及,其一,日後以「粵即客」、「閩即福」之標準進行戶口調查、國勢調查和鄉貫調查時,無論是以方言或祖籍為分類基準,均促使溢出此定義之外的閩籍客方言人群和粵籍福佬落入身分選擇的窘境,然而,也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已有人自稱為「廣東人」或「客人」。
其二,相對於當時仍強調我群為漢人之華南客方言族群,日本殖民者已將臺灣客方言人確定為漢人,並將「客」稱之緣由,定論為閩粵移民來臺先後之不同,於是「閩主粵客」成為臺灣「客」稱之主要說法,影響直至戰後。此外,在福佬人優勢之情況,加以殖民者壓迫下,客家人陷入了雙重疏離的狀況。
戰後,不僅國民政府承襲了日本時代的分類基準,原本中國的客家人也隨政府遷臺,與本土客家結合,繼承了華南「中心客區」的位置,並參與中華民族的建構工程。其以羅香林的客家論述為中心,嫁接起臺灣客家的源流,不同於清朝到日治以方言為中心的族群意識,形塑出具中原文化的客家意識,其中包括《苗友》、《中原》雜誌之創刊,以及同鄉會之創設,均參與了這次的國族建構運動。
雖然臺灣客家因此提升了地位,不過,這卻使其過往歷史只能任由負面評價,夾處於福佬人和中國客家之間的臺灣客家,因此讓自己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直到 1980 年代以降之民主化浪潮下,本土族群的反抗意識甦醒後,才終於選擇與中原客家論述道別。
由上文觀之,林正慧嘗試以國家分類族群的視角,配合方言為認同基準之出發點,提供了影響客家認同的另一種可能。這樣的國家介入甚至擾亂了後來客家的記憶,使得族譜上出現「福建省潮州府饒平縣」或「福建省漳州府饒平縣」(作者按:饒平縣應該是位於廣東省)等記憶錯覺的狀況,,而此處無疑是書中最精彩的一段論述。
文末,作者留下了一個伏筆,足供後來者繼續研究,相對於依附中原客家論述的《苗友》和《中原》,1970 年代起六堆地區的客家論述卻強調本土客家的特徵,究竟為何如此,實是值得探究之處。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陳麗華博士,亦長期關注臺灣客家議題,近年從客家塑造問題轉而深入探討客家認同之問題,《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一書乃是以六堆客家為分析個案,勾勒出清代到戰後其認同的轉變。
六堆位於現今高雄、屏東境內,乃清代以客家族群為中心的自衛組織,自清代六堆地域社會形成以來,其透過嘗會、忠義亭祭祀、語言和風俗文化聚合,並以粵籍和義民身分表達群體認同。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不僅以廣東人之種族觀念,重新分類了客家族群,並透過調整行政區域、安撫地方仕紳、改變祭祀對象、消滅大租權,消解原有的閩主粵客承租關係,最後將六堆地域社會整合進國家。
之後,從傳統邁向近代化中,六堆呈現幾個近代化的面向:教育上,孕育出新式菁英,得以進入城市浸染近代社會的變化;經濟上,將六堆社會引領入資本主義的浪潮中;宗族上,追溯傳統並參與同姓仕紳階層合族組織;信仰上,忠義亭功能弱化,並演變成祭祀明治天皇的場所,代之而起的是內埔天后宮和昌黎祠,促使當地居民重新演繹了六堆的認同。
日治後期,又有一些變化。六堆經濟實力增強後,培養出新興的中產階層,在地的他們建祠堂、修族譜,並且強調地方廟宇與華南一代悠久之傳統聯繫,以及其與日本帝國之間的關係,結果不僅創造出新的地方文化,並且以運動會取代傳統拜祭活動,表達包含地方意識和帝國認同的六堆地域認同。至於不在地的那些人也透過同鄉會等組織強化客家人的同種族意識。
然而,進入戰時體制後,由於皇民化運動之推行,六堆地域認同被壓抑。到了戰後,在中華民族的建構工程中,六堆透過運動會和聖火形式,以及忠義亭改稱忠義祠之轉變,喚起地方民眾對於新國家的熱情。那些日治時期的菁英持續改造地方文化,並透過強調與中原客家血統之關聯,將地方意識融合進新的國家意識中,進而得以延續其地域認同。
陳麗華不僅以其歷史學訓練,建構出六堆地域社會的歷史,並以人類學訓練,從時代背景中分析田野經驗,以拼湊出其認同演變之圖像,給予讀者另一種觀看客家的視角。然而,談論認同並非易事,且認同是甚麼認同,各種認同之間是否相互影響,又,認同之中是否有階層、性別、年齡或教育程度的差異,在在都是不好回答的問題。書中雖然運用了一手文獻,並走訪鄉間,以人類學訓練觀察認同之形成,但是因史料之限制,以及認同定義不明,導致論述有些混亂。
首先,就史料來說,例如第二章提到,清代六堆客家地域社會的客語群體,以籍貫和義民身分表達群體認同,而祭祀中心忠義亭,乃是表達語群意識的場所。但是,文中僅描述忠義亭之祭拜過程,並無充足一手史料印證六堆客家如何透過籍貫、義民或祭拜表達認同。
到了日治時期,作者又指出,「地方領袖階層熱心參與後堆內埔天后宮及昌黎祠的重修活動,便是這一認同的再次演繹」,然而,從文中引用證據來看,僅是一段重修過程,讓人無法理解「認同」要如何「再次演繹」,如此論述過程,書中並不少見,反而讓人感覺這樣的論述需要一些想像力。
整體而言,雖然為了適切論述認同之演變,作者用心描述六堆社會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認同的各種因素,但由於史料之缺乏,導致相較於認同議題,本書其實比較偏向六堆地域社會史的研究。

其次,就認同而言,從題目「六堆客家認同」看來,會有兩種談法:一是「具有六堆特色的客家認同」,二是「六堆客家人對六堆的認同」。從文中論述看來,作者比較六堆客家與其他地方客家,讓讀者了解到六堆客家之特色,應屬於前者。不過,當談及後者時,卻有語言、國家、祖籍等各種認同,其都涵蓋於地域認同,或許這些認同相互影響,惟由於無一主軸清楚地說明其形成,導致閱讀起來不免有些混亂。
以第五章為例,作者談到運動會取代傳統拜祭,成為貫穿地方意識與帝國認同的主要活動,乃表達六堆地域認同延續之主要手段,接著又說,在外地的六堆客家參與了都市等地客家人傳播客家自覺意識之潮流。換言之,這段的客家認同不僅包含了帝國認同和地方意識,同時也被廣泛的客家自覺意識影響。雖然這同時也顯示出影響認同的多種因素,但不禁讓人想問,究竟是要談論六堆客家的什麼認同?還是,這樣的認同係其特色?
從兩書皆試圖談論影響認同的可能性看來,證明「認同」乃是族群史的重要議題之一。近幾年,施添福在《全球客家研究》連續發表了數篇文章,清楚地用本貫主義和方言主義勾勒出通用名詞「客家」如何變成專有名詞的客家,在官方史料的輔助下,可以了解國家對於一個族群分類的影響。
只是,客家人如何自稱客家,乃至其認同之形成,是一個可以持續追問的問題,目前其正持續關注此課題,讀者可以拭目以待。

文末,用一個例子結束這篇文章,如果各位到具有代表性的客家庄時,或許會體驗客家傳統飲食擂茶的活動,擂茶的同時,你可能不知道自己也正在參與中華民族的建構工程。細究起來,「客家傳統飲食擂茶」這樣的認知沒有錯,但不夠精準。維基百科說「客家擂茶隨著客家移民傳入台灣的客家地區」,只不過,到底是何時的客家移民,並未明言。
研究者黃智絹發現,擂茶很有可能是戰後隨著外省客家人進入臺灣,在地化後,從鹹口味成為甜口味的臺灣客家擂茶,商業化後,從家庭飲食變成大眾消費飲食。換言之,這是一種被外省客家傳統嫁接於臺灣客家的飲食文化,透過政府的宣傳和廣告,讓我們以為這是臺灣客家的傳統飲食。這一段過程展現了國家力量的影響,其創造出來的符號,透過各種管道,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常識。
據此,光以擂茶一例,便牽動出影響臺灣客家文化之部分因緣,那麼具有百年以上歷史,並擁有我們以為的各種客家常識之臺灣客家,其形成過程又何嘗不是比此更加地複雜呢?
-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一):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全球客家研究》,第 1 期(臺北,11),頁 1-56。
-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第 2 期(臺北,5),頁 1-114。
-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第 3 期(臺北,11),頁 1-110。
- 黃智絹,〈遠渡重洋的美食:臺灣客家擂茶的流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