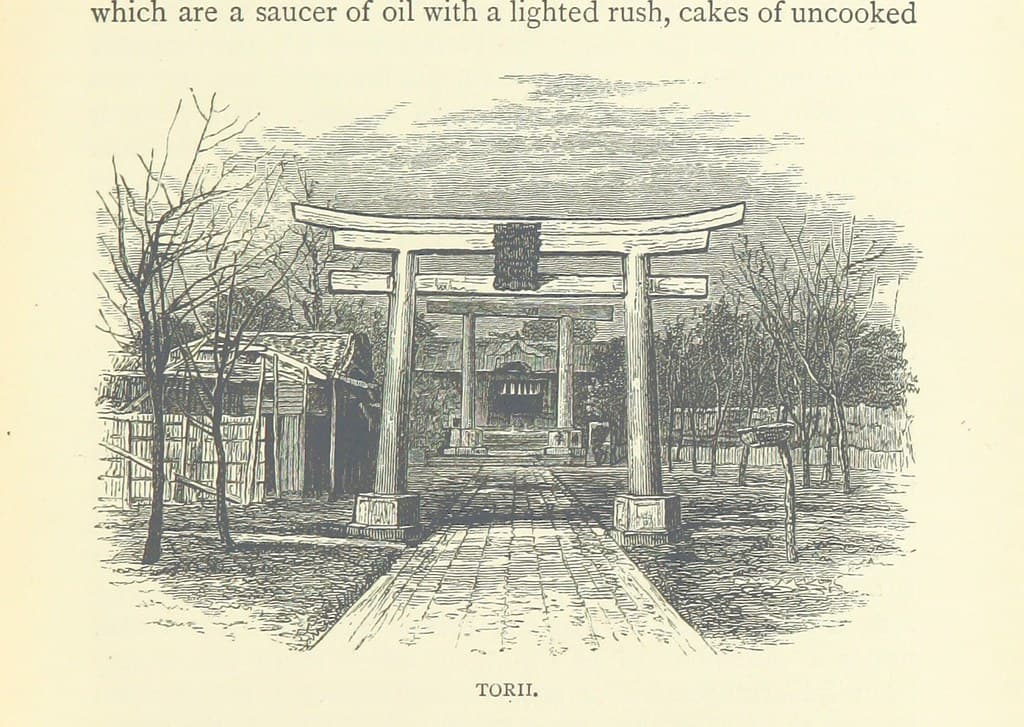不同階層的民眾之間,過著極為不平等的生活,而男性與女性的地位與處境也有相當懸殊的差距。社會上的性別歧視嚴重到會讓你忍無可忍,而且大家對此都心知肚明。哈里法克侯爵在寫給他女兒的家書中表明:
首先妳必須明白,男性與女性有著本質上的差異。為了整個社會的福祉著想,身為立定法律制度的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理性、理智……男性與女性的脾性有所不同,因此我們的缺陷與瑕疵終究能互相補償。妳們女性希望借助男性的理智,來告訴妳們該如何行事;妳們也希望男性能用強健的筋骨與意志來保護妳們。而男性則希望借助女性溫和的氣質,來舒緩娛樂我們的心靈。
上述這段話跟厭女情結一點關係也沒有。其實有很多男人深愛著自己的妻子(妻子也同樣深愛丈夫),但男人仍然會責罵、毆打自己的太太,他們深信自己的出發點是為了老婆好。另外,當時也不是所有女人都認為兩性平等是值得追求,甚至有可能實踐的一件事。很多女性認為自己就是男性的附屬品,而且相信這就是世界的真理。連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也秉持著這種想法。
舉例來說,身為拉丁文詩歌和散文譯者的露西・哈欽森(Lucy Hutchinson),她自己也是一位詩人,而且也曾替丈夫跟自己寫過傳記。你可能會以為她這樣識字、飽讀詩書的女子,會站出來為女性的權益發聲。但是她也同樣認為女性天生就不比男性聰明、有智慧。在復辟時期英國的社會,性別歧視最令人咋舌的地方,在於不平等觀念深化到連許多女性都已坦然接受。

在英格蘭社會上,女性的法律地位到復辟時期也沒什麼太大的變化。簡言之,丈夫是太太跟女兒的主人與支配者,老婆跟女兒不僅要聽丈夫或爸爸的命令,連她們擁有的物品或財產也歸男性所有。
艾德華・錢伯倫(Edward Chamberlayne)就在他所撰的《英格蘭社會》(Anglia Notitia,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England,1669 年出版)中,精確地描寫:「如果已婚女子獲得物品或是財產,這些東西會立刻歸她丈夫所有。在未經丈夫同意之下,她不得將這些物品出租、售出或者借給其他人。」
另外,在沒有經過老公允許之前,老婆也不能隨意向他人借錢或簽訂合約、遺囑。要是先生不同意,太太也不能讓外人踏入夫妻居住的房屋一步。要是有位太太逃離丈夫身邊,那他是有權闖進別人的房產把太太抓回家的。只要不致人於死地,丈夫也有權毆打自己的太太。
如果老婆拒絕跟丈夫做愛,丈夫也可以強迫老婆就範。如果先生被告,不管罪名為何,太太都不能在法庭上提供任何不利於丈夫的證據。所以如果先生跟其他女人偷情時被正宮捉姦在床,老婆也不能在法院中提出證據、控告先生犯下通姦罪。另外還有更多諸如此類的不平等待遇。
在十七世紀的英國社會,很多事都說不準,不過唯一有一件事是能夠肯定的,就是假如丈夫跟太太意見不合,就算太太說的才是對的,在法律上,她永遠是錯的一方。
與其說法律對婚姻生活造成太大影響,不如說是法律建構出來的框架,導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必須壓低姿態。要當一位「好的女性」,絕對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來行事,而是要壓抑自己的本能與渴望。某位作家就說過:「女人或許不能違抗上帝的旨意,但是如果丈夫命令她違抗自身的意志,她也不得不從。」賽謬爾和伊莉莎白・佩皮斯兩人之間,就不斷上演這種丈夫要求妻子壓抑個人情感的情況。

1663 年 1 月 9 日,伊莉莎白對著丈夫朗讀一封信,信中寫滿她悲戚的情緒(其實伊莉莎白已經寫過另一封副本給賽謬爾,但他讀也不讀就將信燒毀)。伊莉莎白在信中,表示每當先生到辦公室工作時,自己一個人在家孤苦寂寞。
對此,佩皮斯感到相當驚愕,他不敢相信太太竟然將家庭私事寫在紙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外人拿去讀。他立刻將太太才剛朗讀的那封信撕碎,還把她珍藏的一整疊信搶過來,在她面前把信件撕成碎片,其中還包含早期他寫給她的情書。而伊莉莎白只是站在一旁淚流不止。
不管佩皮斯其實完全有權這麼做,也不管他當天稍晚在寫日記時,是多麼懊悔自己上午的行徑,最重要的,是法律竟然賦予丈夫這麼大的權力,讓男人變得如此自傲、不願妥協。只是小小的意見不合,最後竟演變為人格侮辱。讀者讀到這裡,一定會相當同情伊莉莎白。跟一個認為自己永遠是對的,而且能隨意對你發脾氣的男人共同生活,有多麼壓抑委屈。就算他事後懊悔不已也於事無補。
未婚女性跟已婚婦女遭受的普遍歧視更加另人沮喪。對女孩來說,要接受拉丁文教育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所以以當時的標準來看,女性的教育程度普遍低落。就算她們能請私人教師到家裡上課,也不能到大學就讀或是以專業身分從事某項工作,例如律師或學校教師。如果女性精通醫術,她也不能向病患收取費用。
另外,女性不能成為議會議員或地方治安官,當然也無法享有市民權,所以也無法擔任市長或市議員等職。女性也不能投票,選擇自己屬意的議會議員。就算身為女公爵,女人也沒辦法在上議院中列席。
在貴族名門中,女兒只能站在一旁,看著每一位年幼的弟弟繼承家產,自己卻沒機會看父親的地產一眼,有時候其他家族中的遠房男性親戚還有權分一杯羹。第三代坎伯蘭伯爵唯一一位在世的女兒安・克里福德夫人就要等她叔叔跟表親(第四與第五代伯爵)過世後,才能繼承父親的房產和家族的城堡。與此同時,她還得忍受兩段不愉快的婚姻。
潑辣的女子會被綁在懲椅上,並且被固定在兩根長棍的末端,再被浸泡到池塘或溪流中以示懲處。更慘的是,整個社區的人還有可能在旁觀賞揶揄,讓當事人更感羞辱。不過善於逞口舌之快的男人卻不會遭此下場。
儘管如此,有時你還是會聽到別人說:「如果有座通往英格蘭的橋,全歐洲的女人一定會立刻奔向英格蘭。」或是「從某些角度來看,英格蘭的律法特別照顧女性,彷彿法律是她們投票制定的。」聽到這幾句話,你一定會滿腹狐疑。
舉例來說,要是英吉利海峽真的出現一座橋,伊莉莎白・佩皮斯肯定想往反方向跑。不過之所以會出現上面那種說法,在羅倫佐・馬加洛堤的手札中可以找到解答。馬加洛堤針對倫敦的女性,寫了這麼一段文字:
無論是身材或容貌,倫敦的女人都不輸男性。她們都相貌姣好,多數人身材高挑,有著深色的眼珠、淺色的秀髮,而且打扮得相當整齊乾淨,唯一的缺陷是牙齒不怎麼白淨。英國制定的法律,讓她們得以自在地過生活。其他國家的法律,對女性施以諸多限制,讓婦女綁手綁腳,但英國的女人想去哪就去哪,有沒有人陪都無所謂;低下階層的女子有時還能公開在街上玩球……她們並不會輕易墜入愛河,或是隨便對男人投懷送抱。
不過一旦她們心有所屬,就會陷入熱戀癡迷,為他犧牲一切。如果男人將她拋棄,她會陷入深沉的絕望與痛苦之中。英國婦女的穿衣風格相當優雅,呈現出法式時尚風情。她們以身上華貴的服飾為傲(連社會底層婦女的服裝也有一定的價值),沒有配戴昂貴珠寶的習慣。她們投資的珠寶基本上就只有珍珠,因此珍珠在英國倍受重視又搶手……另外,婦女在家中的休閒娛樂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妻子和太太專制地管理家中大小事務,男性對她們既尊敬又害怕。
馬加洛堤在此並不討論法律的規範,將焦點放在英格蘭婦女的日常生活。在他眼中,英格蘭婦女比義大利的女性更自由,而且對丈夫有更高的掌控權,因為男人都尊敬,而且害怕自己的太太。其實他口中的自由以及懼怕,也如實印證在賽謬爾和伊莉莎白的婚姻關係中。就算賽謬爾想到太太可能會愛上別的男人,會因此發瘋、吃醋,他還是讓伊莉莎白到外頭逛街玩樂。
至於害怕妻子的部分,賽謬爾在 1662 年的某一天,心中掙扎著到底該不該勾搭家中女僕,後來他打退堂鼓,因為「怕那位女僕太正直誠實,不僅拒絕我,還跑去跟我老婆告狀」,不過日記中沒有寫出如果東窗事發他會有什麼下場。
1668 年 10 月 25 日,賽謬爾把手伸進女僕的裙子裡時,恰好被老婆撞見。他在日記中坦承,「我的手指在她的小穴裡」。佩皮斯太太的反應,令賽謬爾相當不好受。她以沉默來表示自己的憤怒,原本相當自大的賽謬爾,也只能低聲下氣地苦苦求饒。事情發生後的那幾週,伊莉莎白不停地拿這件事說嘴,賽謬爾如此描述:「這是我這輩子最難受的一段時間。」

(Source:Wikimedia)
從某個角度來看,復辟英格蘭的法律以及風俗習慣其實相當保護女性。舉例來說,假如丈夫出門在外很長一段時間,返鄉後發現太太懷孕了,他必須把孩子當成親生骨肉撫養成人,就算他離家超過一年也是如此。同樣的,如果女子在結婚時腹中已經懷有胎兒,無論孩子跟丈夫是否有血緣關係,只要是男嬰,未來都能繼承丈夫的財產。
法律如此堅持丈夫應當全權掌控妻子的行為舉止,以致於即使已婚婦人犯下叛國罪,那也被視為服膺丈夫命令的結果,因此算是無罪。
結婚之後,女性會自動獲得與丈夫相同的社會地位與頭銜。如果丈夫是某位勳爵,那太太也會變成夫人(lady),不過要是地位較高的女性嫁給階層較低的男性,她仍保有原先的頭銜。假如某位公爵的女兒嫁給一般市井小商人,大家還是要稱她為夫人。
而農村中的傳統甚至跟一般都市更加不同。管理農務以及各項家事時,妻子是丈夫的左右手。笛福就曾說:「如果先生的農地營運良好,他會誠實地將收入帶回家,讓太太管理。」雖然在復辟時期,夫妻幾乎沒辦法離婚,就算離了也不太可能有辦法再婚,配偶還是能正式分居。
申請分居後,法院可能會判男方要支付女方一定的贍養費。1677 年,大主教法院(Court of Arches)宣判法蘭西斯・瑟洛摩頓爵士(Sir Francis Throckmorton)跟妻子分居後,每年要支付三百英鎊的贍養費。

(Source:Wikimedia)
除了這些制式的法律規範外,有些賦予女人權力的舊時風俗也會令我們現代人驚奇不已。彌松先生寫過:
有時走在倫敦的街上,我會看到一名女子拿著一個由稻草編成的人偶,人偶頭上掛著一對大型的角,前方有一位鼓手,後方跟著一大群人,用鐵夾、鐵架、煎鍋還有平底鍋敲敲打打,發出震耳欲聾的噪音。我問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說社區中有一位婦女,因為被老公指控在外偷吃,就狠狠地把犯疑心病的丈夫打了一頓。碰到這種狀況,有些善良的社區鄰居,就會替這位傷痕累累、可憐無辜的先生舉行這類儀式。
從離婚的贍養費還有稻草人頭上掛的那對代表姦夫的角,就可看出有多少男人對妻子抱持恐懼。
你可能也想知道,婦女的處境是獲得改善,還是每況愈下?在法律規範上,其中一個顯著的進步,是在 1691 年,女性能跟男人一樣申請在教會法庭受審,這樣一來,如果她們是初次犯下重罪,就可以免於處以絞刑的命運。
此外,婦女地位是否逐漸好轉,就要看她們自身的社會地位。如果妳的老公是窮困的農民,那妳生活肯定是過得越來越糟。
首先,所有農民都覺得時運不濟,不僅糧食價格飆漲,工資也低得可憐。不過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圈地制度也間接貶損鄉村農婦的地位。在十六世紀,許多農婦會跟丈夫一起在田野中耕種。現在農民失去自己負責的狹長耕地,沒辦法到林中砍伐生火的木材,也無法與其他農民共用牧地,只得到外地找其他有給薪的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獨留家中的妻子不僅要扛起原本由丈夫負責的家務,還要兼顧自己原本的義務。因此賺取現金的只有丈夫一人(所以錢該怎麼花也是丈夫說了算),太太越來越像沒領錢的苦工。農婦原本算是丈夫的同事,兩人一起耕種、為家中經濟付出,後來演變成屋裡主掌一切事務的傭人。
屬於「中間階層」的女性,則要面臨另一種困境,就是無法接受正統教育。在這個開始講求專業化的時代,民眾越來越希望外科與內科醫師能具有一定的身分資格,而且曾在醫學院受教育。自己在家進修醫術的婦女,被當成二流醫師,只能解決孩童的疾病或無關緊要的症狀。
教育與正式的資格變得比實際經驗更重要。想成為外科醫生或學校教師,就必須具有主教核發的證書。女性因為無法接受正統教育,因此沒辦法領取證書。對於證書與資格的需求越來越高,有些原本以女性為主的職業也逐漸被男性所佔領,助產士就是其中一例。
清教徒設下的高道德標準逐漸瓦解,較為富裕的女性獲益最為顯著。放縱享樂的風氣在宮廷中逐漸興起,家境富裕的女性也得以同時擁有好幾位情人,這種事在 1660 年之前可是連想都不敢想。具有創造力的女性,也變得更自由,能夠盡情展現自己的才華。
1661 年起,女性能夠在倫敦的劇場登台演出,許多女演員的收入都不容小覷。在復辟時期,繪畫技巧高超的女性能以此維生,反觀在清教徒風格濃厚的英格蘭社會中,女畫家就連要設個工作室都會令人眉頭一皺。
另外,女人要出版自己的劇作、詩和小說,也變得更加容易。還有一些家財萬貫的夫人開始設計、監督建築工程。伊莉莎白・韋伯翰(Elizabeth Wilbraham)的夫家位於史丹佛郡(Staffordshire)的宅邸,名叫威思頓莊園(Weston Park)的寬敞豪宅,就是在她的監督下竣工的。
在此時期,也有妻子接管丈夫的帳目,幫忙老公做生意。而淑女獲得的另外一項自由,就是能出門到遠方旅遊,西莉亞・芬尼斯就是最佳例證。在英國內戰之前,很少有女人能夠獨自出遠門的。內戰爆發之後,許多皇室成員旅居海外,這股不得不走避他鄉的風潮,讓更多女性發掘自己能藉由旅遊來自我學習。自此之後,女性自行出遠門的禁忌就逐漸瓦解。

整體來看,復辟時期的婦女過得不算輕鬆,但並非像往男性一面倒的法律所暗示的那樣嚴俊。有些人就認為,有能力、有辦法工作的婦女,是最快樂滿足的一群人。桃樂絲・奧斯伯恩(Dorothy Osborne)在 5 月的某個傍晚,經過住家附近的某塊牧地。她說:
有不少女僕在這裡看管羊群牛隻,並坐在陰影處唱著歌……我上前跟她們交談,她們對目前的生活已經相當滿足,因為她們知道自己是最快樂的一群人。聊到一半的時候,其中一名女子往四周觀望,看到她的牛群往麥田走去,她們飛步往牛群的方向跑去,彷彿腳上長了翅膀。
除了家境貧窮的婦女遭遇的性別歧視和偏見、極高的幼兒死亡率還有艱困的生活條件之外,你或許會開始思索,這些復辟時期的婦女是否跟 21 世紀的女性一樣快樂自在。

本書帶我們穿越到十七世紀的英國,表面保守的復辟時代,反而是奠定現代文化的功臣。作者用身歷其境的口吻,訴說當時候的社會、文化、政治,從光榮革命到榮光女王,從宗教道德到世俗享樂,徹底扭轉你對十七世紀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