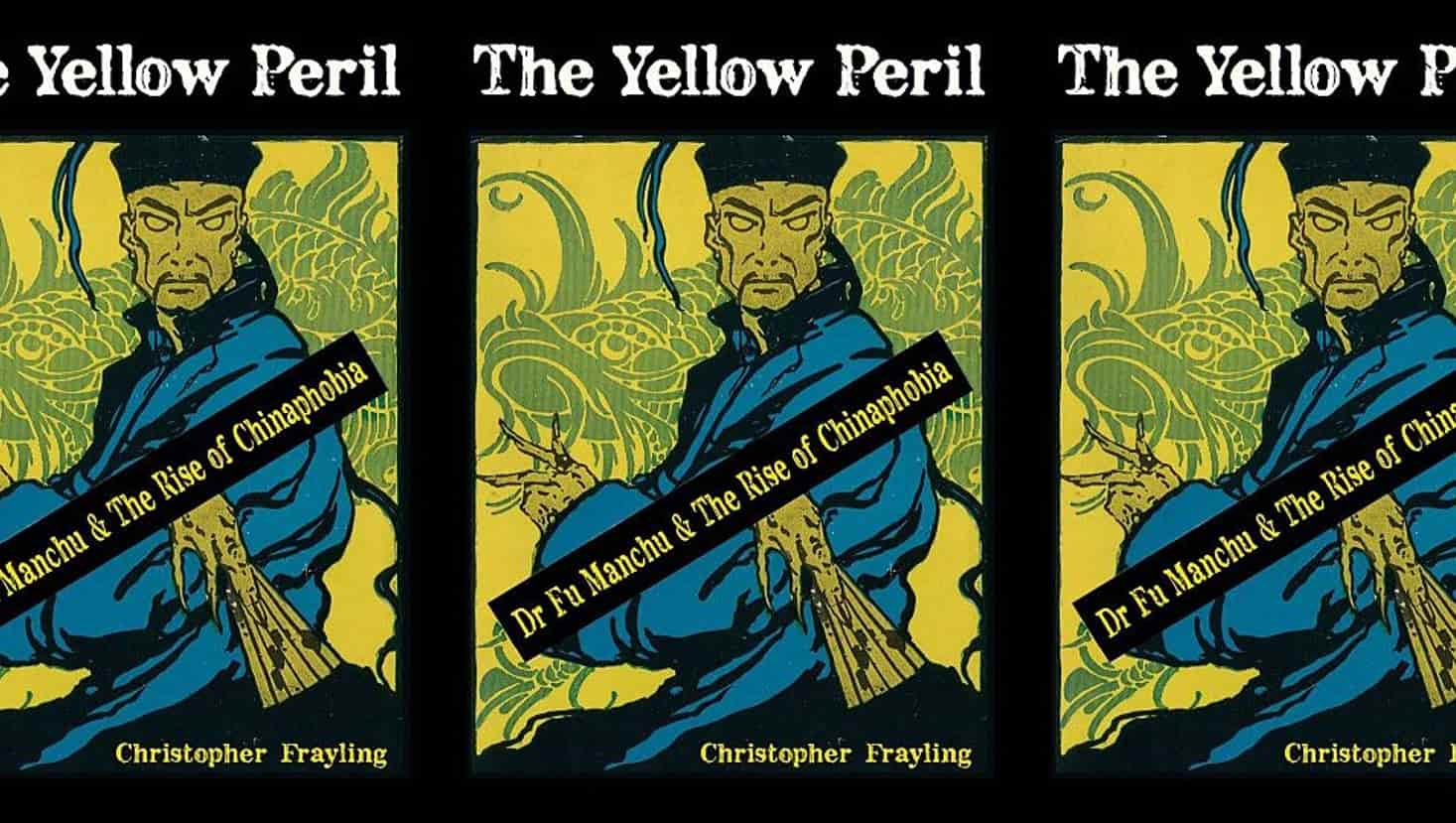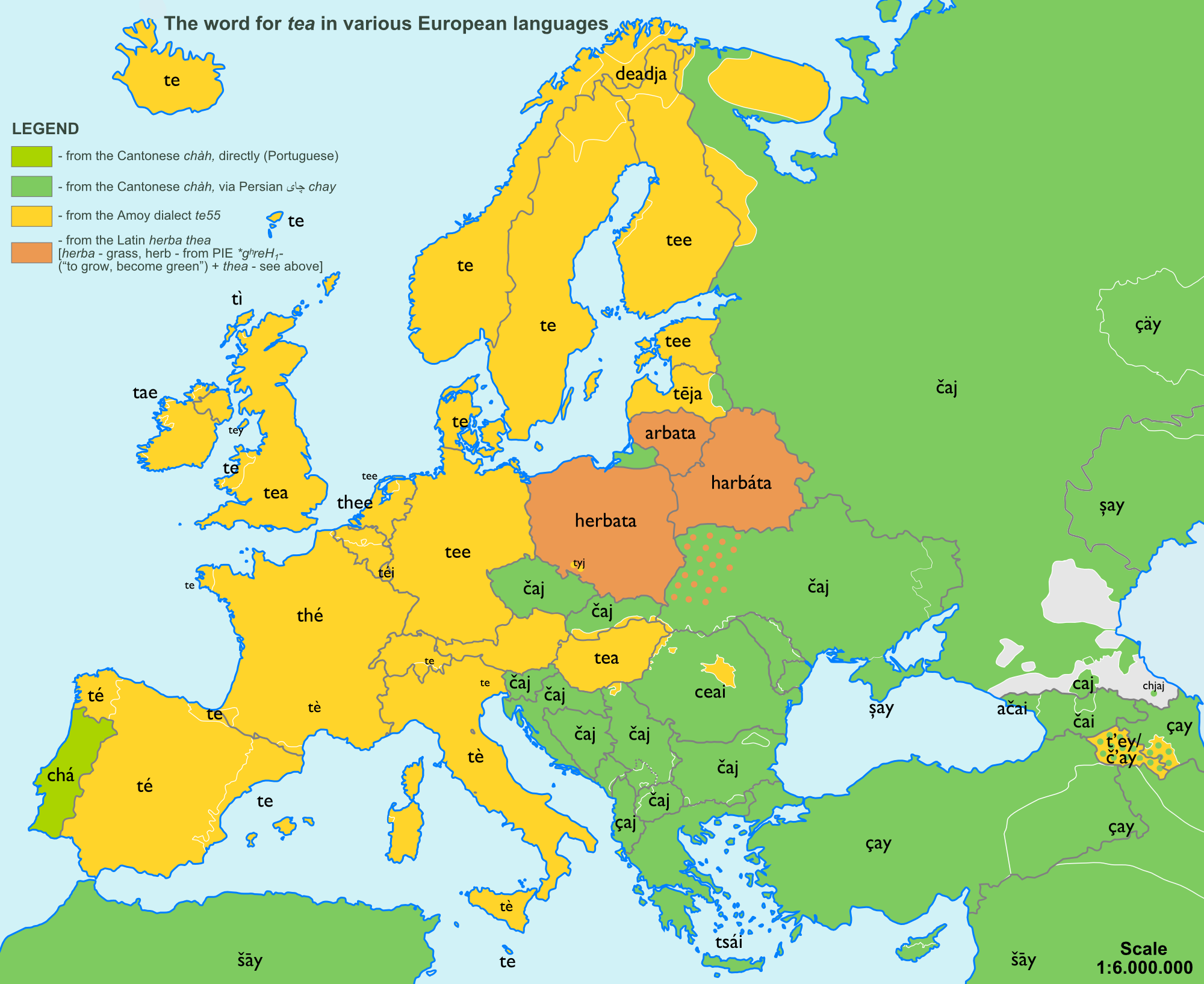1894 年,美國就曾拍攝一部近半小時的無聲影片《華人洗衣鋪》,以鬧劇的形式表現一個移民華人如何想方設法擺脫一個愛爾蘭警察的追捕。此後長期展示在美國銀幕上的華人移民形象,不是罪犯就是惡棍。
在 1970 年代的美國電影中,神祕的唐人街成為中國的象徵:邪惡的陰謀,遮掩的窗簾,在窗口窺視的東方人的面龐,窗簾後若隱若現、身分不明的人物,刻意構成一種祕密恐怖的氣氛。
而影片內中國人的形象與性格,無一不是醜陋、怪誕甚至邪惡的,女人裹著小腳,男人拖著豬尾巴一樣的辮子,留著長指甲,手裡拿著扇子或打著傘,細眼睛似笑非笑,說話怪聲怪氣,腦子裡詭計多端。
所謂「中國風情」即「中國怪事」(Chinesey),除了月洞門、工藝精巧的小骨董、女人的弓鞋和男人的大煙槍之外,就是中國人從早到晚抽鴉片,吃貓、狗、蛇、鼠之類的動物;溺死女嬰,以殘忍為消遣;愚昧無知,信奉一些亂七八糟的鬼神。
電影中還宣傳「中國的一切都是顛倒的」,如男人穿長裙而女人穿長褲,左首為尊位而右首為卑位,讀書是從上到下而不是從左到右,吃飯時總是最後才上湯,葬禮穿白而婚禮穿紅,姓氏在前而名字在後,羅盤指南不指北等等,無不與西方相反。西方觀眾從電影中得到的印象是:中國人是一個愚昧、懶惰、狡詐、骯髒甚至可能是兇殘的劣等民族,他們從來不願幹也幹不了好事。
1920 年代初,美國好萊塢拍攝有關中國人和中國的電影,有兩部曾為國內影評者所知。一部是《男女兒》(The Son-daughter),一部是《閻將軍的苦茗》(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
前者由一舞台劇改編拍攝而成:「背景為舊金山唐人街。一中國志士鑑於祖國國勢日衰,將有陸沉之痛,乃將愛女售與大富賈,得美金兩萬五千,為救國捐。」後者的「本事」是:「但女士(Barbara Stanwych)之未婚夫在中國內地傳道。迨婚期將屆,但女士來華。時中國內戰劇烈,為閻將軍所擄。屢次逼姦,女士誓死不從。事為將軍愛妾所知,憤其得新忘舊,設計通敵。將軍兵敗被擒,仰藥死。」[2]

對於這兩部影片,上海的中國影評家稱之為「辱華」和「失實」。作者署名「抱寒」的文章說:「《閻將軍的苦茗》在故事上而言,並無侮辱我們中國之處,不過在服飾上、化妝上,以及描摹我們中國人的舉動上,總有可挑剔的地方。」
對於《男女兒》,影評家則認為主演「雷門.諾伐羅(Ramon Novarro)係好萊塢地方很看得起中國人的人……所以我想雷門主演這部片子,不至於挖苦我們吧。況且雷門為主演此片,竟剃了一個光頭,戴上一頂方頂西瓜皮帽子,我們在幽默感上,似乎不應當過於苛求吧。即就魯意史東(另一男主角──作者)拖辮而論,我們二十多年以前,不是人人拖一條辮子,加上絲線,自命翩翩的公子?我看魯意史東扮演得真不錯。不過我在未看本事以前,還要保留一個判決」[3]。
在抱寒先生看來,除了演員的服飾、化妝、舉動有可「挑剔」之處外,這兩部影片並無「挖苦」、「侮辱我們中國之處」,即使主演頂著西瓜皮帽子、拖著長辮,那也是因為二十多年前中國人本來就是如此裝束,怪不了別人。
署名鵬年的作者認為抱寒的文章「略有錯誤」。鑑於抱寒對《閻將軍的苦茗》「本事」言之不詳,就稱故事「無侮辱華人之處」;而對《男女兒》的「內容本事尚未研究過」,僅憑主演雷門「很看得起中國人」就猜測這部片子「不至於挖苦我們」,鵬年遂在文章中簡述了兩部影片的「內容本事」,認為兩部影片在「辱華」和「失實」上「同出一轍」,均屬胡編亂造。即如《男女兒》表面上肯定愛國志士,但在實際生活中「華人賣身葬父則有之,賣女救國則未之前聞。外人心目中之中國志士,不過如此」[4]。這正是美國人認為華人缺乏做好事的本性和能力的反映。
更惡毒地把華人形象妖魔化的影片,是好萊塢米高梅公司根據前述羅莫爾的小說拍攝關於傅滿洲的系列影片。從 1929 到 1932 年,米高梅公司至少拍攝了一組以傅滿洲為主角的電影。當時的宣傳材料曾這樣描寫傅滿洲:「他的手指一動就是一個威脅;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個惡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種恐怖。」在電影海報上,傅滿洲的形像高高矗立,白人男女在傅滿洲的巨影下縮作一團。傅滿洲的銀幕形象集中了當時美國白人對東方和華人世界所有最惡劣的想像,在美國公眾中影響很大。

三○年代初為中國人所知的第一部關於傅滿洲的電影是《傅滿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該影片「本事」中的傅滿洲,曾經留學歐美,獲有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基督學院法學博士、哈佛大學醫學博士等等頭銜,但他卻是一個才智兼備而又殘酷狠毒的魔王,擁有極大的勢力,黨羽遍布世界各地。
傅滿洲與英國蘇格蘭偵探局的鄧尼斯.奈蘭.史密斯的「東西鬥法」,即雙方爭奪元太祖成吉思汗墳墓中的一副金面具和一把寶劍。英國人認為,如果金面具和寶劍落入傅滿洲之手,就應驗了成吉思汗死前所說的「我後來必復活」一語,傅滿洲必自稱成吉思汗再生,率領其野蠻軍隊殺入歐洲。因此史密斯搶先派遣探險家巴登爵士去蒙古戈壁尋找成吉思汗的墳墓。
傅滿洲正苦於不知道成吉思汗墳墓的墓道之所在,得知清楚這一祕密的巴登出馬,遂指使手下黨羽輕而易舉地將巴登綁架到了自己的巢穴,先加以利誘,再施以種種酷刑,要巴登說出墓道之所在,但巴登始終沒有吐露祕密。這時,巴登的女兒希拉得知父親失蹤,偕其情人德雷追蹤而至。因為希拉曾從其父口中得知墓道所在,遂能將金面具和寶劍從成吉思汗墓中取出。
但這一切逃不出傅滿洲的預料和掌控,待希拉等把寶物裝入大鐵箱,預備運出境外時,傅滿洲才出手,將希拉、德雷等一干人困住,要他們交出寶物。德雷聽說傅滿洲對美麗的希拉頗有非份之想,十分著急,為救巴登父女和自己出險,打算放棄寶物。
正在傅滿洲即將得手之際,史密斯從英國趕到,由他指揮一切。史密斯趕造了一把假寶劍,德雷不知就裡,將那把假劍獻給傅滿洲。傅滿洲知道成吉思汗的寶劍由百煉純金鑄成,遇見「神火」也不會損壞;而平常鋼鐵鑄成的劍,一遇「神火」就會熔化捲曲。試驗的結果,當然知道德雷所獻之劍是假貨。
傅滿洲把德雷綁了起來,一頓皮鞭將其打得死去活來,之後又將毒藥注入德雷的血管,使其本性迷失,從此對傅滿洲的命令服從唯謹。德雷回到住處之後,即說服希拉,瞞著史密斯,設法盜走真正的寶物,一起送到傅滿洲的巢穴內。這時德雷因為本性迷失,對希拉已無真心,在傅滿洲女兒的引誘下,兩人發生了愛情。
史密斯發現希拉、德雷失蹤,真寶物被盜,決定親自出馬。此刻已被截去一手的巴登爵士的屍體又被擲到史密斯腳前,他感到希拉等人也瀕於險境。果然等到他趕至傅滿洲的巢穴時,希拉已被綁住,傅滿洲正要殺她祭神。千鈞一髮之際,史密斯控制了傅滿洲自己發明的祕密電機,用電力把傅滿洲及其巢穴內的黨羽一個一個地殺死,救出了希拉等人。寶物自然也就落入史密斯之手。
對於這樣一部辱華影片,前述抱寒的文章只是輕描淡寫地說:
「但我們亦不能深怪他們,因為美國人民完全是一種享樂的人民。他們雖好遊歷,但不過遊山玩水作為享樂之一端,並不是真正來費心考察人情風俗的。他們所知道的中國人的一切,不過紐約、舊金山等處的唐人街。他們從來沒有和高尚的中國人士接觸過,所認識的幾個中國人或只是洗衣鋪或雜碎館裡的低級人。這種人大抵不識體統不顧國家顏面的。」[5]
顯然,抱寒先生對美國攝製這部影片的用意,完全缺乏社會學、人種學及政治意義的分析,而且他自以為「高尚」、輕視下層移民的態度,非常不足取。
相比之下,署名「思瀛」的文章要深刻得多。作者說:
強調中國人「對於此種『辱華』影片,實不能不有所認識」。
作者首先批評說:「日本人攫取中國的東三省,所藉口者是中國治理之不良善。所以西方人攫取東方的財寶,亦有很好的藉口。他說這種財寶在東方人手裡是危險的,可以擾亂世界和平。」所以西方人「必欲先探得成吉思汗古墓之所在,並取得墓中的金面具、寶劍等,就是為防止世界之大亂,維持世界之和平」,「而此一段故事就建築在這種片面、不公允的觀察點上」,使「西方人盜取東方之財寶,卻有絕大之理由」。作者諷刺說,推而廣之,「恐怕西方來東方之一切考察團、探險團等,都是抱著這種『大仁大義』之心的」。
至於雙方「鬥法」即「爭取之手腕」上,也是揚西貶東,「當然西方人攫取東方財寶所用的手段,實光明正大的;而東方人保持東方固有財寶的方法,係陰謀、殘酷、無人道」。作者能夠抓住影片的立意和態度,高屋建瓴,直接點中要害。
作者接著批評影片表現傅滿洲等「種種殘酷,亦皆不一而足」,其實都是東方人聞所未聞,「恐怕只有西方古時有之」的東西。諸如傅滿洲對巴登使用的「鐘刑」,「即以人縛置大鐘下,使日夜不斷的鐘聲,刺激他的耳鼓,使人狂猘而死」,中國絕無此刑法。再如「傅滿洲的女兒,做出惡形惡狀的樣子,一會兒去迷惑老巴登,一會兒去引誘希拉的情人德雷」,其「陰險」無恥,也非東方女性所能為。
而德雷與傅滿洲的女兒「發生了愛情」,則是美國影片中常見的「把肉麻當有趣」的表現手法。還有傅滿洲既然「萬知萬能」,「豈能任外人去其巢穴而毫無所知?並且他自己發明的祕密電機,居然能為史密斯所用而自啟殺身之禍。種種不近情理之處,均足證明作者力求荒誕虛幻之後,無法收束,而借用神話中『從天而降』的神助來做一結束,真是無謂幼稚之至」。
作者還自以為很策略地指出:「實則美國影片家用其金錢,費其腦力,製作此種影片,於人於己,兩無利益,亦屬無謂也,未知彼等何獨出此舉。若以此為娛樂之需,則殊無幽默之資料;若以足為教育之工具,則徒增人民之誤解;若以之為宣傳之利器,以中美邦交之友善,似亦不應出此。故除去美國影片資本家之拜金主義、唯利是圖之觀念外,恐無其他解法。」那麼實際結局將會如何呢?
作者認為「此種辱華影片」,「在中國市場已無立足之地」,因為它會「使中國人易觸其懷疑之心,或竟貿然地加以拒絕。中國影劇院對於此種影片,遂不得不過慮及審慎。因此此屬影片,或將絕跡於中國市場,美國影片廠當然須忍受此一筆經濟上之損失」。
因此作者希望,美國影片廠商「應了解此種國際諒解與友誼之障礙,即不從經濟方面著想,亦有早日祛除的必要」[6]。對照作者前面頗能切中要害的分析,此處僅從經濟利益、票房價值所做的解讀和勸告,顯然失之膚淺,或許作者是想把深刻的認識理解與策略的批評兩相結合吧。
好萊塢的影片常常是美中關係的晴雨表。 1930 年代初,儘管中國東北已淪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但當時的美國還陷在經濟大蕭條之中,門羅主義盛行,東方人再度被認為是搶走白人飯碗的「公敵」,遷怒的心理就是有關傅滿洲的電影問世並莫名其妙地引起轟動的原因。
直到中國全面抗戰開始的 1937 年,中國人民的抗戰事蹟激起了美國公眾的同情和好感,加上同年根據賽珍珠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大地》(即前面抱寒先生所「期待」的《佳土》)問世,在美國電影觀眾中初步改變了中國人的惡劣形象,觀眾多達數千萬。為了不冒犯觀眾的情感,好萊塢在其後的一部影片中安排了傅滿洲的自然死亡。
但在 1949 年以後,美中關係惡化,好萊塢電影又密切配合美國政府的反共反華宣傳,充當冷戰意識形態宣傳的先鋒,遂讓傅滿洲再度復活,且形象更加邪惡恐怖。這類影片有 1965 年上映的《不死毒王》(Face of Fu Manchu),1968 年上映的《傅滿洲之血》(Blood of Fu Manchu)。
而最後一部是 1980 年上映的《傅滿洲的奸計》(The Fiendish Plot of Dr. Fu Manchu),內容仍是老掉牙的故事,而且粗製濫造,因此既未產生票房價值,反而激起美國華人世界的一片抗議之聲。不過七○年代末、八○年代初是美中關係的解凍期,美國家喻戶曉的傅滿洲已被製作者安排在影片中再次死去。或許他永遠不會再度復活了吧。

[1] 以上敘述及引用文字參見:周寧:〈「義和團」與傅滿洲博士:二十世紀初西方的「黃禍」恐慌〉,《書屋》2003年第四期;《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學苑出版社,2004年;〔美〕陶樂賽.鍾斯著,邢祖文、列宗錕譯:《美國銀幕上的中國和中國人(1896-1955)》,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年。
[2] 鵬年:〈關於「失實」影片〉,《申報》1933年2月2日,「電影專刊」第五版。
[3] 抱寒:〈關於「辱華」影片的鳥瞰──對於「佳土」的期待〉,《申報》1933年1月24日,「電影專刊」第五版。
[4] 鵬年:〈關於「失實」影片〉。
[5] 抱寒:〈關於「辱華」影片的鳥瞰──對於「佳土」的期待〉。
[6] 思瀛:〈從辱華一點上說說「傅滿洲的面具」〉,《申報》1933年2月2、3、4日,「電影專刊」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