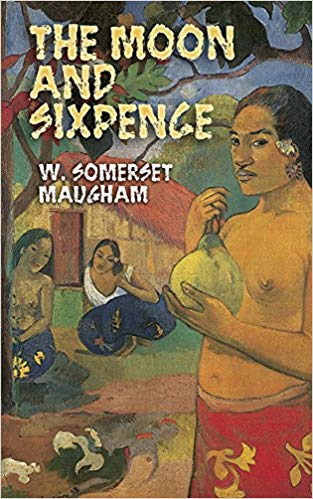此三本小說的書單發想自一首流行歌,由歌曲使人產生的情感中,依此共同情感挑選而成的小說書單。陳淑樺的「夢醒時分」是一首多數臺灣五、六年級生都聽過的流行歌曲。這首過去的流行歌曲已淡出眾人焦點,但像這樣一首人人皆知的歌曲,它可能會成為某些人生活之中,一場淋在心中的即時雨。在一些需要炒熱氣氛的場合中,不少人都可能面臨過這種窘境──被麥克風突襲。在無效的抗拒下,麥克風已傳到自己發汗的手掌上,音響也開始播放歌曲的前奏,麥克風只能被抬舉到乾躁的雙唇之下,聽到一陣陌生歌聲從自己的身體發出:「要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在每一個夢醒時分。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必問,有些人你永遠不必等。」
歌曲尾音一落,眾人驚呼及些許的掌聲,還有從胸腔傳來的心臟跳聲,眾聲齊鳴。待炫暈感一過,我們內心低語:「其實也不就是大家面前唱一首歌嘛!不過…我怎麼可以唱得出來呢?啊…是因為這首歌是〈夢醒時分〉啊!」多數的人都可能被這首歌給打動過吧!因為打動每一個人,正是一種往自己渴望的夢想追逐著,但不免遭受許多挫折,對夢想是否能達成,心底不斷地自我質問的孤苦心境。
這也這是名為「夢醒時分」的主題式書單命題裡,筆者所挑選的文學讀本之中,在這三本小說的世界,每一個小說主要角色必經的心路歷程。
本次的書目《月亮與六便士》裡以一位初出茅盧,並在文壇小有名氣的作家的觀點來說故事,由一個局外人去描述拋家棄子去追求夢想的狂人查爾斯.史崔蘭(Charles Strickland)。史崔蘭的人生故事並非《月亮與六便士》的作者毛姆(W. Somerset Maugham)所原創。他參照著後期印象派畫家高更(Paul_Gauguin)的傳記,創造出史崔蘭這個角色。
作家一開始就先和讀者們說明,史崔蘭倍受人們討論。他以一只紙條向妻子宣告分居,並絕然地揮別過去四十七年所累積的人生,目的並未說明清楚。他的所作所為驚懼身旁所有的人,同時也引起作家的高度好奇。作家得到史崔蘭夫人的托付後,前去巴黎見一見史崔蘭,並搞清楚他的動機。因此作家找到了他,史崔蘭一副邋遢,還向作家索求請他吃飯,作家順勢帶他上餐館,並展開作家渴求的對話:
「你究竟為了什麼離開她?」
「我想畫畫。」「…以其他任何行業來說,你不特別傑出也沒關係,你只要還過得去就能過得很舒適,不過藝術家就不一樣。」
「你這該死的蠢蛋。」「我就跟你說了我得畫。我也沒辦法克制自己。一個人掉進水裡的時候,他游得好或是不好並不重要:他就是得游出來,不然就等著溺水。」
※※※※※※※※※
接下來的故事,史崔蘭是否就此展開他傳奇的畫家人生呢?寫出《月亮與六便士》的毛姆不愧是 1930 年代最賣座的作家,這本略為厚實的小說裡不僅只有史崔蘭的故事引人入勝,毛姆還加入了一些個性鮮明的角色,使得這一本探問追求夢想為何物的小說,讀起來十分過癮。毛姆自 1897 年發表了第一部著作《蘭貝斯的麗沙》,即受到好評,使得原本從醫的毛姆展開作家的旅程,並且在倫敦的劇場界展露峰芒,累積不少劇作。接著開始發表長篇小說:《人性的枷鎖》、《月亮與六便士》、《尋歡作樂》以及《剃刀邊緣》被稱為毛姆四大長篇小說代表作。毛姆在他的時代被當做是通俗小說作家,當時以意識流文體才被人們認為是文學作品,也許他的作品太過於受人們喜愛,所以好的作品得以被冠上「通俗性」。
這種對作品是否受人愛載來決定文學性的判斷,相同的時空背景下,民國才女作家張愛玲也有她的看法,她認為讀者要什麼,就給他們什麼。「我從小就是小報的忠實讀者,它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情趣,它可以代表我們這裡的都市文明。」[2] 事實上,當年的毛姆旋風也傳到中國的土地上,張愛玲也成為毛姆的讀者,她的第一本小說《傾城之戀》,約略可以感受到毛姆的作品影響的氣息存在。
※※※※※※※※※
重新回到小說文本上,一個在巴黎街頭上隨意找人作畫的英國人會遇到什麼事?史崔蘭遇上了德克.史特洛夫(Dirk Stroeve)。或者是說德克遇上史崔蘭,因為同為畫家的荷蘭人德克與史崔蘭的緣份,改變了德克的一生。小說的說書人,也是文本的敘事者,對史崔蘭的個性抓摸不清的作家,在史崔蘭認識德克之前,作家已經是德克多年的朋友,按作家率直的評價,德克的畫作糟透了。與其說德克是一名畫家,不如說他是鑑賞家。作家認為德克對藝術的感受敏銳,並且能做出準確的評斷。
史崔蘭對德克的人生最大的衝擊,就是非出他本意的走進德克的婚姻。一心只求作畫的史崔蘭,對與畫畫無關的事物毫不在乎,這也包括他自己的身體。德克惜才心切,將重病虛弱的史崔蘭帶回家療養。德克的妻子布蘭琪,和自己的生先也是一對外貌上極不相襯的夫妻。相較於善交際且幹練的史崔蘭夫人,德克夫人是蒼白且優雅的。德克是臉蛋紅通通短小的胖個子,布蘭琪與德克的組合如同史崔蘭與其妻子,在毛姆筆下一律都是外在氣質不協調的夫婦,像是各懷心事,對彼此隱藏著炸藥,在平靜生活蓄勢點燃。
德克的存在似乎就像是突顯史崔蘭的「奇異」性格。在小說劇情中,一件引發德克巨大的精神崩潰的事件發生了,身為二個人的共同朋友的敘事者也氣壞了,敘事者認為史崔蘭卑劣至極,對他自己造成的傷害渾然無覺,幾近沒有人的情感。但最大的受害者德克卻為了「美」原諒了史崔蘭。
藝術上,眾人煞費心力,像是追求高高在上的神祇一般的美。「美」之於藝術家,猶如「真理」之於知識份子。德克從史崔蘭的畫作上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美」,他試圖表達自己的感動給作家:
人們常輕率地談論美,由於他們對於文字沒有感覺,便隨意使用那個字彙,導致它失去強度;這個字所代表的意義,由於和上百個微不足道的物體共用一個名字,因此被剝奪了尊嚴
史崔蘭與德克若至少有一處共同點,那就就是他們皆是「美」的信徒,不過力度上,史崔蘭有如被魔鬼附身,作家稱他兼具狂熱分子的直接及傳教使徒的兇猛。事件平息之後,不想再被過往記憶引起悲傷的德克,選擇離開了巴黎,史崔蘭則是踏上前往大溪地的道路。
故事進展到這裡,小說已進行到三分之二的內容,敘事者常回想自己對於史崔蘭的描述是否合宜,以一個書中人的角色,他將自己置於史崔蘭的人生的外部,與小說書頁外的讀者近似。作家突顯自己的客觀企圖及所知有限,並自謙如同生物學家,從各式關於史崔蘭的人事物去拼湊他的「真實」故事面貌,他並承認這個人物在他嘴裡的描述,讀起來仍然不夠清楚。
作家此番的自白心態,令筆者不禁揣測史崔蘭的個人形象,是否就像天上月亮一樣?越靠近越覺得對月亮的理解總是不夠。月亮所散發出的迷人月暈,是否就像藝術家給常人的神秘氣質呢。藉此提到《月亮與六便士》書名背後的故事,該書名據說是來自讀者對毛姆另一本小說的評價。讀者評論《人性的枷鎖》的主角:「菲利與許多年輕人一樣,都對天上的月亮神魂顛倒,卻不見腳底下的六便士硬幣。」毛姆知道了後,將這個評論變成下一本小說的書名。後世眾家都將「月亮」當作是夢想的暗喻,「六便士」則暗指現實生活。
以一個真實人物為藍圖所描繪的小說角色,由法國畫家高更為靈感來源所創作的史崔蘭。讀者若以非虛構的傳記文本對照著虛構的小說敘述,將高更的真實人生去對照虛構的史崔蘭,這會是《月亮與六便士》本文閱讀後,另一種玩味之處。特別是毛姆透過作家之眼,去想像已達到藝術巔峰的史崔蘭的結局。比照高更的傳記,應該算是毛姆同樣對追求藝術上的自我實現的高更一種致敬吧。作家對史崔蘭在大溪地的終幕如此地感嘆:
我喜歡他從四十七歲開始追尋新世界的模樣,大部分的人到那個年紀早已安於規律的生活。在我想像中,海面在西北風吹拂下一片灰撲撲地捲起泡沫,他注視著法國海岸線漸行漸遠,而命運注定他再也看不見;我覺得他英姿煥發且心無所畏。
我好想讓故事結束在希望的氣氛中,這樣彷彿能強調出人類不被打倒的精神。
也許作家在感嘆人們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需要無所畏懼的強悍才能不被打倒,否則我們抵達不了夢想的高度,像掛在高空上的月亮需要人類幾百年努力,才能踏上去月亮的地面上,走那麼一小步。但《月亮與六便士》的毛姆,塑造書中作家背後的作家。除了以此小說向人們展示追夢的過程,在小說的結尾也隱含著對於「評論他人」一事的批判。[3]就像真實的高更在數十年後,不斷被人議論及評析。
「你有夢想才能活!」[4],可能會是史崔蘭夫人回給史崔蘭的忿怒之語,但也可以另一種說法,你我有了夢想才能去活。夢想與生活的關係如何決定?應該都操之在你我手中。
我們之中,都會有人不斷去挑戰這個說法是否適用在自己身上。究竟像史崔蘭為了追求藝術理想的人生,或是回到他當畫家之前的人生,那種生活才是真的成就人生,此番人生為何的大哉問,在這本《月亮與六便士》的小說裡,或許不能得到通透的解答,但卻提供一種開廣及奇妙的視野。
最後以書中的小說作家的一段自嘲作結尾。向耐心讀完本文的讀者致謝:
從事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生活在讓自己開心的狀態下、自己心安理得,這樣算是把自己的人生給搞砸嗎?還是成為知名的外科醫生、年收入一萬英磅、娶得美嬌娘,這樣就算是成功?我想取決於你賦予人生的意義、你對社會的要求,以及你個人的要求。不過我還是乖乖閉嘴,畢竟我有什麼資格與勳爵爭辯呢?
[1] 參見蔣勳,《破解高更》(臺北:天下文化,2013),頁 46。關於高更的人生,他並沒有像《月亮與六便士》的史崔蘭般突兀的離去,後來的評論家研究他的生平,為他的人生重大決定,找了不少合乎人性的解釋:「高更離開金融市場,並非任何狂熱衝動的表現。整個1882年金融市場均呈現不穩定狀況,高更只是轉盈為虧的許多人之一而已。完全投入繪畫一行需要相當的勇氣,但倒也不盡如某些評論家所云純屬血氣之勇。高更的妻子未從過苦日子…在哥本哈根的日子,高更夫婦不得以教法文補貼生活。他曾有意重振事業,不過沒有成功,正繪畫上也徒勞無功。高更並未放棄一切,他曾經賣畫,或運用生意手腕等努力,衷心想使全家能在一起。」參見何政廣主編,《高更:原始與野性憧憬》(臺北:藝術家出版,1996)頁 32、66。
[2] 參見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制度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13),頁179。
[3] 參見李繼宏譯著,〈導讀〉,《月亮與六便士》(天津:天津出版社,2016)。
[4] 文章標題發想出自臺灣獨立樂團 Tizzy Bac 之「你需要快樂才能活,我不用」一曲,收錄在《易碎物》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