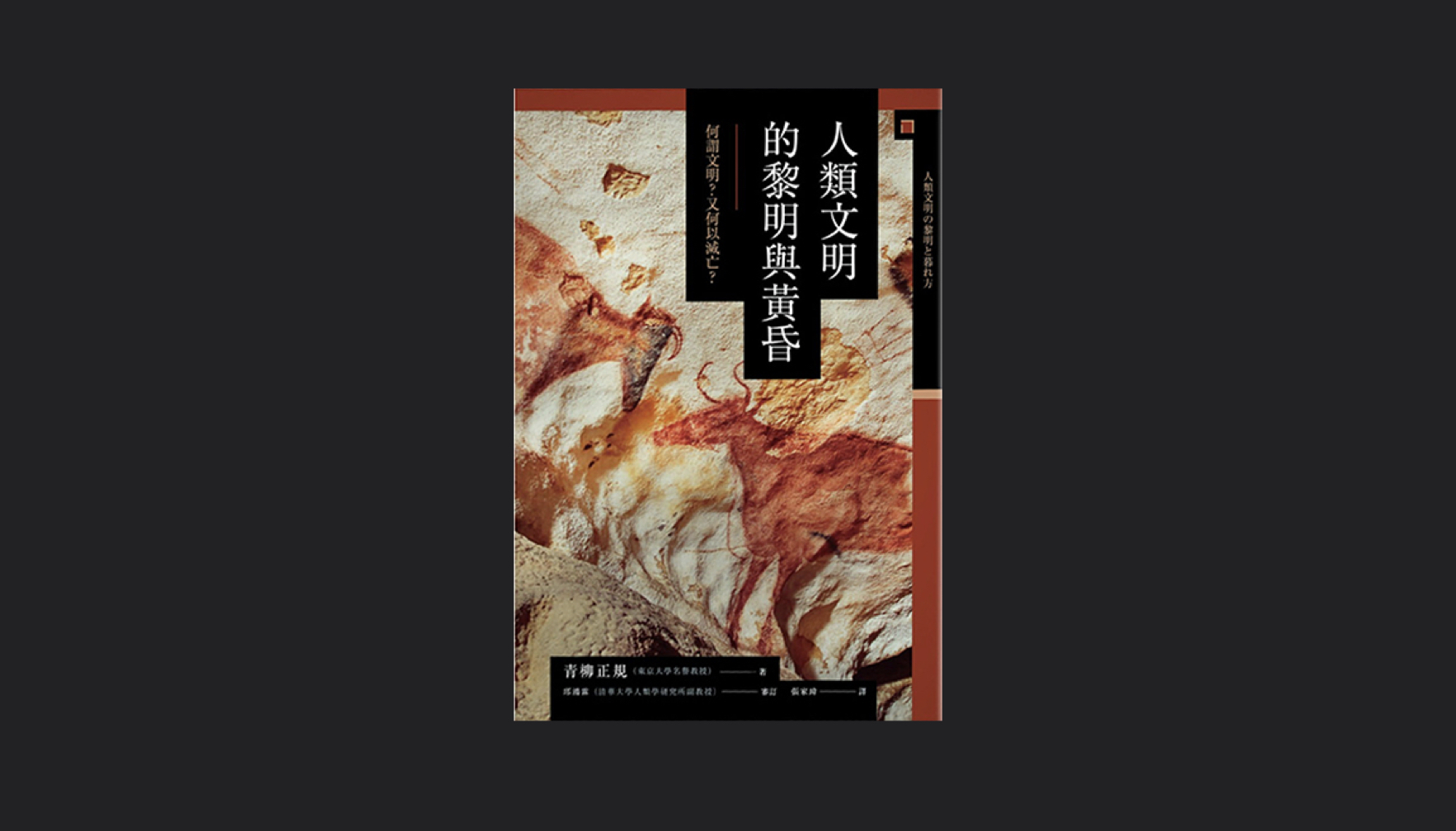擔任劇本競賽的評審是件讓人低頭歎息的苦差事,因為劇作不是用來讀的,是用來演的。初讀《逆旅》,看到劇本第一頁曹海安嘴裡蹦出謝雪紅三個字,一度令人神經緊繃,深怕又是一篇政治正確的敗筆。然而從第二景開始,海安失聯多年的女兒 Vivi 站在陷入昏迷的海安床邊,努力想從那張安靜的臉龐讀懂她已然陌生的母親開始,我便昂立引頸地期盼著,Vivi 究竟要怎樣從海安的日記和海安參與的謝氏傳記眉批裡,拼湊海安(甚至謝氏)看似不平凡卻又一無所成的女人的一生?
自從那刻起,我看著《逆旅》一路從得獎到搬上舞臺又到如今再出版,無論如何修改,只愈動人地從一個平凡女人曹海安臨終的安靜臉龐上,映照另一個過度被政治化與傳奇化的謝雪紅的面容,讓彼此都變得更平凡也更有人的溫度。
作者稱《逆旅》是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程。更具體說,它是一部關於三代人互為彼此生命眉批的故事。歷史人物的傳奇性也許容易入戲,歷史裡政治人物卻很難寫,因為作者太容易露出自己幼稚的政治見解。《逆旅》作者技巧地從一個他最熟悉的「閱讀」行動下手,設計了彼此陌生又關連的三個女人:謝雪紅、《謝雪紅傳》的合撰者曹海安,和自認被海安遺棄的女兒 Vivi,讓他們在閱讀彼此生命的歷程中,成為對方日記上的眉批。
故事開始於戒嚴前的台灣,應該安穩過日子的曹海安,幫一個辭去大學教職的歷史學者張崇輝,準備撰寫當時仍視為禁忌的謝雪紅傳記。他們在拮据的角落,啜飲一杯曼特寧,熱情地閱讀謝雪紅,安靜交換對彼此的澎湃,十足的小確幸背後,是解嚴前夕的台灣,人們處心積慮攢積一點自我的小浪漫。
不過作者並不耽溺於此。第一場裡被傳記人物啓發的家庭主婦曹海安,第二場來到生命尾端,最終只落得截然一身入院,一生的故事盡藏於床下的一只皮箱,上了鎖等待知音人猜中密碼重新開啟。自此,海安的故事和她眼裡的謝雪紅的故事,都要由不瞭解她(們)的女兒 Vivi和後來畏縮離台的昔日戀人的兒子士允,從她(們)的日記與傳記眉批中,從她(們)臨終的面容變化裡,細拆密縫,重新拼湊。
劇本的精彩之處,在於劇中人物在閱讀彼此的過程中,讓自己和對方,短暫地合而為一又迅速分開,即彼此依靠又各有性格。例如,謝雪紅回憶幼年的自己的姓氏像「衣服一樣縫在我身上。我低頭發現,世界,也不過就是我腳底踩的一小塊地」,喚起了曹海安和姊姊海寧(隱喻謝氏的二姐)和後來的單親女房東「一世人做別人媽媽和做別人的某,攏袂記做自己是啥滋味?」的共鳴。
劇本的結構,自此讓劇中所有的女性,都因為曹海安撰寫謝雪紅,而互為彼此了。謝雪紅的旅程,也成了她們的旅程,就像 Vivi 想像母親怎樣在火車站等者張崇輝卻等來讓她下獄的警察,看似理解了海安當年等待的,未必是張,而是一個真正可以掌握自己未來,不再害怕的曹海安。
劇中的高潮之一,當是第六場謝雪紅的單人旅行之二「世界」,扮演海安,房東,Vivi 的三個演員,同時閱讀謝雪紅,並在閱讀中回顧自己的遭遇。當讀者觀眾快要被這群昔日的家庭傀儡的眼淚窒息的時候,劇作家不忘給我們片刻的莞爾。例如,劇中曹海安的姐妹淘對謝雪紅的好奇,非關政治革命,卻是「聽說謝雪紅是台中第一個會騎腳踏車ㄟ查某人!每一次出門騎車,路邊就會有一堆人搶著看!」這樣的生活「醋汨」。
她們,終究不曾造就什麼了不起的革命,不過是激起了片刻的叛逆漣漪。
初識《逆旅》的人,往往好奇年輕英俊的斯文書生如詹傑,怎能這樣細寫女性的幽微情愫?然而詹傑對生命和歷史的憐閔,才是《逆旅》真正讓人驚悸錐心處。正如劇中士允伴著 Vivi 待在海安床邊,想著堪稱海安與父親婚外情犧牲者的母親的孤獨臨終,卻只悠悠地說著,「其他人漸漸就不來了。他們沒想到死是一件這麼久的事。」無論生命如何激烈飄盪像謝氏傳奇,或如何平凡無成似劇中女性,死亡的過程都是漫長而孤獨的。
從死亡的一端,來回搬演的一度叛逆激進的劇中人短暫的菁華和漫長的臨終,詹傑似是透過《逆旅》為我們展開了一種台灣的歷史情懷。那究竟是什麼情懷?劇中兩句臺詞,又像是詹傑自己的兩則眉批:「有天當我離開,你就再也找不到我了。」「但是那些字會活得比我們更久,去到更遠的地方。」一旦它們的順序如《逆旅》般顛倒,觀者得到的歷史情懷,同還是不同呢?

(本文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