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讀過尤其有趣的,是三本備受各自專業領域重視,也同時成為英語世界暢銷書籍的著作。首先是 Kate Manne 的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Oxf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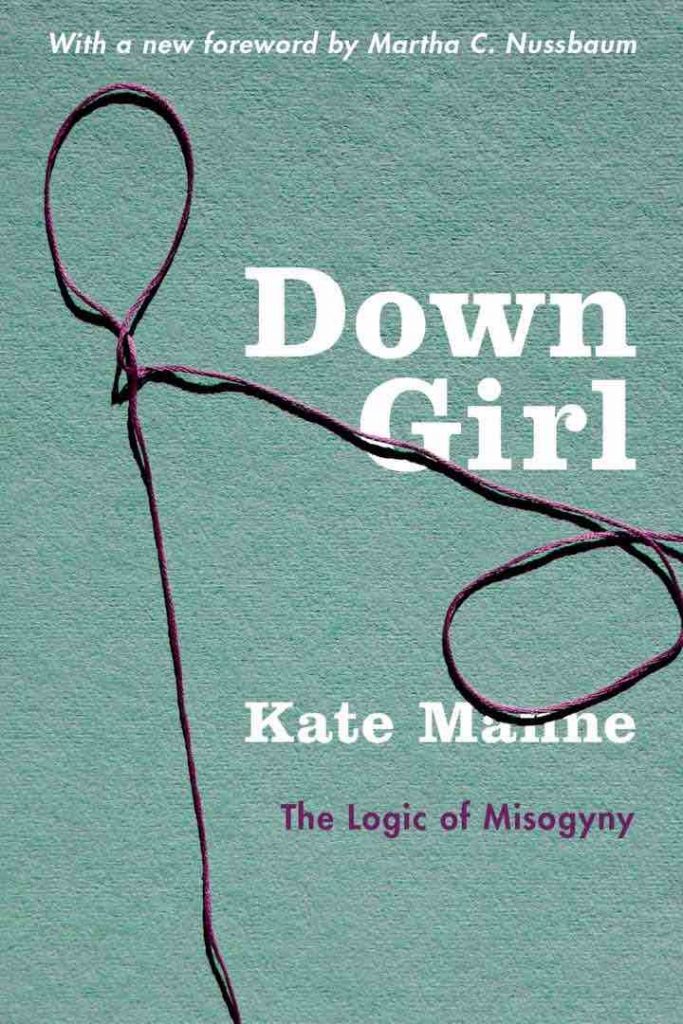
女性追求性別平等,似乎不只是一個追求或呼籲重視權利的社會裡,再平凡不過的一種訴求。我們很熟悉一種反對權利運動的言論,其句式往往是「我知道你們追求的 X 權利很重要,但我們不是已經給你們因應的 Y 了嗎?為什麼還要不知足、得寸進尺?」不過在性別議題上比較不同的是,這樣的句式(「性別已經很平等了,不然還想怎麼樣?」)之後,往往會伴隨對女性的人身辱罵與威脅。為什麼在「性別已經很平等了」的社會裡,還是會出現目標多為女性的仇恨言論與行為?
這是本書主要探討的問題。要有效地回應此問題,我們必須要在邏輯上分別理解「性別歧視」(sexism)與「仇女」(misogyny)兩種態度。前者更近似於一種意識形態。它是一種認識世界的視野,連帶會影響人們如何判斷事物。這種視野認為,男女的性別分化是自然的,因此性別分化後所有相對的行為能力與社會職責也是自然的。破壞這種視野的期待,會造成一定的判斷與認知上的不適應,但未必會招致敵意。甚至儘管這種意識形態產生的言論,可能會造成女性與男性受眾的不適,但這種不適未必是針對特定對象的敵意導致(當然,這不構成為此開拖的理由)。
「仇女」則不然。「仇女」的邏輯,具備強烈規範要求的倫理位階:女性就是不應該踰越這種倫理位階,一旦女性試圖踰越,或脫離她們所應處的倫理位階,則女性必須受到相對應的懲處。「仇女」因此不僅只是性別歧視的激化結果、或是對女性追求性別平等的反動。它基本上是一個「獨立自足」的邏輯系統;一個有明確懲處對應機制,以確保女性必需要長期位處在她們的倫理位階的類警備機制。
這也說明為什麼在「性別已經很平等了」的社會裡,還是會出現一些目標多為女性的仇恨言論與行為。或者應該說,正因為在「性別已經很平等了」的社會裡,女性脫離「仇女」邏輯的倫理位階應是常態,具仇女邏輯的人更可能認為必須將懲處機制付諸實踐,進而出現前述的仇恨言論與行為。換句話說,「仇女」警備邏輯造成的後果,很可能與社會對於性別議題的態度趨向平等成正比。這樣的分析,指出了權利運動遇上具備倫理位階的警備邏輯時,極可能無以為力的現象。
第二本書和第三本書分別是 James Susskind 的 Future Politics: Living Together in a Transformed World(Oxford),以及 Shoshana Zuboff 的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rof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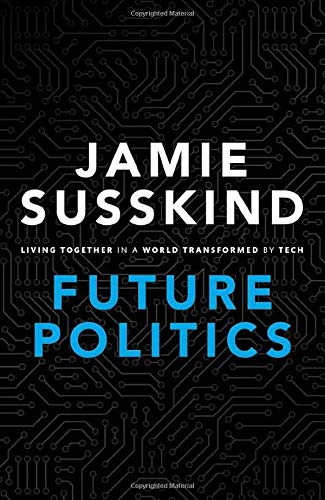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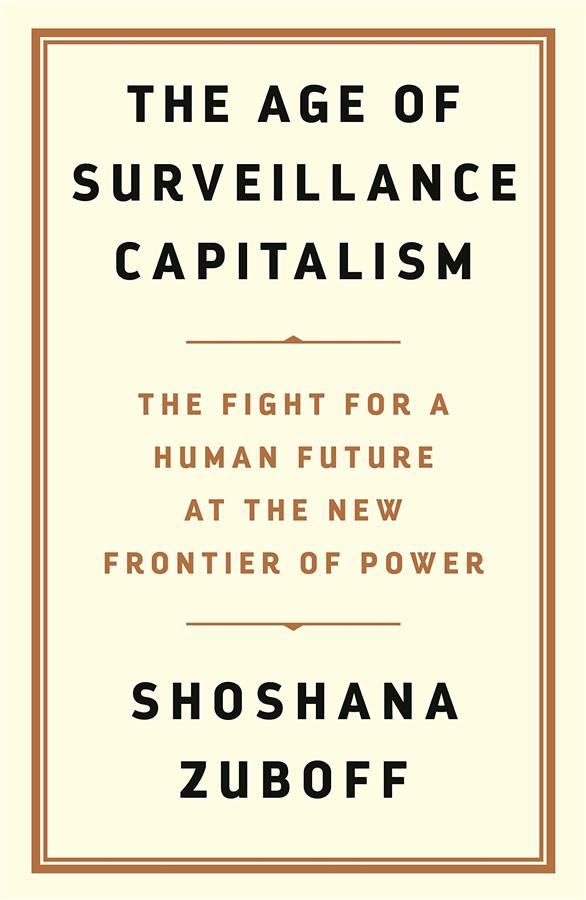
Future Politics 的問題有兩個層面,首先是「人們應該如何共存?」其次是「人們應該如何在一個已然發生巨變的世界共存?」這個發生巨變的世界,指的是現在這個數位科學與科技發展迅速,且已經實質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世界。
儘管第二個問題已然成為顯學(「教你如何在 AI 的世界生存」等主題的文章、研討會、座談已經多到有如內容農場衍生物),但顯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第一個問題才是第二個問題的根本。對第二個問題的有效回應,無法迴避對第一個問題的有效回應。事實上,如本書所言,我們對第一個問題的反省,也許早就鋪陳好對第二個問題的解答。
Susskind 認為,在所謂的西方世界,對第一個問題探討的最重要成果,是意識到第一個問題歸根究底是一個政治理論的問題。這是因為「我們要如何共存?」,其實可以由至少四組問題組成:在一個共同體裡,「強者如何統治(對待)弱者」、「什麼樣事態、言行、與事物被允許,又什麼不被允許」、「人們可以如何治理共同體」,以及「人們彼此間有什麼樣的責任」。
這對應的是四組西方政治理論淵遠流長的概念:權力、自由、民主、社會正義。當我們詢問「我們該如何與一個已然發生巨變的社會共存」,其實是在問,在一個數位科學與科技發展迅速,且已經實質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世界裡,我們社會裡的「權力」、「自由」、「民主」、與「社會正義」是否發生了改變?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因此我們更進一步追問,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並善用這樣的改變?
對於改變的不解,往往造成我們對「共存」這個政治課題有錯誤的認識與恐慌。尤其近幾年,在幾個所謂成熟民主國家,皆發生了應該作為有效反映民主機制的投票系統,受刻意為之的資訊誤導嚴重影響結果的現象。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其中 Susskind 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既有政治制度與思考政治的方式,太過於仰賴遠則兩三百年,短則八十至一百年前的經驗結晶。但這樣的制度與思考和理解它們的方式,也許早已不合時宜。這些制度也許無法消化與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資訊量,因此本應是為了減少成本維持穩定的系統,成了不穩定的來源。
站在舊制度的立場,這個時代當然是充滿危機與威脅。但如果制度也與時俱進呢?以投票來說,如果投票不再需要投票人親身到場領票投票(過往沒有除此之外更好的身份認證方式,但現在有)、投票不再需要人工計票(過往沒有除此之外更好的處理程序,但現在有)、甚至,如果投票本身都不再是「人們如何治理共同體」的必要條件呢(過往沒有更好可以提供頻繁、大量雜亂訊息與意見交會分流,並從中得到最終結論的機制,但現在有)?括弧中提到的,都是目前科技已經有辦法提供的處理機制,這是所謂 E-Democracy 的根本概念,也是 Susskind 所謂政治必須未來化,成為未來政治的理據。
Susskind 並沒有表示我們應該即刻開始如此改變政治體系以及思考政治的方式,而是指出眼前已經具備足夠幫助我們擺脫舊制度的數位與智識工具。之所以無法及時,主要的原因也有許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這些工具並不是被透名、公開的 agency 掌握。這是 Zuboff 的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談的主題。這是個資訊科學與科技發展大幅影響生活的時代,但也是個前所未見的監控式資本主義的時代。監控式資本主義與過往資本主義的差異主要有二。
第一,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是,個人得以透過勞力換取資本,企業獲利仰賴個人勞力累積,因此無論個人勞力換取資本的比例多低,個人始終可以透過禁止輸出勞力作為干涉企業的手段。但監控式資本主義的企業獲利來源,極大程度是透過擬定強迫式契約及未經個人許可所攫取的個人行為資訊,這使得個人勞力與企業獲利結構脫節,個人干涉企業獲利的可能微乎其微。
第二個差異是企業對個人生活與生命歷程的宰制力,這也是「監控式」資本主義的本質。在過往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個人生命歷程有一定比例的時間,是可以脫離企業攫取利益的機制而存活。但在監控式資本主義裡,個人言行極難不受利益攫取機制控制。我們已經不僅僅面臨「需求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整個生活習慣與行動規律都是被創造出來的」。例如,我們必須聽從監控式資本主義企業,引導駕駛時的行經路線,同時回饋至我們的行路經驗。即使我們不使用導航,依循自己的經驗行駛,手機仍能無時無刻傳送我們的行駛路徑,進而提供監控式資本主義企業新的行徑路線以供操縱。
過往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個意識形態迷思,即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必須攜手共進,這是因為相信資本主義的獲利機制,與自由主義中個人的能動性息息相關。但監控式資本主義徹底地破除了這樣的迷思。獲利機制不僅與能動性無關,甚至個人的能動性其實無法不受獲利機制擺佈。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的難題因此也可以是對 Future Politics 的挑戰。我們目前只能仰賴舊制度,試圖制衡監控式資本主義逐步失控的獲利結構,但成效可能有限。Zuboff 將抵抗的新希望寄託於能動性的重新展現(如集體抵制使用 Google),但這樣能動性與受便利與資訊馴化的生活模式對抗的訴求,也許終難落實。
FYI, 遺珠是 David Wallace-Wells 的The Uninhabitable Earth: Life after Warming (Random 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