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克的《處方藥手冊》於一九六七年春天出版,在上市之前就已經掀起軒然大波。一九六七年四月,西維吉尼亞州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勞勃・柏德(Robert Byrd)對參議院呈報了它的預印本,同時申請禁制令,理由是,「如果美國媒體與大眾真的採用這本書,那樣將會動搖我們的藥物產業與美國醫學會,就像拉爾夫・納德的書《任何速度都是危險》衝擊汽車產業。」
其他的參議員則將布拉克的書與瑞秋・卡森的《寂靜的春天》相比較,就像在進行國會讀書會。當親近消費者運動的議員(例如愛德華・甘迺迪與蓋洛・尼爾森)讚揚《處方藥手冊》的時候,身兼醫師身分的保守派眾議員德沃德・豪爾則在眾議院憤怒地揮舞這本書,認為這是消費主義入侵醫藥領域的警訊,它為醫療制度開了個「壞處方」。《商業週刊》的編輯則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詢問讀者,〈藥物產業遇上它的納德了嗎?〉(Has drug industry met its Nader?)。
一九六七年春天,哈佛大學校刊《哈佛深紅》(Harvard Crimson)在與布拉克進行了兩次訪談後,直言他「絕不是另一位拉爾夫・納德」。相反地,這份大學週刊適當地呈現出布拉克友善的一面:納德是任職於劍橋醫院的一般內科醫師,曾經與哈佛大學醫學院的歐德・克萊爾(Otto Krayer)共同研究與教授藥理學。
在《處方藥手冊》出版時,布拉克已經離開劍橋醫院,準備在牛津度過學術假,接著到新罕布夏州的鄉間擔任家庭醫師,這樣的安排完全稱不上是「煽動者」。《哈佛深紅》認為,布拉克在某種程度上應該算是一位「叛逆」的哈佛教授,而不是「普通的家庭醫師」。
布拉克最叛逆的地方,是他願意對病患揭露只有醫師知道的療效相等性秘密規則,鼓勵讀者運用他的書來「反駁」醫師。一九六七年五月,就在《處方藥手冊》發表後不久,布拉克在某次《紐約時報》的訪談中提到,「病患應該要選購藥物,正因為他們是俘虜消費者,他們有權利知道自己買的是什麼,以及要花多少錢。」
如此單純的聲明,為什麼會讓布拉克變成爭議人物?我們必須瞭解,一九六七年的藥品消費者不只受醫師處方的限制,他們對自己購買的藥品也時常一無所知。直到六〇年代後期,處方藥罐仍然不需要標示內容物的名字,許多州甚至明令禁止。
布拉克質疑,如果病患連自己購買的是哪種類別的藥物都分不清楚,又怎麼可能以消費者的身分做出理性選擇?他力勸讀者,至少要瞭解自己服用的是什麼藥,這樣才能查他的《處方藥手冊》:
病患也能精明地消費醫師。布拉克要求病患警告那些拒絕開立學名藥的醫師,他們的業績會因此下滑。同樣地,布拉克也主張有良心的醫師應該承認,他們「對病患所有切身相關的福利都負有責任,包括他的口袋書。」
布拉克的《處方藥手冊》和《醫藥展示》一樣,也依賴某種形式的代理家長主義(substituted paternalism);讀者必須信任他,才能在面對醫師時擁有更「平等」的地位。他所主張的學名藥相等性讓人安心,不過多半是出自於個案經驗。
奇怪的是,在看了布拉克淺顯易懂的文章之後,讀者尋求的卻是超出書本內容的醫學建議。布拉克的個人文件中,有著他與幾百位讀者熱絡的書信往來,人們詢問著關於個人處方、病痛或醫師的專業意見。
雖然布拉克在回信中強調《處方藥手冊》不能取代醫師的判斷,他也建議病患在就診時可以帶上他的書,這或許能增加他們的自主權。某位病患便在回診日的早上寫信給布拉克,「現在我正拿出你的書,請我太太在下午回診時帶給醫師看。我發現我們的醫師沒看過這本書,〔這讓〕我覺得它很有價值。」
布拉克的《處方藥手冊》想把病患轉變為主動的學名藥消費者,這遠超過了《醫藥展示》的企圖。因此,消費者聯盟在自家出版的《消費者報告》中,便對《處方藥手冊》抱持保留態度;他們提醒讀者,儘管這本書「或許能幫助消費者省下處方藥的花費;不過,對於一本同時寫給病患與醫師的書來說,〔這裡〕還是有陷阱。」
消費者聯盟特別批評布拉克不顧學名藥療效相等性的激烈爭議,執意為「所有的學名藥背書」的立場。「很不幸地,關於醫師在不同狀況下對不同療程的判斷,消費者沒有反對的立場。」消費者聯盟的醫學顧問認為,「與其拿著一本外行人的書與醫師爭辯,或者到處逛醫院尋找認同這本書的醫師,支持你自己的醫師應該是更恰當的作法。」
在學術領域,《處方藥手冊》受到了藥理學家艾爾佛列・古爾曼(Alfred Gilman)的抨擊,他是經典教科書《藥理學原理與實務》(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Pharmacology)的共同作者。古爾曼寫了公開信給蓋洛・尼爾森,批評臨床醫界與政界不該在《處方藥手冊》一出版後就馬上照單全收。他呼應消費者聯盟的顧慮,指出《處方藥手冊》隱含的消費者賦權模式太過頭了;此外,他也暗示學名消費主義將會「為醫病關係帶來無止盡的麻煩」。理由很簡單,它「不適合交到外行人手裡」。
布拉克則迴避了這些指控,反擊古爾曼只是輸不起,因為他艱澀的《藥理學原理與實務》的銷量顯然遠不及《處方藥手冊》。幾個月後,參議員蓋洛・尼爾森的助理揭露了古爾曼的利益衝突,原來他的公開信採納了製藥商協會理事長 C・約瑟夫・史特勒的「建議」(與部分手稿)。
古爾曼的評論或許帶著惱怒與自私,然而並不是一無是處。布拉克的著作確實在上市前就已經是出版界的大事。每月一書俱樂部(Book-of-the-month clubs)在幾個月前開始推薦這本手冊,在出版後便立刻銷售一空。藥局與雜貨店的結賬櫃檯擺著《處方藥手冊》的平裝本,和通俗讀物並列。這種混合行銷造就了奇異的讀者組成,包括醫藥專業者、醫學生、關注藥物的消費者,以及越來越著迷於六〇年代揭發製藥醜聞的報導而心懷疑慮的大眾。
當《處方藥手冊》第四版(最終版)於一九七六年發行時,布拉克能自豪地宣稱,學名藥消費已經被普遍接受了。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間,藥物處方以學名藥開立的比例從百分之六點四增加為百分之十點七,這既可以解讀為好消息(按相對值來看,這幾乎等於在八年內成長了兩倍),也可以解讀為壞消息(按絕對值來看,只有十分之一的處方是以學名開立)。
布拉克指出,「某些具影響力的關鍵族群逐漸瞭解,原廠藥產業確實就像那些指控,是最後的強盜資本家(robber-barons,譯註:以剝削與壟斷手段致富),他們展開行動,整頓了醫學組織與藥物產業在『相互往來』中衍生的失序混亂。」他補充說明,事實上,「那個出現在五〇年代末,隨著參議員凱弗維爾調查首度浮上檯面,接著在在尼爾森公聽會前期達到白熱化的『學名藥大爭議』,現在終於平息,能讓絕大多數不帶偏見的專家感到滿意。」
那麼,學名藥手冊還是必要的嗎?要怎麼讓那十分之九的處方也改以學名藥調配?布拉克承認,問題在於醫師仍然相信品牌的力量,這股力量被製藥產業維持著,當作「聲東擊西的煙霧彈,讓大眾沒有時間思考與討論一個更基礎的議題,那就是理性開立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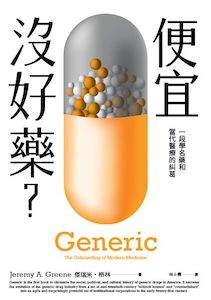
還是魚與熊掌可以兼得?
作者從歷史觀點出發,
談及原廠藥與學名藥之間的爭議、
醫藥專業的利益衝突、
藥廠間的利害關係、專利的攻防戰,
最後論及全球的藥品市場。
我們應該重新思考:
創新 VS.模仿,小公司 VS.跨國企業,
以及公共衛生 VS.私營市場這些對立觀點。
最後,我們會發現,學名藥是少數「便宜有好物」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