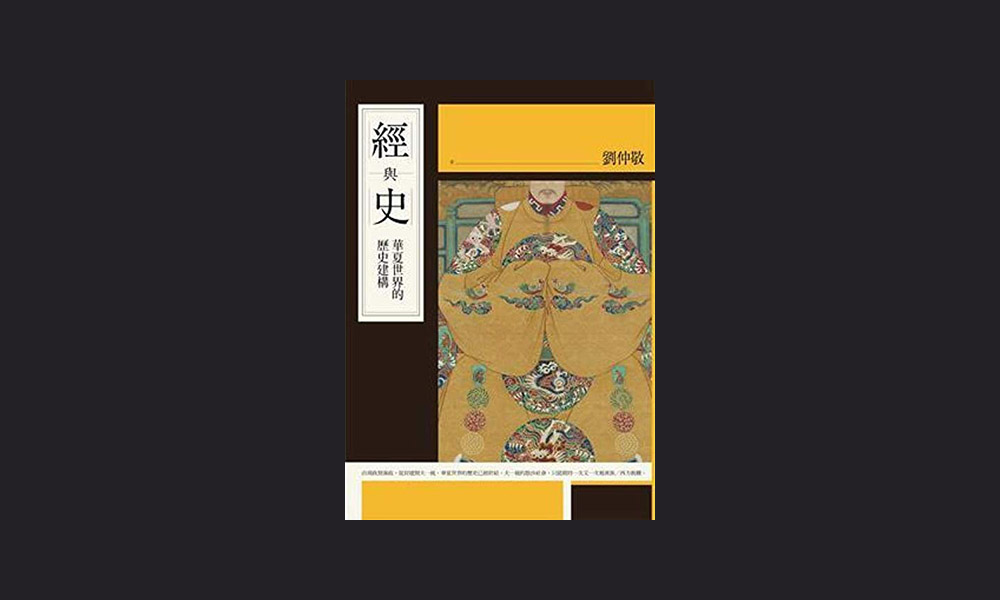一位編輯朋友希望我為劉仲敬重新出版的《經與史》寫篇書評。事實上,我頗猶豫。我並非鄙視普及歷史讀物,反而擔心知識專業化的侷限性讓我無法公正評論這本書。即使能把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句話倒背如流,但作為一位以歷史為職業的教書匠,我長期困在學院內,視野與思考皆深受知識專業化的制約。
我的訓練鼓勵我宣稱對某幾個特定領域的掌握,卻讓我不敢自誇對華夏歷史(作者以華夏代稱中國)有透徹的理解和融會貫通。作者恰好相反。活躍於學院之外的劉仲敬有強烈的企圖心,冀望藉由《經與史》建立一家之言,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從宏觀的角度,重新思考上下數千年的華夏歷史。這樣鮮明的反差,使我感到評論劉仲敬的大作猶如夏蟲語冰。但我又礙於情面,不知道如何拒絕朋友的請託,只得勉力一試。
作者相信,若要正確地理解(華夏)歷史的發展,首先必須掌握其背後的總原則。可惜,當代的歷史知識傳播受到我這類學院派蛋頭學者相當程度的干擾。所謂的學院派蛋頭學者,又可稱之為「學術無產階級」,在專業化歷史知識的生產過程中被異化,強調史料證據的重要性,見樹不見林,欠缺宏觀的視野。
「如果你居然事先沒有全域性的理解,卻想僅僅依靠史料對具體問題下結論;那麼你的結論不僅肯定錯誤百出,而且準確率還會低於富有健全常識的外行。」(頁 14)「如果你抬槓說,我非要見到史料才能下判斷,那你就輸了,多半被吃掉了。按照學院派的觀點,什麼都要實證,沒物證不採信,孤證也不信,那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靠不住的。」(頁 373)作者對學院派蛋頭學者(包括筆者自己)的批評絲毫不留情面。劉仲敬認為,理解華夏歷史不應該自我設限於史料證據,須先知道什麼是「經與史」,才能擁有全面的判斷。換句話說,作者對經與史的定義,是本書關鍵之所在,也是我們同意或反對作者之起點。
什麼是經?什麼是史?「『經』意味著基本法和正統性,是衡量價值的準繩。『史』意味著基於『經』(正當性)的價值裁斷和歷史建構,史官通過歷史編撰,行使世界法庭的職能。……史學負有伸張正義,維護國民道德和信仰的特殊任務。……華夏歷史的建構不是一個技術問題。同時,史學也沒有脫離經而獨立存在的可能。」(頁 13)依照作者給的定義,「經」至高無上,其位階比「史」更高,是先驗的價值理念或原則。歷史學則是建立正當性、塑造國民認知的工具,而歷史書寫必須建立在正義與其他各種價值的判斷之上。
但是,道德價值沒有明確的指涉,是相當空泛的概念,不僅其本身的內涵隨時間而改變,而且不同價值彼此之間時常存在緊張關係。例如,《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也許孔子認爲父子之間應該互相隱瞞罪行,但我們今天不見得會同意他的看法。換句話説,父子倫常與正直的價值内涵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
既然價值判斷是多元的,不是絕對的,讀歷史就不會只有一種觀點。作者如何能提出一套令眾人信服的經學和史學,並主張歷史重建工作的價值絕對性?作者沒有花太多篇幅詳細討論理想的華夏之經應該是什麼,也沒有特別解釋爲什麽華夏(歷史與文明)等於中國。嚴格來説,中國有相當豐富而多元的歷史源流,化約為華夏略顯狹隘。劉仲敬似乎把這些貫穿《經與史》的關鍵概念當成不證自明的。這一點頗令人感到可惜。
他直接斷言,《經與史》之目的是「借助源遠流長的兩希(希伯來和希臘)文明價值和日耳曼—撒克遜憲制體系,釐清遠東諸文明盛衰成敗的線索。」(頁 14)質言之,《經與史》從希伯來、希臘、日耳曼、及撒克遜等四種文明擷取其所偏好的,揉合一套自圓其說的經學,重新解釋數千年的華夏歷史,企圖建立一家之言。
對作者來說,華夏歷史只有少數幾個關鍵時刻。「文明和邦國的興廢都有其不可逆的節點…… 劉邦和項羽的鬥爭很重要,因為涉及大一統和多國體系的路徑選擇。朱元璋和張士誠的鬥爭不太重要,……誰會在乎皇帝姓張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頁 371)這樣的論點來自於作者對春秋時代之憧憬以及對中央集權皇帝制度確立之厭惡。對作者來說,春秋時代並非是儒家所說的禮樂崩壞之肇端。相反地,該時期的「秩序的複雜性和成熟性達到最高峰。」(頁 106)
齊桓公尊王的意義是「『宜粗不宜細』地維護禮樂秩序(『王道』)的根本精神……」,「攘夷可以解釋為諸夏的護憲軍事行動」。而霸主象徵的是「華夏世界的蘇拉,既是法律的破壞者,又是憲法的拯救者。」(頁 102)「城濮之戰開啟了晉楚爭霸的新時代……晉人在現實主義傳統和禮樂傳統之間保持平衡……在此期間,禮樂秩序的定義大大放寬了,各邦憲制的地方性和特殊性日益突出……春秋既是西周封建解體的時代,又是各邦封建成熟的時代……」(頁 107)
爾後,封建制度持續解體,反而使春秋時代複雜而成熟的憲政秩序出現倒退和簡化,直至始皇帝統一六國而到達另一極。秦朝末年,群雄逐鹿中原。項羽嘗試恢復封建制度,而他的敗亡意味著春秋時代的秩序一去不復返。漢朝的建立可說是「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之勝利。(頁 151)此後,華夏世界的「憲制已經確定。今後不再有原則性爭議,只剩下人事和技術性糾紛」。以作者的話來說,這是華夏歷史之終結。(頁 149)
筆者不禁想問,近代西方殖民主義之擴張如何影響已經終結的華夏歷史?若有改變,又如何能宣稱華夏世界的歷史已於漢朝建立時終結?十九世紀下半葉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價值虛無主義的洪水滔天,從來不曾像二十世紀那樣嚴重。」(頁 15)「庚申之亂將大清從世界秩序降為地方性秩序」,「歐洲式的國際體系觀」衝擊朝貢體系的世界觀。(頁 334)「庚子之亂不再是尋常的各國交兵,而是國際社會集體懲罰踐踏國際準則的肇事者。《辛丑合約》不是為戰敗國準備的,而是為犯罪準備的。」(頁342)諸夏淪為蠻夷,其原先地位由日本取而代之。這是以大英帝國為霸主,「體現封建遺風」的新春秋時代,而日本則「擔任英國在遠東的代理人」。(頁 338、344)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新春秋時代結束,新戰國時代開啟。
接著,作者筆鋒一轉,開始談論二十世紀以降國際政治的局勢變化對華夏世界的影響。他大膽主張,美國是當代的新羅馬,「繼承了三重遺產:羅馬的古典共和主義、英格蘭的傳統自由、新教徒的救世主義。最後一種元素是她最根本的驅動力量,給她的世界體系賦予了特殊的色彩。」(頁 366)美國正一步步朝「世界帝國的終結點」邁進。「任何人阻礙自由帝國主義的群眾大軍,相當於褻瀆神明的政治版。」(頁 367)「在這種情況下,爭取『羅馬人民的朋友』資格變成了最大的國家利益。」(頁 368)既然作者不加批判地接受美國在當代國際關係扮演的角色,肯定美式自由民主的價值,也認同美式自由民主向世界輸出,這暗示作者希望華夏世界的未來能無限接近趨近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羅馬。作者因此總結,「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如果尚未終結,就要這樣的世界上展開。」(頁 369)
我們應該如何評價《經與史》?起碼對筆者來說,《經與史》的說服力是稍嫌薄弱的。即使不吹毛求疵,作者提到的「經」:兩希文明和日耳曼—撒克遜憲制體制,又提到新羅馬的三重遺產,看似兩種不盡相同的價值體系。兩者之間有什麼關聯?這部分的解釋付之闕如。如果「經」的定義含混不清,作者又如何奢言重新建構華夏世界的歷史?大體而言,作者心中理想的史學,依然屬於傳統的春秋筆法,只是另有一套價值判斷的標準。作者博覽群籍的用心令人佩服。劉仲敬身處學院象牙塔之外,不受學院成規之束縛,自由運用豐富的想像力,大量援引歐美歷史事例類比,提出一套相當具有個人特色的歷史敘事,的確自成一家之言。至於讀者同意與否,不是筆者這樣的蛋頭講師能隨便說三道四的,得靠讀者自行判斷。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