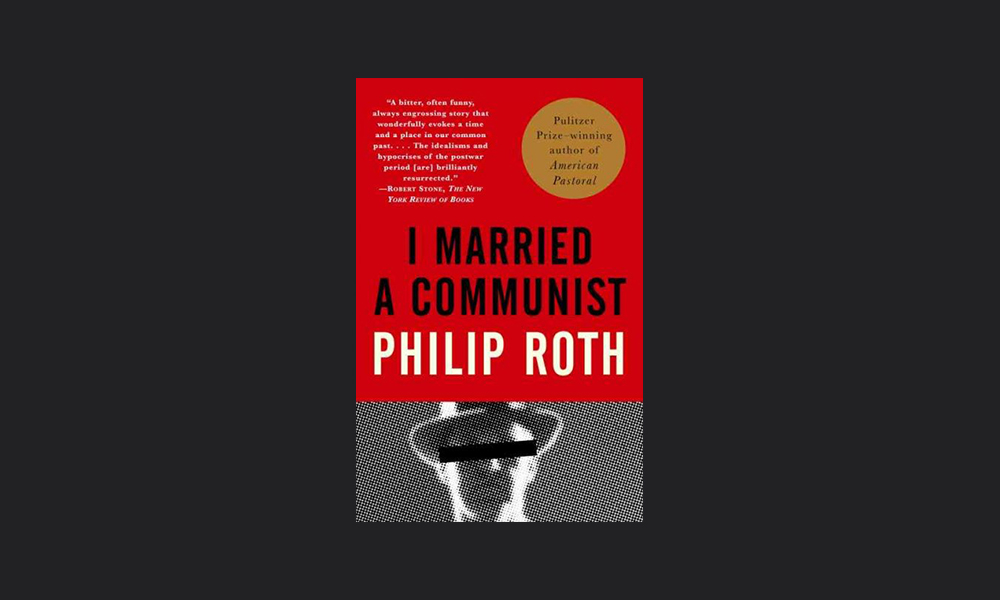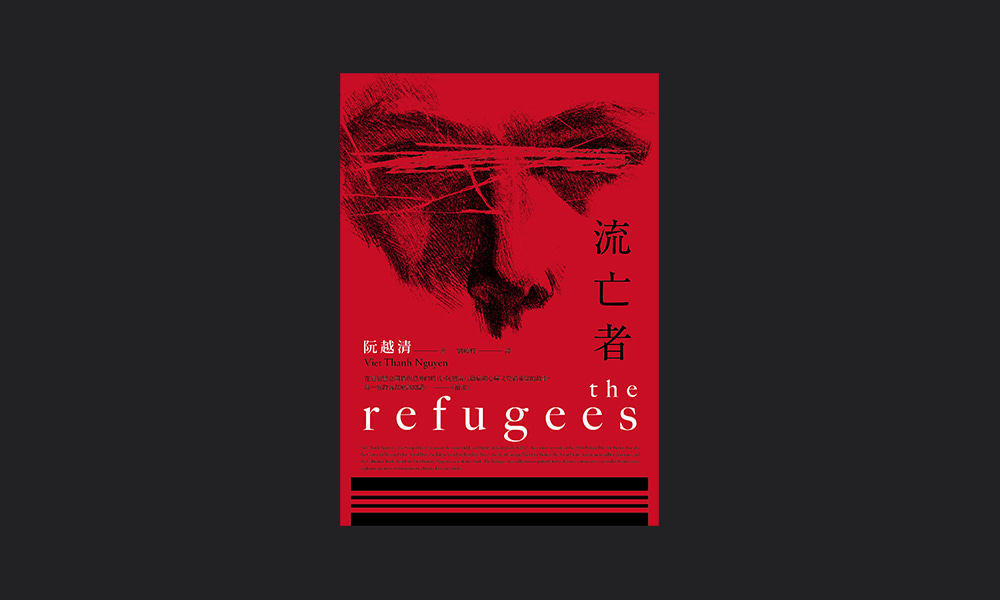臺北:木馬文化,2005。
羅斯的冷峻公知形象
自今年五月美國左翼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去世以來,媒體大多致敬和緬懷他對二十世紀美國社會的剖析和刻畫,無不強調一則冷峻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
不錯,從《再見哥倫布》、《美國牧歌》到《人性污點》,從宗教、種族到戰爭,羅斯的小說和他本人都帶着一種美國式左翼風格。譬如他常用自傳式筆法描繪猶太青年在二戰和冷戰語境中的成長經歷,剖析官方政治圖景下非主流生活的細節。與羅斯同時期的美國作家,包括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也都以這類注重現實批判性的作品而著名。
有趣的是,這種社會觀察的角色似乎通常都由男性作家扮演,我們是否能想到一批同樣擁有現實批判作家名望的美國女性小說家?哈波・李(Harper Lee)的作品《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1960)流芳百世,但她並不如羅斯那樣多產。當《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被改編成電視劇後,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才作為政治批判作家被大眾所知。[1]
進步、理性、冷峻、甚至民主和自由等概念難免帶着默認的性別印記,但在男性左翼作家以冷峻知性的形象剖析社會現實時,他們如何掩藏自己的脆弱和私慾?公共知識分子在私人領域的人格和道德是否應該與公域一致?
在羅斯眾多批判美國社會的著作中,有一本就不經意地揭示了這位左翼作家的內心世界,那就是他回應前妻回憶錄所著的《我嫁了一位共產黨員》(I Married a Communist,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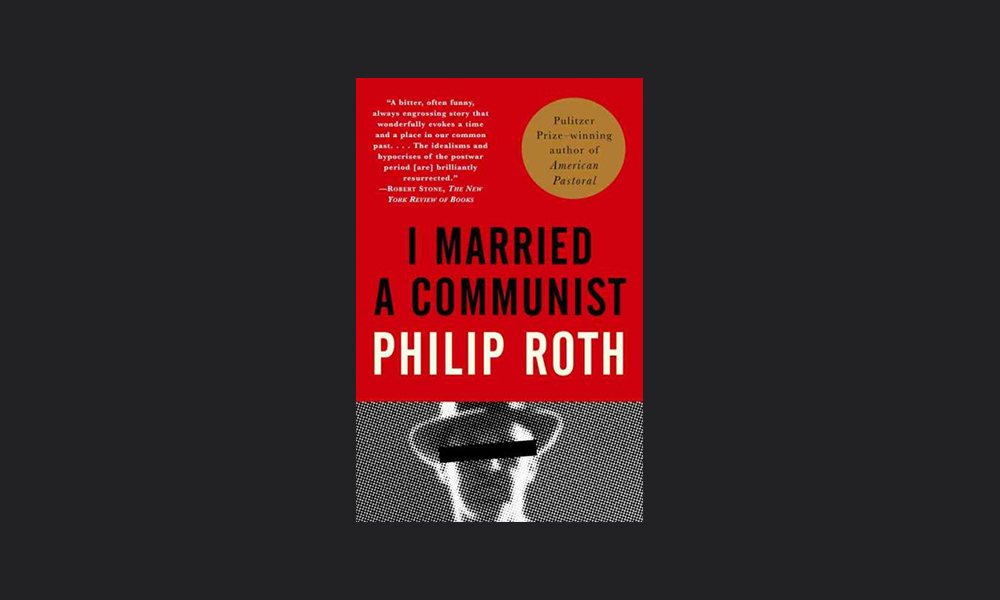
與前妻之間的輿論爭奪戰
《我嫁了一位共產黨員》是羅斯「美國三部曲」的一部分,但這也是一本報復性的自傳式小說:羅斯本人的前妻、英國女演員克萊爾・布魯姆(Claire Bloom)著書《出走玩偶之家》(Leaving A Doll’s House: A Memoir,1996),講述她與羅斯生活的點滴矛盾,披露了羅斯痛苦的生理疾病,藥物如何致使羅斯性格扭曲,以及羅斯如何在文學創作中將他們的現實生活與想象的情節交織,比如男主角的濫交,讓克萊爾無法分辨真實與虛構,也越來越難以信任羅斯。羅斯也討厭克萊爾與前夫所生的女兒,限制克萊爾的經濟自由,甚至將兩人的對話作了錄音。克萊爾的回憶錄引起羅斯不滿,成為出版《我嫁了一位共產員》的契機。換言之,兩人用文字打了一場爭奪輿論的筆戰。
《我嫁了一位共產黨員》的背景與羅斯的大部分作品相似,也是從猶太青年的成長歷程講起,同樣圍繞美國政治和猶太身份,特別關注麥卡錫主義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細膩地描寫談冷戰時期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氛圍和餐桌對話。
在這樣的背景下,羅斯講述了一個幾乎在冷戰時期不可能的愛情故事:銀幕美人伊芙(Eve)與草根出身的艾拉(Ira)轟轟烈烈地相愛了。但伊芙最終出賣了艾拉,出版自傳《我嫁了一位共產黨員》,將艾拉描繪成偏執而瘋狂的蘇聯間諜,在麥卡錫時代背景下致艾拉的職業生涯和個人前景於死地。被激怒的艾拉試圖殺死伊芙而未果。
小說主人公的名字「艾拉」在拉丁文中就是憤怒的意思。羅斯本人的名字也和憤怒(wrath)相近,這是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巧思。艾拉和羅斯一樣來自貧困的猶太家庭,在新澤西州以意大利人居多的區域中長大,不得不一手打拼自己的出路。艾拉曾憤怒地說道:我們只有漸漸學會憤怒。小說借旁白解釋了他兄弟的暴力行為:我們身邊有很多像艾拉這樣憤怒的猶太人……這是美國給猶太人最大的饋贈:憤怒。
憤怒的艾拉在礦產豐富的新澤西荒野中挖過溝,做過礦工、服務員;十六歲的時候因為激憤而殺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在陸軍服役,被左翼思想打動。艾拉外形高大,尤其神似林肯,也在舞台上因扮演林肯而成名,成了代表美國左派英雄的左派英雄。因為林肯,艾拉開始進入演藝圈,找到了在電台的工作,也成開始出演電視劇,由此認識了女演員伊芙。兩人的愛情故事是該書的核心線索。
伊芙是一位來自布魯克林的猶太女子。她努力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默片女演員之一。但羅斯對前妻之恨,令他選擇用哥特小說《蝴蝶夢》(Rebecca,1938)裡描寫陰魂不散的女主人的手法來鋪陳她的出場,在全書開頭通過他人的流言由讀者構想女演員。
羅斯把伊芙描寫成一位病態的猶太人:她為自己的猶太身份感到尷尬,也為她的女兒長得像猶太人而尷尬。伊芙曾嫁給一位英國同性戀演員,內化了對方的英國式優雅,將這些細節帶入自己的生活,掩飾布魯克林猶太人的身份。現實生活中,羅斯的前妻恰恰是英國人,這一點讓人忍俊不禁。
伊芙對自己身份的厭惡也體現在平日閒話中,譬如「在好萊塢,地下共產黨員十有八九是猶太人」,這在冷戰時期是一句殘忍的指控。而伊芙最後在自傳中將猶太人艾拉描繪成蘇聯間諜,也再次重申了她原來輕飄飄的閒話。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到,伊芙在小說中是一位毫無政治智慧與道德原則,且為了私慾能夠出賣一切的女子。
伊芙的女兒也是兩人感情破裂的導火索。伊芙的女兒被刻畫成一位有暴食症的肥胖女子,厭惡母親,在家中和公共場合都控制和摧殘着伊芙,處心積慮破壞母親與艾拉的關係。艾拉苦心說服妻子與女兒分開,希望削減母女間的相互依賴,讓女孩和伊芙都得到獨立的自由。但伊芙在情感選擇上背叛了艾拉,有一晚在大家談論共產主義時,伊芙突然不顧一切地尖叫。也在政治上背叛了他:她所出版的自傳將他描繪成瘋狂的蘇聯間諜,又讓艾拉陷入危局。從一無所有而來的艾拉曾苦心經營的政治理想和事業都付之一炬,他本人也一蹶不振。
但羅斯確實是語言大師。他寫女主人公的美,說「她不僅儀態精緻或模樣高貴,而有種美得讓人捉摸不定的優雅,一種介於黑暗的異域風情或溫柔的拘謹之間的美,一種必然引人入勝的美 」;寫伊芙與艾拉的愛情,說「我們的愛有近乎疼痛的甜蜜和奇特,它不斷讓我融化 」,引用艾米麗・迪金森的詩
和你一起,在沙漠──
和你一起焦渴──
和你一起在羅望子密林──
豹子得以呼吸──終於!
這是作家永遠讓人捉摸不透的地方:他是否借筆下人物回憶和悼念自己與克萊爾曾經的情感,抑或僅僅為創作而構建了這樣的情節,而將真實的情感掩埋?小說自然可說是虛構的創作,但情感是否能夠真實?
大時代的男性經驗?
艾拉的故事由艾拉的兄長穆雷與旁白「我」的對談中緩緩呈現。對「我」而言,艾拉和他的兄長是「我」在冷戰時代的父親角色,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的見解讓「我」大開眼界。
「我」對那個時代的記憶也包括私生活的細節:艾拉的老車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做愛的地方,「我」清晰地記得當時自己的左腳踩在剎車上。這樣的回憶讓給此書染上了一層男性代繼相承的色彩:男性才是時代政治的媒介;也讓人心生好奇:究竟有沒有在描繪水乳交融的過程中精準地抓住女性體驗的直男作家?同時,伊芙的角色設置也落入常見的性別敘述:女性是有魅惑力的怪物,不但在「大背景」中毫無能動性,最終更會背叛和摧毀本可以造就時勢的男性英雄。
意識形態和大環境要放置在個人脈絡中才耐人尋味,對大時代的描繪總要與小人物的故事結合才顯得生動真實。艾拉與伊芙、或羅斯與克萊爾・布魯姆之間的問題也是一個大時代中一個群體如何摧毀另一個群體、人們如何在意識形態的藉口中彼此摧毀的例子。
在《齊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1957)中,帕斯捷爾納克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那些在家庭生活中不愉快、沒有能力處理個人情感的男人如何爭先恐後地報名參軍,企圖用時代英雄主義掩飾自己的懦弱。我們可以看到時代和意識形態如何塑造一個人、一個群體,又如何摧毀一個人、一段感情。相應地,個人如何用意識形態等更大的東西尋找意義,為自己的軟弱和脆弱作推脫。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從羅斯本人的生命歷程來讀《我嫁了一位共產黨員》,不但為作家本人,也為時代作了意味深長的註腳。
[1]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確實是女性批判作家的代表人物,但她主要以散文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