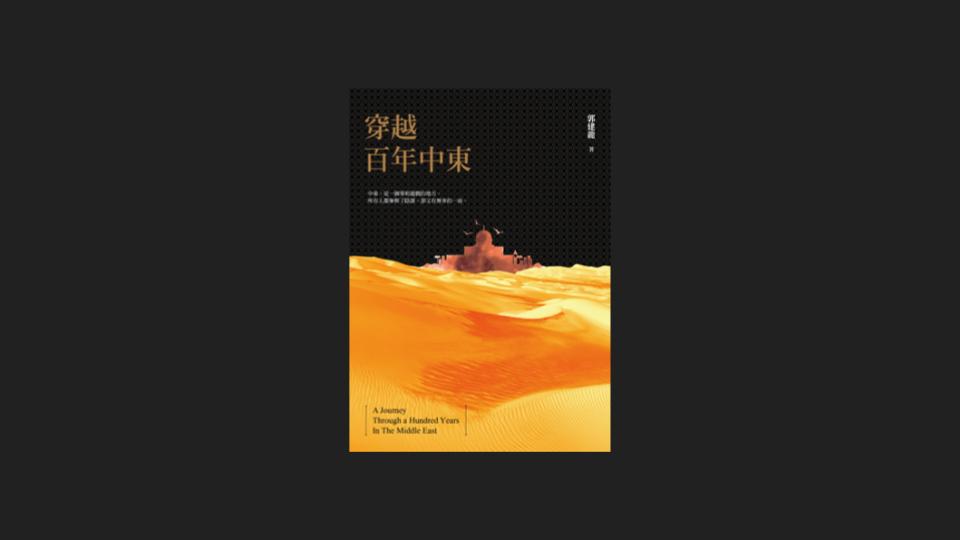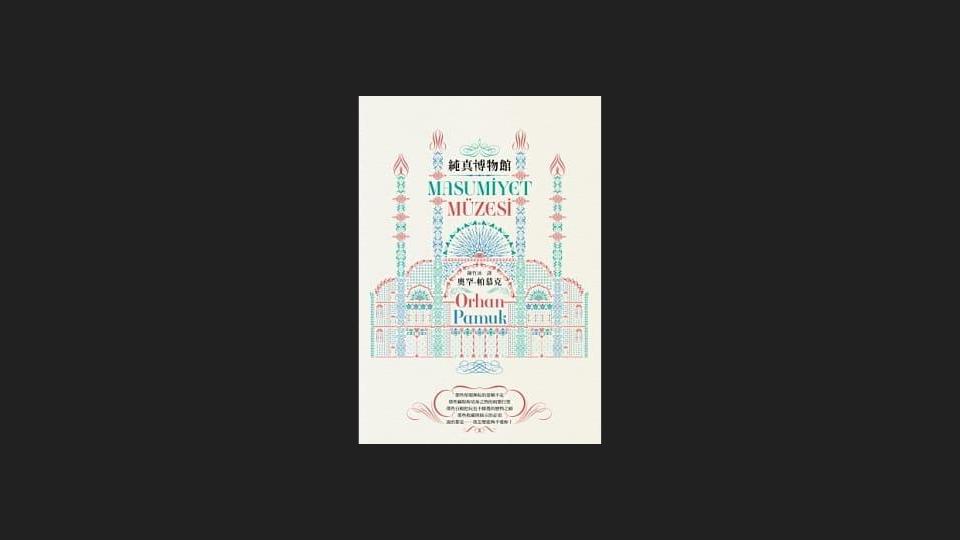「在追尋故鄉的憂鬱靈魂中,發現文化衝突與交疊的新表徵。」—2006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評語
上回介紹了土耳其籍作家奧罕.帕慕克的在 2008 年的最新小說作品《純真博物館》,這次則將介紹作家在 38 歲時(1990 年)所出版的《黑色之書》。

卡利普是一名伊斯坦堡的執業律師,某天下班回家,迎接他的只有愛看偵探推理小說的妻子魯雅(土耳其語的語意為「夢」,對岸版本的此名翻譯則為「如夢」)所留下的告別紙條,接著他發現自己一直仰慕的妻子的同父異母哥哥耶拉,一名行事總是神祕但全國知名的報紙專欄記者,也失蹤了。
卡利普不只在伊斯坦堡的大街小巷中,從與魯雅有關聯的人事物中找尋線索,他還深信耶拉的所有專欄文章中都包含著暗語,在暗示著一個謎團。
而他只要投入耶拉的世界,將自己代換成耶拉的身分、角度、生活作息去思考,最後甚至開始代筆替耶拉寫專欄,那麼他就能從耶拉的專欄文中解開「謎」,找到追尋他的妻子魯雅以及妻舅耶拉的下落。
故事就是這樣從兩個人的消失,一名肩負偵探責任的主角,展開尋找線索並解謎的事件開始,然而「尋找線索」與「解謎」在接下來的發展中,卻轉身一變,化成兩條故事線:一條是卡利普在外頭大街小巷中不停地聽著不同世界不同世代的人們的故事,追尋著消失者們的蹤跡線索;另一條則是刊登耶拉舊稿的專欄文章。這些文章被不同世界、不同世代的人們,根據自身經驗來詮釋、解讀藏在文章中的「謎」的暗示故事。
在此書中,所謂的「線索」與「解謎」並不是重點,重點是以此二手法作為手段,去對於「何謂做自己」的大哉問作出外向擴展與內在深掘的交互詰問過程。
《黑色之書》並不是一本推理小說,而是一本對於作者身處的故國土耳其──包含著歐洲與亞洲兩洲區域為國土的這個世界──的歷史交疊與文化衝突的觀察與紀錄,進而從這些交疊與衝突中,試圖對於「身分認同」做出定義。
整本書透過一個又一個人們訴說的、如同《一千零一夜》般的故事,與消失的報社記者由自身去挖掘並轉換成專欄文的另一種故事形式,兩者相互印照,相互堆疊。
這可以是一本土耳其近代史的小說、一本哲學探討的小說、一本作者自身提出疑問與提出解答交錯的純文學小說,但絕對不是推理小說。很多讀者都因此覺得被騙了。
值得玩味的是,在此書中奧罕─帕慕克仍舊慣性地使用華麗繁複文字技法,但並沒有他一貫在作品中對於故國往日散發的強烈的「呼愁」感,可是他仍透過小人物們的故事提及家國的歷史。
雖然他的文字技法為文學圈詬病,也不忘偶而提及家國的曾經的榮光,但《黑色之書》卻因為不停地詰問、辯論、探究,反而被譽為奧罕.帕慕克最好的文學作品。
或許可從這個高尚的讚譽來反思,文學,是否已經走到被定義得太過僵化或者是太過遠離世俗的狀況?
回到此書,奧罕.帕慕克繼續用他為人詬病的總是費盡心機安排篇章順序,而將看似不相關的兩條故事線,漂亮且巧妙地串連成一個題目,去提問去回答去反思去辯證。因此讓這本書就像近年聞名的「禪繞畫」一樣:從反覆繞繪的過程中,完成成精緻細膩的圖案。再透過不同的圖案拼湊,達到一個繁複的結果。
「禪繞畫」的由一對美國夫妻,先生曾具僧侶的身份,妻子則是一名植物插圖藝術家兼書寫體藝術家一起發展而成的創作方式。透過有規律以及一筆一畫構成圖樣,讓繪圖者透過專注而達成放鬆的狀態,並從中得到平靜入禪,獲得心靈療癒能力。

然而《黑色之書》中每個一筆一畫精心描繪、層疊交錯的圖案,所拼湊出的卻不是平靜,而是一股向世界向自己詰問的憤怒。
「做自己」這三個字,在現在的台灣被用到非常氾濫了,可謂是「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代表的關鍵詞;「做自己」這個三個字,也在《黑色之書》之中氾濫地被使用。只是在奧罕.帕慕克的眼裡,這三個字,代表的是「土耳其」這個曾經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燦爛輝煌的歷史聞名於世的國度衰落消逝之後,變成了在領土與文化上既是東方又是西方,既不是東方又不是西方的「迷失」的國度。
奧罕.帕慕克透過「『謎團』失蹤」與「追尋『夢』」的方式,帶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個人身分迷失」、「個人身分認同」,追尋著故鄉過去的逝去與未來的不確定性。
對讀者而言,此書以一般推理小說的寫法展開:「有人消失了,有人開始尋找了。」於是,懷抱著想要享受偵探推理的過程,抑或是被勾起躍躍欲試想知道跟隨追尋者的腳步找到失蹤者結果這樣的想法進行閱讀。
最後卻迷失在奧罕.帕慕克最擅長也最為讀者或者文學界詬病的創作習性:精心雕琢與堆砌過的文字之謎,以及對「何謂做自己」這個問題的反問追問,進而能找到真正「做自己」的夢想之中。
因為這並不是一本推理小說,小說內容也沒有用邏輯精心設計過的線索以供追尋,所以提及故事的結局並不會有破梗問題。結局就是魯雅與耶拉都死亡,卡利普則成為了耶拉,但卻越來越搞不清楚自己是卡利普還是耶拉。
夢和謎都消失了,「做自己」卻仍未獲得解答。
奧罕.帕慕克在書中用一名敘事者(未明指是否是卡利普)去告訴讀者,此書不該有解答也不應該結局。結局的部分應該全部被塗黑。
只是作家也在本書的最後透過一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王子的故事去試圖解答。王子為了不像兄長一樣因為對於王位繼承的漫長等待而發瘋,他決心找出「做自己」的方法。王子大量閱讀,卻發現從閱讀之中,每部作品都讓他成為了該位創作者或者是該作品的角色。他做不成自己。
於是,他把他所學和所擁有的一切全部丟掉,讓自己成為了「空」,把他身處的小屋漆成全白,這樣就沒有人能夠影響他。但他還是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做自己」,於是他在空白的內在心理與外在環境中,找了個口述記錄者,將他的故事寫下,以文字的形式完成了「做自己」。
「做自己,好自在。」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 slogan,相信台灣的朋友都耳熟能詳。
但若是把這個 slogan 拿到土耳其並交給奧罕.帕慕克看,在他對故國的夢和謎都消失了,陷入於追尋的憂鬱中:眼見故國在文化衝突與交疊中迷失,不知道他對這個 slogan 的想法會是什麼?
或許,依舊是沒有答案,而且結局未完。
白色是反射所有光的,而黑色則是吸收了所有的光
若不以色彩學的觀點論,全白與全黑其實是同義的。
全部的反對與全部的接收,都是一種失去。
於是這裡蒼白如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