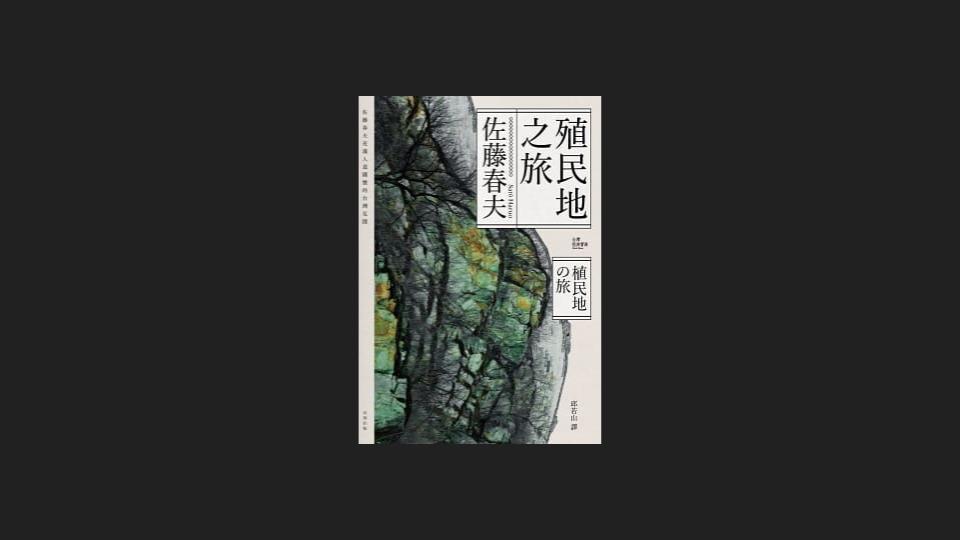「阻擋不了浪潮,那就航行吧。」
──Margaret Atwood, The Year of the Flood
我在學術上的專業研究領域之一,是日治時期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然而我生也晚,又長年留學他鄉,所以始終無緣接觸到那些活躍在《警察沿革誌》或者《台灣文藝》書頁之中的歷史人物。楊逵先生,是我唯一曾短暫親炙過的戰前民族運動世代前輩。
一九八三年冬天我透過楊翠,邀請了楊逵老先生到台大演講,作為「台灣文學週」活動的壓軸。當時我是台大代聯會主席,因為沒有入黨,成了國民黨眼中的可疑危險的校園「黨外份子」。我向課外活動組申請辦理「台灣文學週」系列演講時,課外組主任曹壽民告訴我,根據台大外文系某蔡姓教授的「專業」意見,「並不存在『台灣』文學,只有『在台灣的中國文學』」,要我更改活動名稱,否則不許舉行。
後來經過一番「學術」「專業」談判,總算准了活動,但楊逵這場卻又特別派了課外組幾個組員監視,因為擔心有「黨外人士」出現鬧場,他們還預先警告我,活動中不准楊逵和楊翠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上台。
我已經不記得那晚楊逵先生講了些什麼了,不過總之絕對不是什麼「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然而我依然清楚地記得他一身黑色台灣衫的瘦小身影,溫暖而滄桑的笑容,還有娓娓道來的親切的台語,釀出了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重量與力道,深深地震懾了年輕無知,而且早被強制抹除了歷史記憶的我。那晚活動中心來了很多同學,場面很熱鬧而溫暖,很有一種歷史現場的感覺,生性善感而容易衝動的我,受到那種奇妙氛圍的感染,不顧課外組的警告,硬是把坐在台下的民歌手楊祖珺小姐拉到台上,鼓動我的伙伴和場內所有人,在她的帶領下一起合唱了楊逵作詞、李雙澤作曲的《愚公移山》。
活動結束後,課外組 D 姓組員在離開會場時,對我不客氣地說:「吳叡人,你自己看著辦吧!」我沒有理他,因為終於和台灣的歷史臍帶連結起來的衝擊,正使我百感交集,無法自己,媽的要記過就記過吧,誰在乎這些歷史的泡沫呢。不久以後我接到一封公文,發覺我只被記了兩個警告,因為根據他們的「校規」,我一旦受到小過以上的懲戒,就必須被強制解除代聯會主席職位,但他們不想讓我變成為一個校園「烈士」或者「政治犯」,所以只記了兩個警告,點到為止。
因為我不抽菸,身上沒有打火機,所以我把那封公文撕破,隨手丟進了垃圾桶。
那次我沒有機會變成「校園烈士」或「學生政治犯」(令人遺憾的是,儘管後來我做了一些更危險的事,但始終沒有機會成為烈士,有人天生就只能做第二線或第三線人物),沒有機會創造歷史,不過我卻遇見了台灣歷史。楊逵就是我的台灣歷史。那個冬夜,我曾經從父親書房裡的小學館《日本史》殖民地篇,從偷印來的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和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裡面讀到的那段用文字編織的神祕歷史,突然變成了血肉,有了生命,攫住了我的靈魂。
然而那是一種過於茫漠巨大的歷史意識,而我太無知以至於無法辨識它的意義,太年輕莽撞以致無法理解血肉終會萎縮,生命終會消逝,於是我在無知莽撞之中,竟然就這樣和楊逵先生交錯而過,甚至沒有再轉身向他叩問一次關於這一切的意義。兩年後,楊逵先生過世了,我唯一親炙過的歷史前輩如今又化為歷史書頁中的抽象鉛字。
所以那個冬夜我從楊逵先生的身影和話語中感知到歷史的存在,歷史的體溫和重量,但我必須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後才開始理解那些歷史的意義。我開始體會到台灣政治學與社會學之缺乏歷史意識,開始「折節」修習台灣史,已經是九〇年代中期以後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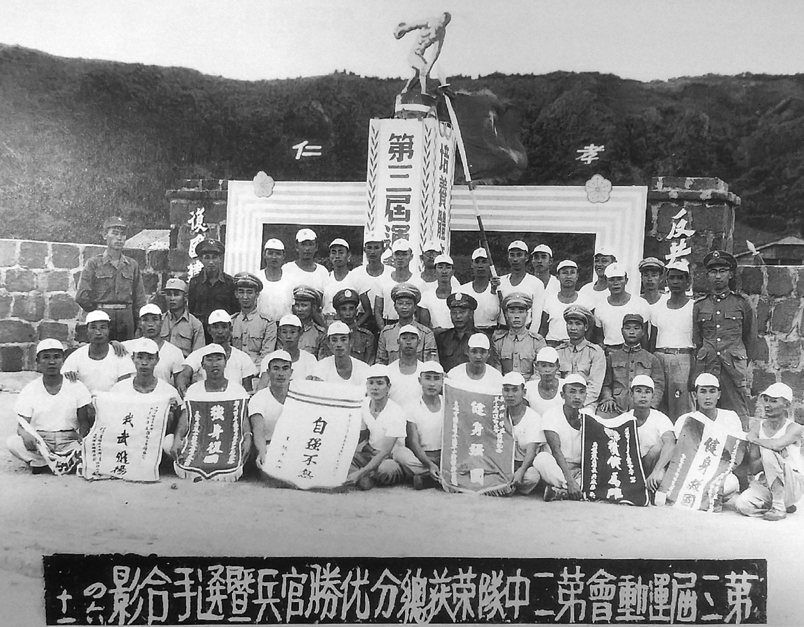
等到我開始笨拙地嘗試運用我在西洋政治思想史課程學到的方法來解讀台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文本,開始一篇一篇累積我對這些困難的、不透明的文本的解讀,直到我終於寫出了一本叫做〈福爾摩沙意識形態〉的博士論文,弄清楚了一點那個世代的精神輪廓,又過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然而楊逵在我晚熟的台灣史與台灣思想史意識中,卻依然是一個巨大而模糊的形象,他比較像是一個人格典型(抵抗者),一種行動典範(組織與啟蒙工作者),而非思想或意識型態的化身。
然後我從早稻田回國,開始研究芝加哥時代未完成的台灣左翼傳統研究,並且完成了一篇連溫卿研究後,終於在一字一句重讀《警察沿革誌》的過程中和楊逵先生再會,而這一次他終於以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明確姿態出現在我描摹的光譜之中。儘管如此,我並不真正理解這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楊逵,也尚未開始試圖去理解他,因為這時候我忙著學習世界語,深深地沉浸在另一位社會民主派連溫卿複雜、重層的思想世界之中。
然後又過了十年,楊翠寄給我《綠島家書》,我開始重新閱讀這些過去自以為明白易懂的文字。現在的我,和大學時代比起來,多知道了一點台灣史和世界史的知識,學會了一點解讀歷史文本的方法,還多了一點研究二二八事件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還有在民間從事轉型正義工作的經驗,而且才剛出版了自己生平第一本文集《受困的思想》。
這些歲月的積累對我重新閱讀這些看似平凡的家書頗有助益。我先讀了一遍,然後再一遍,一開始非常困惑,因為似乎找不到太多可供深度解讀的文字段落,也想不出任何具有新意的詮釋。這些文字就是一種特殊的「家書」,是一個政治犯在嚴密監控的條件下寫給自己妻子兒女的信,充滿了日常性的細節,不能陪伴在妻子兒女身旁的歉意,以及試圖透過文字參與妻子兒女生命的熱切的補償心意。他們也表現了書寫者一種難以形容,甚至難以解釋的人格強韌與樂觀進取。這些文字動人,然而透明到了不透明的地步,因為他們呈現的是一個太過私密的,外人無由進入的情感世界。
讀到第三遍或第四遍,我開始注意到書寫者反覆致意的幾個關鍵詞,如「土地」、「農場」與「家園」,如「互助」、「協力」與「自足」,以及反覆提起,幾近於執著的一家團結,共同建立「理想農園」的夢想,例如以下這段寫給長子長媳的代表性文字:
八月底有一位朋友會約你去白河…看土地。他有三十幾甲(有山、有園)的共業,可以合作,也可以請他們讓幾甲給我們經營。詳細情形到實地察看商量一下。這地方離城市較遠,自然不合種植零賣草花。不過,果樹、果樹苗和菊花、花菖蒲等的大宗生產及種苗球根的生產是可以的。更可以換些飼料餵雞鵝。因不零賣,倒比在城市種零賣花草有時間來看書寫作,對於我們的整個計劃來說也許是更適宜的。祖母的扶養問題不必介意,只要把一個理想的農園建立起來,我一定有辦法請她出來同住,讓她快樂享受晚年。大姊自然也可以安置的。
長年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史與左翼理論的專業敏感,讓我突然聯想到這個看似執迷的世俗夢想之中,似乎隱藏著一個完全不世俗的烏托邦願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事不可為的黑暗年代中,試圖透過家族互助,深耕土地與農業勞動,建構自主生存基礎的迂迴的個人實踐計畫。
這也是一種「孤島」,不過不是楊翠所描述的那種被國家暴力傷害與隔離的,悲傷的個人孤島,而是在資本主義大海中浮現的一個個以家族為基礎的,互助與共同勞動的幸福之島。如楊逵在信中說的:「不能走直線的時候,你們應該轉彎。」在資本主義的洪水之中,我們家人應該緊緊相擁,結合成一座保有了最低限度人性與幸福的島嶼。
然而這個突如的聯想或狂野想像,這個過於跳躍的解讀其實依然不夠深刻,依然只是停留在表層,停留在我作為一個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專業形式之中,沒有觸及到事物的深層本質,也就是楊逵其人的本質,直到我再一次從頭閱讀,注意到楊逵次子楊建的提醒,這些家書大多因超過三百字的限制而未曾寄發,直到我重新閱讀了楊翠的〈穿越時空的家書〉,讀到她提醒說這些家書因未曾寄發,因而是「作家私語的日記」,我才終於理解到這些家書的特異之處──幾乎所有這些親情絮語,所有這些鼓舞勉勵,所有這些「馬拉松式的」勇氣堅毅,所有這些「雷公打不死」的樂觀,所有這些「長遠的計畫」,這些建設理想農園與個人社會主義實踐的烏托邦的傾訴,幾乎所有這一切都是楊逵孤身一人在火燒島的獨白,在孤獨之中與自己靈魂的對話。

在火燒島上,在孤獨之中,楊逵靠在勞動改造的菜園裡的肥皂箱上,在簡陋的筆記本一字一句細密地、綿密地、稠密地印刻他與家人的想像的對話,包含著懺悔、叮囑、鼓舞、責問與指引,刻印一種無法分享,無從交流的溫柔與摯愛,刻印一種執迷的、終生不悟的熱情──刻印一種沒有根據,無須根據,無法證明,不證自明的,只要人活著,只要人渴望活下去,就會從靈魂深處迸發出來的,叫做「希望」的東西。然後我才發覺,和楊逵擦身而過三十三年後,我終於好像看懂了他那「似溫馴而又不太溫馴」(Scalapino 教授描述台灣人的用語)的,謎樣的溫暖笑容的意義。
於是我才理解,《綠島家書》書寫著楊逵朝向希望的意志,它是台灣人精神史上的一冊希望之書。
2016.8.2 清晨三點三十九分於草山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孤獨之中,
楊逵在簡陋的筆記本一字一句印刻他與家人的想像的對話。
這些獄中家書原本是寫在 25K 的橫條筆記本上,
一直等到楊逵過世一年後,
才由有心人將它送交他的家人手中,
這些未能寄發的信稿,
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
讓人感受到這位生命勇者陽光般溫暖的愛。